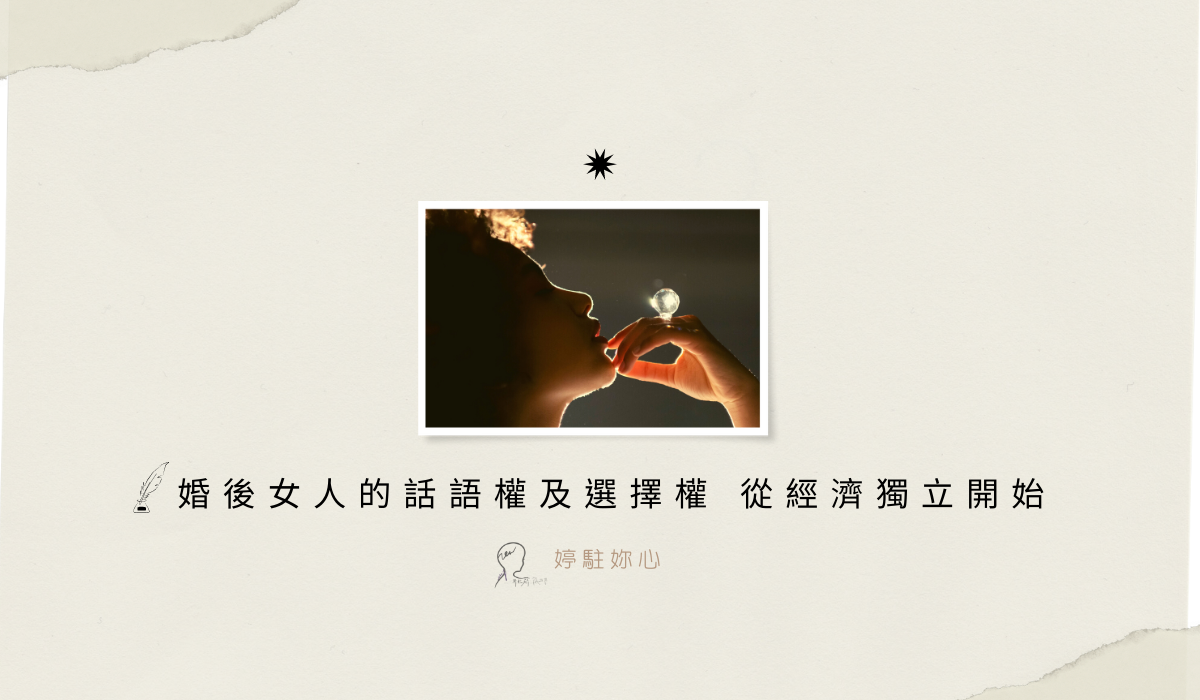與家務分工相關的性別研究一直不在少數,就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Claudia Goldin也提出「嬰兒與宏觀經濟學」(Babies and the Macroeconomy),探討為何部份國家的生育率穩定處於每位婦女約生育1.6個孩子,反觀南韓、日本和義大利等國則下滑到最低水準,每位女性平均生育低於1.3個孩子。Goldin認為嚴重失衡的家務分工型態,正是南韓淪為全球生育率最低國家的主因之一,南韓女性每天從事無償家務的時間比男性多出2.8小時(註1)。
在性別研究領域裡,早已從關注可量化的無償勞動時數轉移到更幽微的隱性勞動。例如,研究空服員勞動狀態和職場女性第二輪班的Hochschild(1989)提出如今我們耳熟能詳的「情緒勞動」和「家庭生活管理」。Coltrane(1996)、Allen& Hawkins(1999)等學者指出「管理家務的認知⼯作」與協助完成家務的體⼒⼯作是不同的。另外也有學者著重在家庭的規劃工作,提出該勞動如何不同於一般的體力活。然而Allison Damingera認為,即便將勞動區分出體力和情緒兩種也有所不足,在"The Cognitive Dimension of Household Labor"一文中,Damingera提出「認知勞動」的概念。
***什麼是認知勞動?從受訪者自述來看,當Alan把妻子形容為「專案經理」,或Jason提到妻子「管理更多事情」時,都暗示了體力工作(如做飯、打掃、付帳單)與認知工作(如預見需求、做決策、監督家庭運作)之間的區別(註2,p. 609-610)。作者聚焦於後者,也就是本文所稱的認知勞動。在研究中,Damingera嘗試定義認知勞動的主要活動,以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若未加以闡明,此類勞動很容易被視為體力勞動的附帶活動,往往不被紀錄,或僅僅是模糊的「管理」或狹隘的「規劃」。
Damingera從過去質性資料中發現認知勞動的普遍性與性別差異,例如:(1)男女參與差距最⼤的是管理活動。(2)女性更感到須對結果負責。(3)女性時常提醒伴侶完成家務。(4)女性設定清潔標準。(5)女性協調與監督聘請的幫⼿。(6)女性多⼯、時間碎片化與時間壓⼒。(7)女性的休閒時間更常被家務打斷。而這些高認知負荷特徵近年來在心理學、健康障礙研究中被密切討論,影響包括降低意志⼒與⻑期決策能⼒、多⼯嘗試與焦慮、壓⼒及其他健康障礙相關。Damingera認為,我們有理由相信健康、關係滿意度及職業決策都可能受到影響,揭示家務勞動的認知維度極具重要性。
***
在研究樣本上,作者訪談波⼠頓地區35對中產及中上產階級(物質與社會資源理論上能促進其平等理想的實現)夫妻成員的70次個別訪談。所有訪談均於2017年6⽉⾄12⽉期間進⾏。參與者均已婚,年齡介於25⾄50歲,⾄少持有學⼠學位(持平等主義的理想之比例較⾼,學歷女性與「強化⺟職」⾼度相關),並與⼀名或多名五歲以下的孩⼦同住(父母時間壓力最大)(註2,p. 613)。
最終樣本有76%男性與70%女性全職⼯作;12%男性與14%女性兼職;12%男性與16%女性未就業。在研究程序上,作者採同⼀天、分別對每位伴侶進⾏訪談、兩次訪談完成之前避免討論、 60-80分鐘、錄⾳。主要優勢有三:首先,可以從每對夫妻獲得兩份第⼀⼈稱報告,不必依賴⼀方描述雙⽅的認知活動。其次,由於知道另一伴也會受訪,故增加受訪者提供誠實觀點的可能性。最後,針對事件重疊的部份,能直接比較他們對同⼀事件的理解。整理研究程序如下:
- 訪談前,要求參與者獨⽴記錄 24 ⼩時內所做或參與的所有家務決策 ( 女性平均 15 條、男性 10 條 )。
- 詢問每條記錄的觸發原因、考慮過的其他選項、配偶扮演的⾓⾊、該例⼦與家庭中典型事件的比較針對不定期活動回答類似問題。
- 訪談最後討論對家庭中認知勞動理想與實際分⼯的看法。
- 過程中讓受訪者先描述具體事件,再反思「通常」會發⽣什麼事,從決策或結果倒推。如當受訪者提到晚餐決定做義⼤利麵時,作者會追問為什麼是做義大利麵?有查看冰箱食材嗎?考量家庭成員喜好?
作者分析資料包含逐字稿、訪談記錄、訪談後不久撰寫的⺠族誌筆記,以開放編碼方式標出反覆出現的主題、反思、建立初始編碼、二輪審視跑NVivo 分析,再擴展或修改初始編碼。如此反覆幾輪,最後確認了九個認知勞動領域:(1)食物、(2)兒童照顧、(3)後勤/⾏程安排、(4)清潔/洗⾐、(5)財務、(6)社交關係、(7)購物/採購、(8)家庭/⾞輛維護、(9)旅遊/休閒。以及四種認知勞動類型:(1)預期、(2)辨識、(3)決策、(4)監管。並將勞動領域與類型編碼:女性主導、男性主導、共同分擔、未定義。
***
研究發現,在九項勞動領域中,女性主導六項:後勤/⾏程安排、兒童照顧、社交關係、清潔/洗⾐、購物/採購、食物。在四種認知勞動類型裡,女性大多承擔預期和監管。研究結果呈高度性別化分工,男性主導影響力大或陽剛氣質的領域(財務、旅遊/休閒、家庭/⾞輛維護)。在認知勞動方面亦然,隱匿性高、影響力低的預期和監管,很大程度由女性主導。
負責大多隱匿性高的認知勞動的結果是,女性沒有真的做所有事,卻像跟著做了所有事的活動總召。從一開始的投入情境、發想,到列出待辦清單,最後追蹤完成(且達標),沒有一刻真的放下一切不勞動。常見的情況是,一邊煮飯一邊想明天要買什麼、一邊洗衣服一邊看顧孩子,女性經常多工的投入到家庭照顧的情境裡,所以能迅速反應並預期未來事件和需求。然而壞處是,女性的休閒時間經常被打斷、零碎而難以完整或好好投入於自己的愛好中,且難以對他人說明自己的疲勞(可能自己也沒發覺),因為表面上看來,就只是順便多煮一份晚餐、順便看一下孩子,會有多麻煩?有多做什麼體力活動嗎?反之,男性往往被指派明確任務,因為看不到要做什麼、看不到家裡的洗衣粉要沒了、看不到孩子的親師座談與臨時加班撞期,也看不到完成的標準。在先前討論的《第二輪班》裡,我們會看到典型的爭執是丈夫不覺得要做、且標準不用那麼高,認為被妻子指派任務是被限制了自由。
最後作者總結到,女性負擔最⼤的預期與監管,是最隱形、最抽象、最遠離權⼒的部分,同時也指出,時間並非衡量家庭勞動性別不平等的唯⼀或最佳指標。透過本研究與社會學領域對話,主張認知勞動必須被納入考量,才能精確理解家庭內性別不平等的本質與規模。另外亦與心理學研究對話,認為高負荷的認知勞動與與關係衝突、個⼈福祉下降,甚⾄職場成果相關,但有待進⼀步探討。作者透過研究證明,現行常見的量化家庭勞動負擔研究,不適合捕捉認知勞動的差異,也勢必忽略隱性的性別勞動分工。
在《第二輪班》裡,有些丈夫會認為自己的看不到是因為組織力低、能力不如妻子。但事實上,丈夫在職場上能夠發揮其組織力來管理並順利完成任務。是什麼原因讓丈夫回到家下意識地不去投入,反之,是什麼讓妻子下意識地過分投入以致身心俱疲?期待這部份研究可以有更多情動政治的討論,或許我們不再需要就「勞動」切出那麼多維度(體力、情緒、認知),而就完整的一個人,一名勞動者,與其世界來討論他的操煩。
後記
- 這篇文章獨特之處,在於把時間帶進勞動面向的討論,把「勞動」攤展開來:實際上是「某人在勞動」,而非單一事件、單一動作那脫離了脈絡的「勞動本身」,也因此有別於過去量化可見的「勞動」。就這點而言,本研究打破我們對性別不公的陽剛想像,與社會學、性別研究、心理學領域的學者們交織對話。
- 未來有沒有可能測量認知勞動?除了作者提出的腦科學測量,心理學的量表研究(如憂鬱症也有量表)也是可能發展的方向。
- 現代居家科技越來越多(如掃地機器人),體力勞動可能會越來越少、認知勞動會越來越多,更凸顯本研究的重要性。
註
-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599/8560824
- Daminger, A. (2019). The cognitive dimension of household labo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4(4), 609-633.
- Coltrane, Scott. 1996. Family Man: Fatherhood, Housework, and Gender Equalit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llen, Sarah M., and Alan J. Hawkins. 1999. “Maternal Gatekeeping: Mothers’Beliefs and Behaviors That Inhibit Greater Father Involvement in Family Work.”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1(1):199–212.
【延伸閱讀】
《第二輪班》:表層與底層的性別意識形態
《家庭優勢》:文化資本如何在不同場域間轉換?
平等與社會(七):社區照顧的發展與可能(上)
平等與社會(八):社區照顧的發展與可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