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地獄前我想忘記的八十七件事 | (2) 自由
閱讀時間約 1 分鐘
(2)
坐車前往轉運站的路上,我的腸胃似乎還不能適應失去實體血肉組織後只剩下靈體的事實,一股噁心感不斷在我五臟六腑間流竄。那股噁心衝破喉頭的剎那,我撞開車門,雙腳跪著趴在路邊的水溝蓋上嘔吐起來。水溝蓋的正下方是那座著名的女神像。那些她象徵的意義長成茂綠色的藤蔓,已經緊緊勒住她的頸部使她窒息、並繼續吸取她的養分向上生長蔓延。
在一陣溫暖的翻騰後,中午的酸印度咖哩、早上的酸熱奶茶、酸蒜味麵包一起朝那個直指向上的火炬傾倒。茂綠色的火焰吞下這些穢物後向上竄升,幾乎要燒到我伏著的水溝蓋,一股鋒利的寒意刺進我的雙手,徹骨難消。
胃裡的食物都清空了,嘔吐仍沒有終止。我繼續把一些人世間還放不下、已經無關緊要的東西混著胃液吐出來,像是無名指指甲、膝蓋上的髒紅色痂片、死前還想為某些群體發聲的使命感。吐到後來我漸漸察覺物體流動的速度越來越緩慢,時間在一個短暫靜止之後,重力力場扭轉,我的口成為新的重力場中心,而我正隔著水溝蓋,貪婪幸福吸取腳下這個世界的一切。
把整座神像吞下後,我滿足地站起身,伸伸懶腰後縮回車子,砰一聲關上車門。司機終於鬆開剛剛緊壓著喇叭的手、打一個嗝以後,把方向盤轉了180度,往地心的方向駛去。
留言0
查看全部
你可能也想看
Google News 追蹤

這個秋,Chill 嗨嗨!穿搭美美去賞楓,裝備款款去露營⋯⋯你的秋天怎麼過?秋日 To Do List 等你分享!
秋季全站徵文,我們準備了五個創作主題,參賽還有機會獲得「火烤兩用鍋」,一起來看看如何參加吧~

美國總統大選只剩下三天, 我們觀察一整週民調與金融市場的變化(包含賭局), 到本週五下午3:00前為止, 誰是美國總統幾乎大概可以猜到60-70%的機率, 本篇文章就是以大選結局為主軸來討論近期甚至到未來四年美股可能的改變

Faker昨天真的太扯了,中國主播王多多點評的話更是精妙,分享給各位
王多多的點評
「Faker是我們的處境,他是LPL永遠繞不開的一個人和話題,所以我們特別渴望在決賽跟他相遇,去直面我們的處境。
我們曾經稱他為最高的山,最長的河,以為山海就是盡頭,可是Faker用他28歲的年齡...

🔥1600張超大容量 全網cp值最高🔥 6包一箱 懸掛式抽紙 衛生紙 可掛式加量加厚
📌原生木漿,不含螢光劑
📌1袋1600 (單張5層,320抽)
⬇️完整說明網址⬇️
👉https://s.shopee.tw/VlPQuYNmL
#Pp貓 #1600張 #超大容量 #

🔥限時破盤價🔥新升級 強力抗風 黑膠自動傘 24骨 12骨 10骨 遮陽傘 雨傘 自動傘
📌防潑水傘布,雨傘甩乾就可以收
📌防曬係數UPF>=50+,大太陽也不怕被曬
⬇️完整說明網址⬇️
👉https://shope.ee/9pIQ51moaV
#Pp貓 #黑膠自動傘 #自動

❗下殺1元👉濃艾草款/黑色款🔥台灣賣家 純艾草棒 竹炭艾草棒 薰香
📌防治蚊子及小黑蚊的好幫手
📌圖片裡有買家使用效果評價
⬇️完整說明網址⬇️
👉https://shope.ee/30RusCO1sp
#Pp貓 #下殺1元 #台灣賣家 #純艾草棒 #竹炭艾草棒 #薰香 #防蚊

分享老牛與方格子合作的限時優惠!
現在開始到 5/20 ,訂閱股海老牛抱緊股專欄「首次訂閱」只要 1 元!
歡迎各位夥伴去看看!

歡迎各位來到Life Architect.今天我們來看看2月14日至19日的人類圖天象啟示.
由於這段期間的太陽是走到閘門30的位置,對應的易經的離火卦.正如易經中有關離火的現象,是一種向外展示,洋溢着熱情,温暖,光明等能量.閘門30在情緒中心內也是有着類似的表示.
所以,這段時

上週五在方格子的閒聊,有跟大家報告分享台積電的技術面出現非常漂亮的型態,今日就被老巴抬轎,非常開心

今天小聊台積電,今天反彈到季線賣壓好重,然而我這邊覺得是買點不是賣點
今天帶量跳空過7/5日低點433頸線,然後也是廣義的島型缺口,10/11日向下跳空和今日向上跳空成對稱,這個底部好漂亮。

每日前言:
當沖是一條刺激緊張的路。
他可以是一個手遊,每天輸錢就像是剋金;
也可以是一場鬥智的博弈運動,像是德州撲克;
也可以是一個投票機,是一個選美比賽,你能理解別人的想法或是能抓到後面那一隻承接的老鼠,你就能獲利。
───
🖤然而當沖也可以毀了一個人,可以奪去你的身心靈健康,全因心態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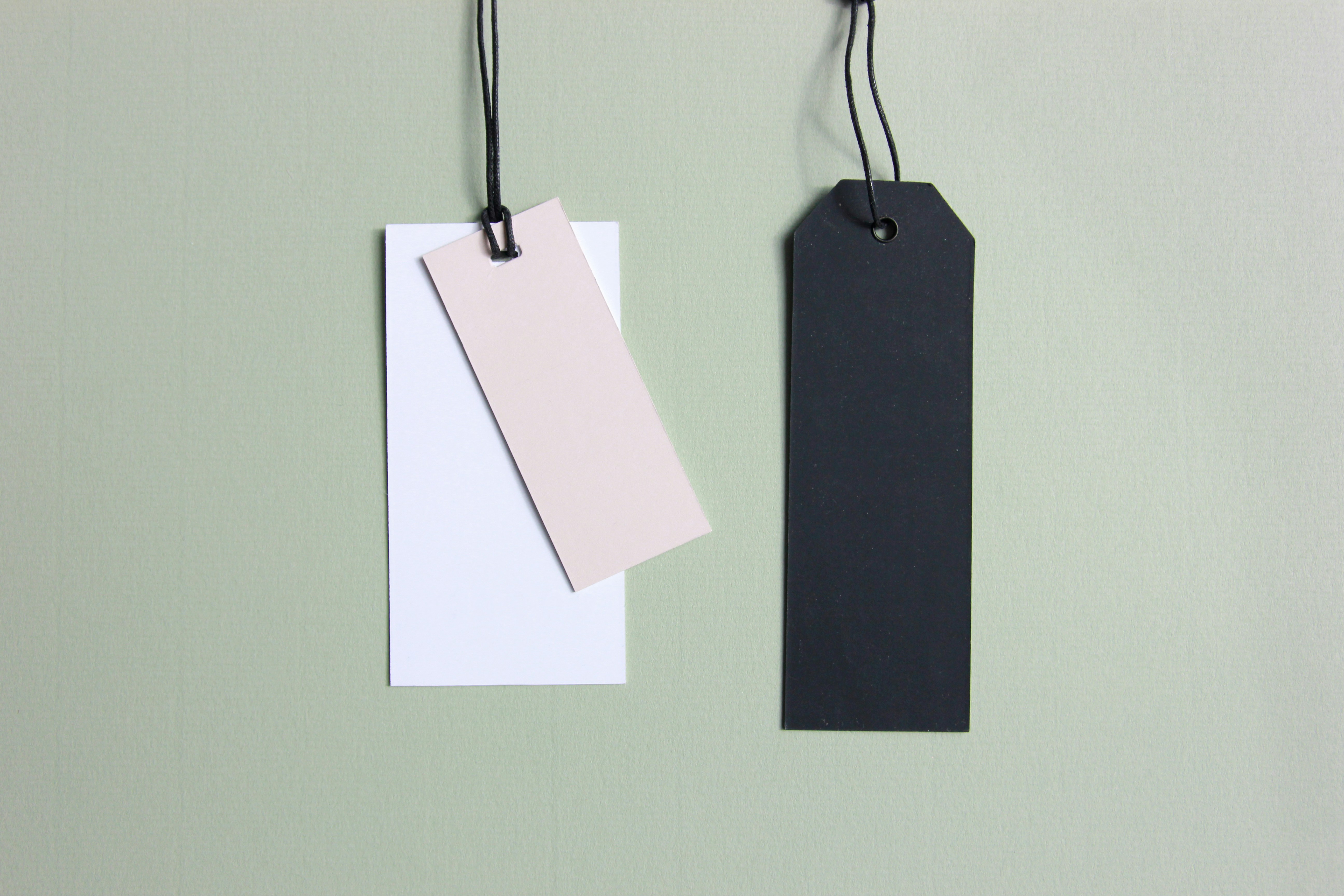
過載的疲倦與咖啡因把時間扭曲成一捲厚實的雪茄,我漂浮在裊裊上升的煙圈間,痛苦地亢奮著。

賞蟲・拍照・記錄~並不是看到昆蟲都要抓!
一個柵欄,一張告示,大家知道這裡是哪裡嗎?
看到大屯姬深山鍬形蟲非常開心,雖然只發現一隻,但也按了不少快門,可以帶著微笑心情結束今天訪蟲行程!

這個秋,Chill 嗨嗨!穿搭美美去賞楓,裝備款款去露營⋯⋯你的秋天怎麼過?秋日 To Do List 等你分享!
秋季全站徵文,我們準備了五個創作主題,參賽還有機會獲得「火烤兩用鍋」,一起來看看如何參加吧~

美國總統大選只剩下三天, 我們觀察一整週民調與金融市場的變化(包含賭局), 到本週五下午3:00前為止, 誰是美國總統幾乎大概可以猜到60-70%的機率, 本篇文章就是以大選結局為主軸來討論近期甚至到未來四年美股可能的改變

Faker昨天真的太扯了,中國主播王多多點評的話更是精妙,分享給各位
王多多的點評
「Faker是我們的處境,他是LPL永遠繞不開的一個人和話題,所以我們特別渴望在決賽跟他相遇,去直面我們的處境。
我們曾經稱他為最高的山,最長的河,以為山海就是盡頭,可是Faker用他28歲的年齡...

🔥1600張超大容量 全網cp值最高🔥 6包一箱 懸掛式抽紙 衛生紙 可掛式加量加厚
📌原生木漿,不含螢光劑
📌1袋1600 (單張5層,320抽)
⬇️完整說明網址⬇️
👉https://s.shopee.tw/VlPQuYNmL
#Pp貓 #1600張 #超大容量 #

🔥限時破盤價🔥新升級 強力抗風 黑膠自動傘 24骨 12骨 10骨 遮陽傘 雨傘 自動傘
📌防潑水傘布,雨傘甩乾就可以收
📌防曬係數UPF>=50+,大太陽也不怕被曬
⬇️完整說明網址⬇️
👉https://shope.ee/9pIQ51moaV
#Pp貓 #黑膠自動傘 #自動

❗下殺1元👉濃艾草款/黑色款🔥台灣賣家 純艾草棒 竹炭艾草棒 薰香
📌防治蚊子及小黑蚊的好幫手
📌圖片裡有買家使用效果評價
⬇️完整說明網址⬇️
👉https://shope.ee/30RusCO1sp
#Pp貓 #下殺1元 #台灣賣家 #純艾草棒 #竹炭艾草棒 #薰香 #防蚊

分享老牛與方格子合作的限時優惠!
現在開始到 5/20 ,訂閱股海老牛抱緊股專欄「首次訂閱」只要 1 元!
歡迎各位夥伴去看看!

歡迎各位來到Life Architect.今天我們來看看2月14日至19日的人類圖天象啟示.
由於這段期間的太陽是走到閘門30的位置,對應的易經的離火卦.正如易經中有關離火的現象,是一種向外展示,洋溢着熱情,温暖,光明等能量.閘門30在情緒中心內也是有着類似的表示.
所以,這段時

上週五在方格子的閒聊,有跟大家報告分享台積電的技術面出現非常漂亮的型態,今日就被老巴抬轎,非常開心

今天小聊台積電,今天反彈到季線賣壓好重,然而我這邊覺得是買點不是賣點
今天帶量跳空過7/5日低點433頸線,然後也是廣義的島型缺口,10/11日向下跳空和今日向上跳空成對稱,這個底部好漂亮。

每日前言:
當沖是一條刺激緊張的路。
他可以是一個手遊,每天輸錢就像是剋金;
也可以是一場鬥智的博弈運動,像是德州撲克;
也可以是一個投票機,是一個選美比賽,你能理解別人的想法或是能抓到後面那一隻承接的老鼠,你就能獲利。
───
🖤然而當沖也可以毀了一個人,可以奪去你的身心靈健康,全因心態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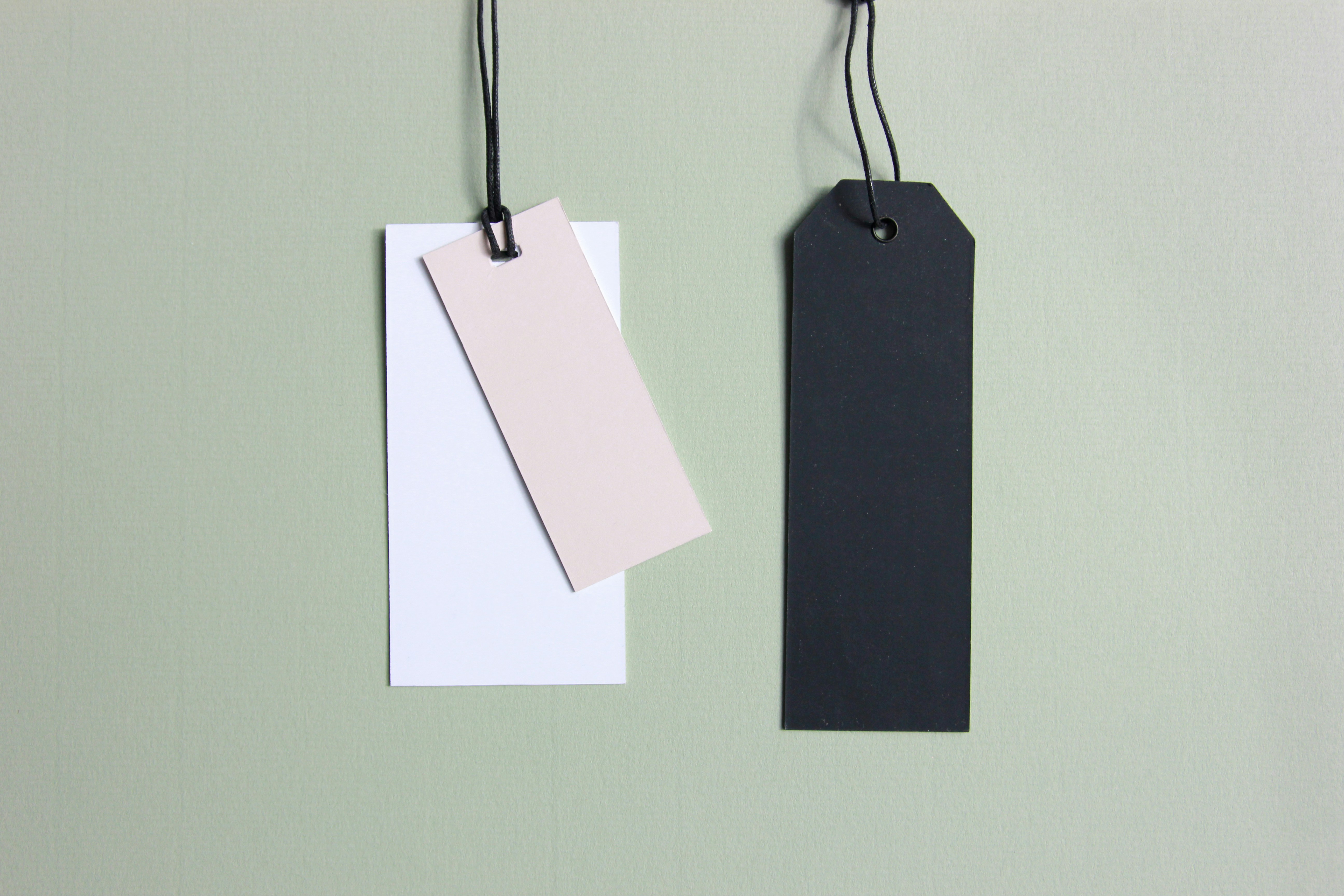
過載的疲倦與咖啡因把時間扭曲成一捲厚實的雪茄,我漂浮在裊裊上升的煙圈間,痛苦地亢奮著。

賞蟲・拍照・記錄~並不是看到昆蟲都要抓!
一個柵欄,一張告示,大家知道這裡是哪裡嗎?
看到大屯姬深山鍬形蟲非常開心,雖然只發現一隻,但也按了不少快門,可以帶著微笑心情結束今天訪蟲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