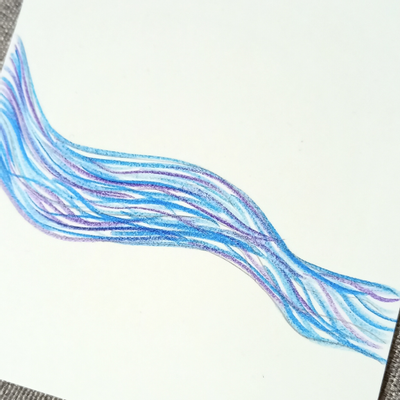這房子的隔音很差,是她當初搬進來時沒有預料到的。她不懂建築,不太明白這是因為牆壁的材質、開窗的角度、或是房與房之間的格局使然。只知道,廚房流理台右手邊那面牆的另一邊是隔壁鄰居的浴室,因為嘩啦啦的水聲常常穿牆而過;書房的樓上應該住的是個男生小屁孩,因為總有各種玩具的乒乓聲響;還有不知到底是哪一樓哪一戶住了個應該是精神有問題的年輕人,時而大吼大叫咕噥些沒有人聽得懂的字句。而每次在自己的客廳總能聽到從陽台傳來隔壁客廳從他們陽台傳出來的聲音,那是一對男女,三不五時的吵架,偶爾又逗嘴,又或者,有時上演限制級的愛情動作片。
她因此失去了高聲唱歌的勇氣。光是想做個發聲練習,她都覺得自己的胸腔和喉嚨被一種緊張感限制住,那個聲音能量都還沒出盡,甚至還不到50%,她便擔心左右鄰居會不會迅即站在她家門外進行人肉搜索。但唱歌啊,唱歌就是要盡情盡興啊,她覺得悶,明明一個精神病患都可以這麼勇敢,不管別人懂不懂的大聲吶喊,為什麼自己就只能這麼峱在屋子裡,用喉音清唱。她想起了在剛過去的春節假期中,這個住宅大樓區中的當然不知道是哪一戶的某一戶,還甚至用麥克風廣播似的唱起了卡拉OK,一整個下午歪七扭八的歌聲就這樣迴盪在整個中庭,理所當然。
「阿阿阿阿阿」,她試著做發聲練習,卻還是無法不緊張地限制了自己的共鳴。住在這個隔音甚差的屋子裡,她感覺自己像一個透過心電感應聽見別人心聲的怪胎,為了怕別人也聽見自己的心聲而噤聲。牆太薄,那些穿牆而來的聲音,逼得她小心謹慎地築了一道厚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