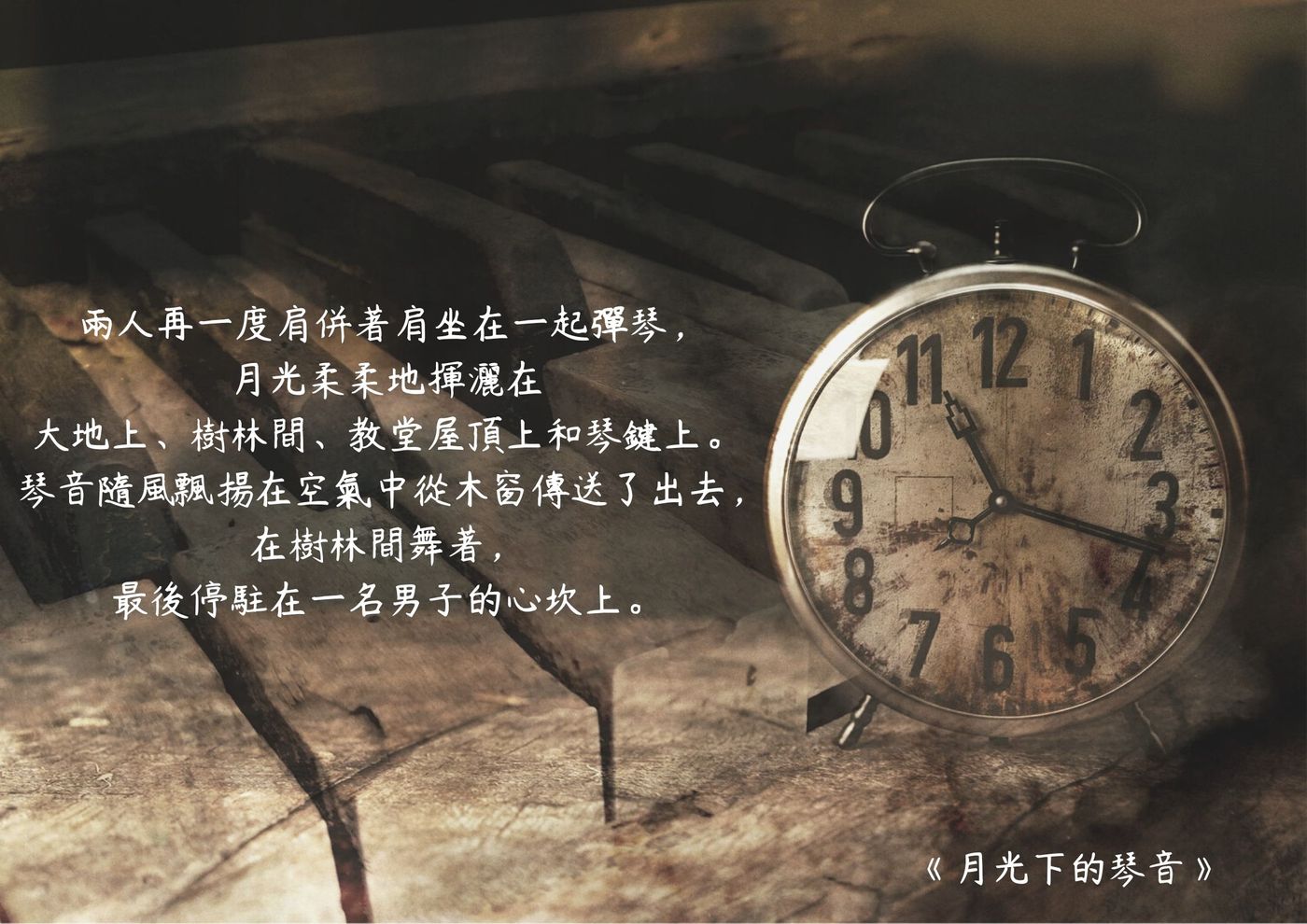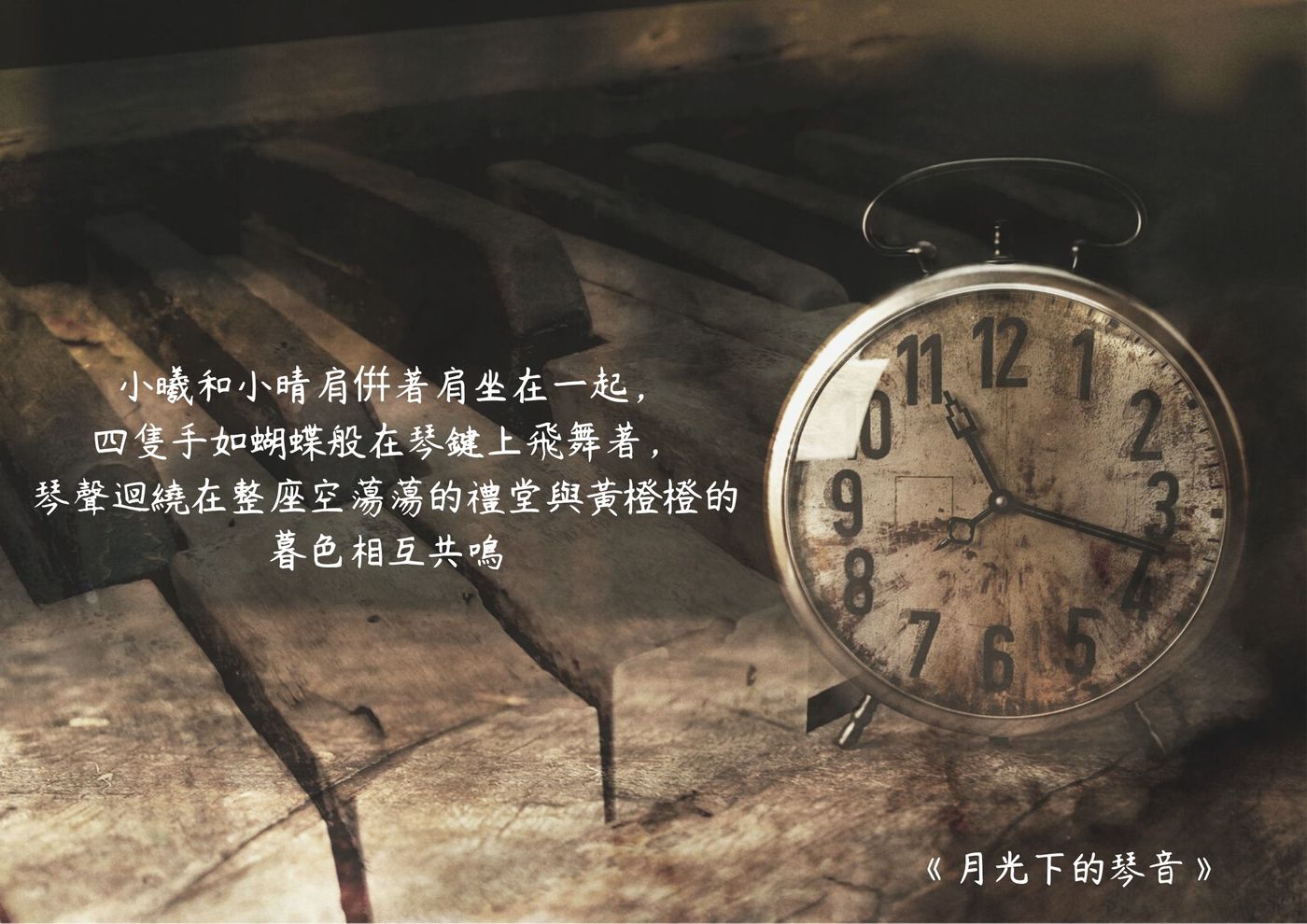三
谢福恩是收到父亲病重的消息匆匆回国,但最终还是没能赶上看上父亲最后一眼。家族等到他回来后举行了葬礼,葬礼隆重,来的人很多。在送葬的人群里,凯蒂.摩尔小姐格外多注视了谢福恩几眼。凯蒂小姐的父亲老摩尔与老谢菲尔德是几十年的生意伙伴,凯蒂从小就从各种闲聊中听说了许多关于谢福恩的不同常人的议论。
按照老谢菲尔德的遗嘱,把贸易公司、保险公司的股份,还有纽约的几处不动产分给了谢福恩的两个兄弟,而把康涅狄格州新港镇郊外的千亩庄园留给了谢福恩。
庄园有几百英亩的葡萄园和苹果园,有大型的牛舍和养鸡场,还有更大的一片未开垦的茂密树林。有些清晨,树林里的野鹿偶尔会跑到果园里来,偷吃挂在树上的果实。一条小溪缓缓流过,横贯整个庄园,河水清澈得能看到河床里的每一块卵石、每一条鱼虾,夏天的时候,整个庄园仿佛图画般的美丽怡人。
凯蒂.摩尔小姐打心底里喜欢这个庄园里的一切,这个夏天,谢福恩陪伴她游览了庄园里许多有趣的地方,讲述了许多关于他自己和中国的有趣见闻。恰好凯蒂最要好的表姐嫁给了谢福恩的哥哥迈克尔,第二年夏天,当迈克尔一家回庄园避暑的时候,邀请了凯蒂一块同行。于是,又一整个夏天,谢福恩陪伴凯蒂游览了庄园里和庄园外更多有趣的地方,讲述了更多关于他自己和中国的有趣见闻。
庄园的房子很大,宽敞的客厅里有一架老式的立式钢琴,夏天的傍晚,谢福恩偶尔会坐在钢琴前,弹上几首舒缓的肖邦或者莫扎特,凯蒂很享受谢福恩的琴声。一天傍晚,谢福恩又坐到了钢琴前,窗外是夏夜的微风安静的掠过草坪和花园。谢福恩只弹了一小段就停了下来,凯蒂从没听到谢福恩弹过这一段,但这却是她听到谢福恩为她弹过的最美的一段。
“这是什么曲子?”她问。
“我也不知道,你的美丽占据着我的脑海,当我把手放在琴键上,就有了这些美妙的音符。”谢福恩诚实的回答。
这个夏天的夜晚,凯蒂主动拥吻了谢福恩。再后来,秋天的时候,谢福恩和凯蒂在新港镇的教堂举行了婚礼。
赵静安的到来给谢福恩的家庭带来过一阵惊奇,人们第一次见到这个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的小家伙,而且都对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感到由衷的高兴。很快,大家就习惯了看到小赵静安在庄园里,到处的跑来跑去。
谢福恩和凯蒂结婚后,赵静安就不再到镇上的学校去了。谢福恩请了个住家的家庭教师,露西小姐。谢福恩经常到镇上和附近的教区去处理教会的事务,他不在的时候,露西可以和凯蒂做个伴儿。
小溪里清澈的流水冻上了又融化,果园里的果树开花、结果又再开花,庄园里的日子就象没有风的湖面,安静而平稳。这一年,赵静安十三岁了,在庄园里也快活的生活了三年。三年里小赵静安长大了许多,顿顿吃肉已不再是他最大的梦想,遥远的中国也不大让他想念。他现在想的是,希望每天有多些机会和他美丽的教母呆在一起。
从老屋步行十五分钟,在树林里有一个不太大的湖,夏天是划船和游泳的好 去处。凯蒂从纽约买了两套时髦的泳衣,送给了露西小姐一套。露西相貌普通,上帝没有给予她象凯蒂那样的美貌,但她知道的很多,文学、音乐、绘画,还有游泳。夏天的时候,凯蒂带着赵静安跟着露西学游泳。
去年一整个夏天,凯蒂午睡醒来,如果丈夫不在庄园里,她就跟着露西学上一个小时的钢琴或者绘画,然后看看太阳不那么灼人了,就拉上露西和赵静安,到湖边消磨掉整个下午的时光。赵静安游泳学得很快,一个夏天就学会了,而凯蒂则始终不得要领,游起来像只受了惊的鸭子一样,在浅水里扑腾来扑腾去,但她并不在意,她更喜欢在清澈的湖水里泡着,或者穿着泳衣坐在岸边的树荫下,让掠过湖面的微风轻轻吹拂她的身体。
现在,树上的知了又开始呱噪了,树叶由嫩绿变成了浓荫,又一年的夏天已经来到。
凯蒂在她的画板上添上了最后几笔油彩,说:“露西,你过来帮我看看画得怎样? ”
“您画得真好,夫人,您对色彩的把握真是妙极了。我觉得都可以送到纽约的画廊去展览了。”
“得了吧,你这个老师别挖苦我了。”凯蒂不相信露西说的,但心里还是高兴的,“杉尼,你的画怎么样了?”
赵静安现在叫杉尼.赵,名字中有个赵字,那是他的教父希望他不要忘了自己的家乡,还有生身的父母。
“我觉得我画不好,我想留到下回再画了。”赵静安不喜欢画画,今天本该画的是一盘静物水果,但他却不由自主的画起了坐在他对面的美丽的教母。
“我看看。”凯蒂走到赵静安的画板前,“你画的这是什么?一个金发的女人吗?”
“是的,我想画一幅画,我想把你画在画上。”
“天啊!你确实画得很糟很糟,我可不想变成你画的这个样子。好了,孩子,别管那画了,我们该走了,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去拿泳裤。”中午在午饭的饭桌上,凯蒂提议去游今年夏天的第一次泳,回到房间,赵静安很快就把他去年的泳裤从柜子里给翻了出来。
“去吧。我的梳妆台上有了包,我把泳衣、毛巾都放在包里了,你一块帮我拿下来吧。”
“好的。” 赵静安兴高采烈的朝楼上跑了去。
“露西,你还是决定不和我们一起去吗?”凯蒂转身问露西。
露西红着脸,说:“我昨天答应杰克了,说好今天给他上一次生词课。要不, 我去告诉杰克,说生词课改天,然后我还是和你们一起去游泳。”
杰克是庄园养牛场新来的雇工,有着一头金色的短发和牛仔般的体魄。杰克每天驾着马车给老屋的厨房送来新鲜的牛奶, 一天, 杰克在厨房里遇到了露西, 两人对视了两秒。杰克微笑着自我介绍说,我是新来的雇工,我叫杰克。露西就说,我叫露西,是家庭教师。又一次在路上,杰克遇到了露西,杰克说,露西小姐让我送送你吧。露西说,好吧。于是,两人就坐在杰克的马车上,肩并着肩。杰克说,我没上过学,但喜欢看书,不过经常会碰到些不大明白的字眼,以后我可以向你请教吗?露西说,当然,说说看,你都喜欢看些什么书。打那以后,杰克就经常夹着本畅销小说,或者笑话全集,来找露西请教其中的生僻词句了。
“你还是和杰克继续你们的生词课吧。”凯蒂暧昧的笑着对露西说,“杰克确实是个不错的棒小伙。”
露西的脸更红了。
在二楼教父和教母的卧室,赵静安找到了凯蒂让他拿的那个手提包,但他没有马上离开。他看到梳妆台上有两个粉红色的扎头发用的发圈,发圈上还缠绕着凯蒂的几根金色的长发。他拿起发圈,隐隐感觉到发圈上有股美人樱一般的淡淡清香。他把发圈送到鼻子跟前轻轻的闻了起来。
那张巨大的铜床就静静的躺在卧房的另一侧,赵静安走过去,贴着床,把脸埋进教母松软的枕头里,枕头上浓郁的美人樱的迷香激动得小赵静安的身体一阵颤抖。
通往湖畔的土路干燥而结实,夏天刚到,走这条路的人还少,路上长出了许多新鲜的杂草。凯蒂牵着赵静安的手,像一大一小两只快活的糜鹿。
“你说你昨天真的看到露西小姐和杰克 ,一起去了牛棚后面的草料仓了? ”
“是的,我原本打算找杰克带我骑马来着。”
“后来呢,你又看到了什么?”
“没什么了,我想他们又要上他们乏味的生词课了,就到果园里找别的小孩玩去了。”
凯蒂开心的咯咯笑起来,“你真以为露西小姐和杰克只是在上生词课吗?”
“那还有什么?”赵静安装作不解的问。
凯蒂笑得更开心了,“等你长大点再告诉你吧。”
凯蒂不知道,其实她的教子已经长得足够大了。好几个月前,赵静安就发现自己的乳头下面长起了两个小小的肿块,用手压下去还隐隐涨痛。更大的发现是, 他看到自己的小小的男根的四周,竟然冒出了一圈淡淡的茸毛。茸毛长势很快,很快就长成了一把乱槽糟的黑色杂草。
昨天在草料仓,赵静安其实看到了很多,但他知道,那种事是不能说的。草料仓的屋后有一把长梯,把梯子搭在墙上可以爬上屋顶。赵静安爬上去过,知道在屋顶上有一个喜鹊的窝,还知道揭开喜鹊窝旁边的一小块瓦片,就能看到屋顶下的一切。他想好了个恶作剧,拿了一把土块,打算从屋顶上砸到杰克和露西小姐的头上,还不让他们知道是谁干的。但当他爬上屋顶,揭开瓦片,看到杰克和露西小姐已经搂抱着,在草堆上激烈的翻滚。
杰克和露西小姐急促的互相吻着,双手在对方身上胡乱的抓挠,仿佛对方身体里藏着某件自己渴望得太久的宝物似的。露西小姐的肩膀从碎花短袖的连衣裙里裸露出来,她一边喘息着迎奉着杰克在她脖子上、肩膀上的亲吻和噬咬, 一边伸手反复抠抓杰克腰间的皮带。杰克喘息着直起腰,飞快的解开皮带。当他两腿间那象木薯一样粗大硕长的家伙从裤子里弹出来时,赵静安简直惊呆了,他很惊讶这么粗大的物件平常是怎么藏在一条紧绷绷的牛仔裤里的。但还没等他看清楚细节,杰克已从露西小姐的连衣裙下一把将她的内裤扒了下来,然后俯下身,把那根大木薯彻底埋在了露西小姐敞开来的两腿之间。小赵静安更惊讶了,露西小姐的两腿间怎么能容纳这么硕大的一个玩意儿?赵静安伸长脖子,竭力想看清楚发生的一切,可是杰克两片不停耸动的大白屁股挡住了他的视线。随着杰克的两片大白屁股越来越急促的耸动,露西小姐的喉咙里,也越来越急促的发出一种类似于母兽般喘不过气似的呜鸣声。小赵静安趴在屋顶上,屏住呼吸,瞪大双眼,眼前的一切让他既紧张又兴奋。
比起露西小姐,平日里赵静安更喜欢他的教母凯蒂。不单是因为凯蒂有着和那些从纽约寄来的时装杂志上的模特一样漂亮的脸蛋,也不仅是因为教母身上那隐隐约约的沁人的芳香,更让赵静安着迷的是教母胸前一对圆润饱满的乳房。赵静安总是格外喜欢那些胸前鼓涨的女人,在他的记忆里,直到六岁的时候,每夜都还要抓着母亲的乳头,才能停止哭闹安静入睡。邻家谁有喂奶的婆娘,他也总要跑去看,因为他是个孩子,大人们也不避着他,趁着奶孩子的时候,他可以把女人的乳房看个够。
凯蒂来到庄园后,每次和凯蒂在一起,赵静安很难不让自己不去多看几眼凯蒂胸前那对浑圆高耸的凸起。偶尔有机会得到凯蒂的拥抱,他总要把脸整个埋进教母的怀里,尽情的摄取那隔着衣料传来的温软和芳香,直到凯蒂咯咯笑着把他推开。
不过也就仅限于此了,虽然对教母包裹在层层衣饰下的身体充满了好奇,但赵静安知道,这样的念头在大人们的世界是多么的可耻和不可饶恕。他知道,如果他流露出丁点这样的念头,那等待着他的将是多么可怕的惩罚。小赵静安为自己的念头感到羞愧难当恐惧万分,而同时,好奇与渴望又在他的身体里一天天的膨胀。
凯蒂领着小赵静安来到夏日的湖畔,湖边有一间小屋,平日用来存放渔网、船桨这些东西。凯蒂把赵静安留在屋外,她进到屋里更换她的新式泳装,嘴里有一句没一句的哼着一支欢快的曲子。整个湖区安静极了,斑驳的阳光透过树叶间的缝隙,安静的跌落到碧绿的草地上,只有凯蒂的哼唱,和着微风,在树林间荡漾。
小树林里,赵静安很快换好了自己的泳裤,他望向小屋,心砰砰的跳。只犹豫了一小会儿,他就决定了要干的事情。小屋的四面都是用一层厚木板钉成,经年累月,木板的拼接处裂开来一条条窄窄的缝隙。小赵静安蹑到木屋的一侧,从一条裂缝处往小木屋里张望。
凯蒂在屋里的另一侧,背对着,正在解开紧身的胸衣,嘴里还是有调没调的哼着那支欢快而单调的曲子。虽然光线黯淡,又只是看到背影,但当胸衣解开那一刻,还是能感觉到凯蒂丰满的双乳充满弹性的跳了出来。凯蒂接着弯腰褪下贴身的内裤,露出了整个浑圆翘立的臀部,然后直起腰,双手伸到脑后整理散开来的长发。赵静安的心狂跳不止,他使劲咽了咽口水,心里期盼着美丽的教母转过身来。
没等凯蒂换好泳装,赵静安已逃离了木屋。他跳进湖里一口气连扎了几个猛子,然后从水里冒出头来,喘着气抹着脸上的水珠,假装在水里已游了许久的样子。
当凯蒂从木屋里走出来,赵静安的小心脏又是一阵狂跳。一件黑色的连体泳衣紧紧的绷在凯蒂的身上,刚才木屋内光线黯淡,现在身体的每一处凹凸都清晰的展露在阳光之下。
这件泳衣是1883年时装杂志上最时髦的一种款式,昨天刚从纽约最时髦的时装商店寄来。比起去年的款式,不单上身露出了整个胳膊,腋窝也露在了泳衣的外头,肩膀上只剩下两条类似贴身背心那样的窄窄布条。整套泳装本来还包括一条长及膝盖的裙子、一双类似芭蕾舞鞋的系带拖鞋,和一顶花哨的泳帽。在 1883年,即使把所有的这些全都穿在身上,出现在纽约的公共泳池里,也还是件让许多人侧目的事情。而现在,凯蒂连外头的裙子也去掉了,露出了整个下半身完美的曲线和裸露的大腿。
“杉尼,你过来扶我一下。” 湖水清澈见底,凯蒂深一脚浅一脚踩着脚底的卵石,踉跄的朝赵静安这边走来。
“好的,我这就过来。” 赵静安跑过去,扶住美丽教母的一只手。
湖水没到了凯蒂的腰间,清凉的水流从两腿间滑过,凯蒂象个孩子似的咯咯咯的笑起来。
湖水快到齐胸深的地方了。“好了,杉尼,别去太深的地方了,你托住我,我看我还能不能想起露西去年教我的那些 。”
赵静安小心翼翼的在水里用手拖住凯蒂的小腹,凯蒂使劲抬起臀部和大腿,极力想在水里将身体摆成水平的姿势。刚开始学的时候,在一旁帮助凯蒂的是露西小姐,赵静安只能在一旁看着,现在露西小姐没来,偌大的湖区只有他和凯蒂两人。
教母近乎赤裸的身体紧挨着身边,涨满的乳沟在领口处时隐时现,赵静安感觉教母身上的芳香越来越浓郁了,他看着、呼吸着、感受着教母的身体传来的一切动人的信息,感觉心跳随时会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凯蒂站在水里又咯咯的笑起来,“我怎么觉得老是浮不起来呀!”
“你把腿再抬高点就能浮起来了,我会托住你,不会让你沉下去。”
“好吧,我再试试。”
小赵静安感到全身的血液在快速的流动,脑际一片空白,只剩下恨不得一把把教母紧紧抱住的冲动。但另一股力量似乎更加强大,牢牢的控制住了他,使他的双手除了老老实实的停留在教母柔软的腹部外,不敢再挪向别处。而紧绷的泳裤里,尽管浸在清凉的湖水里,却早已肿胀到躁动全身了。
不会水的人,总是对在水里双脚够不着地充满了恐惧,凯蒂也是这样,在她频繁的抬腿打水和落下恢复站立的过程中,紧靠赵静安一侧的大腿,反复刮蹭着他涨到几乎就要爆裂的小家伙上。美丽教母的大腿在赵静安小棒棒上的每一次触碰和离去,都让他一次次的冲向兴奋的顶点,或者跌落企盼的深渊。但美丽的教母丝毫没有察觉到她13岁的教子此刻心中的汹涌波澜,依旧专注于她笨拙的泳姿。
“啊,杉尼,咱们再来一次,这一次我一定要在水里浮起来,你可要把我托住了。”
这次凯蒂使出全身力气,上身猛的向水里扑去,两腿同时使劲的向后快速的抬起,身体的重心全部落到了托在她腰间的赵静安的两只手上。凯蒂左侧的大腿又一次重重的撞击了小赵静安直挺挺的小家伙,他只觉得全身的肌肉一阵失去了控制的猛烈紧缩,眼前一片晕眩,一股热流喷射了出来。他本能的伸手去抓自己的家伙,小棒棒不由自主的猛跳几下,第二股、第三股热流喷射了出来。随之而来的极度畅快的感觉,从脊椎末端顷刻传遍了全身,仿佛将他一下拽入了天国。
凯蒂的身体突然失去支撑,快速向水里沉去,她在水里一阵乱抓,搂住了身旁的赵静安。赵静安双脚站立不住,随着凯蒂一道向水里沉去。幸好,水不深, 猛呛了几口后,两人都很快从水里站了起来。
“哈哈哈哈,是不是我刚才踢腿太使劲了。” 缓过神来的凯蒂,又开心的咯咯咯的笑了起来。赵静安鼻子进了水,咳得鼻涕眼泪直流。
“啊,可怜的衫尼,别咳了,是教母的不好,对不起,宝贝儿!” 齐胸深的水里,凯蒂伸开双臂把赵静安揽入怀里。隔着薄薄的泳衣,赵静安紧紧抱住了他美丽的教母,他把头依偎在教母的胸脯上,恨不得就这样死去。不知是因为幸福还是因为痛苦,他的眼泪流得更加的汹涌了。
小赵静安恍恍惚惚的度过了这一天余下的时间,直到晚上和教父教母道过晚安,回到自己的卧房,躺倒在自己的小床上。黑暗中,教母迷人的身影在脑海里漂浮,胯间的小家伙又不由自主的挺起来。他从枕头下摸出两个他在凯蒂的梳妆台上偷来的发圈,发圈上淡淡的遗香让他头晕目眩。他把发圈套在滚烫的小棒棒上,顺着那又酥又麻的快感的指引,紧紧握住,一上一下的开始了套弄。最后,象下午发生过的那样,全身的肌肉再次失去控制的一阵阵紧缩,仿佛岩浆爆裂一般,棒棒猛跳几下,将一股股热流射向了空中。
在这天之前,赵静安还从未有过如此体验,下午在水中的那次,他还以为是小便失去了控制,羞愧得无以复加。现在他爬起来,点上蜡烛,看到床单上几处乳白色的鼻涕一样的东西。他用手指挑起一些,凑到鼻子跟前,是一股淡淡的草根一样的草腥味。虽然弄脏了床单,但“鼻涕”从棒棒喷射出来时的快感是如此的猛烈,小赵静安从此迷恋上了这种异常刺激的游戏。
就这样,小赵静安完成了他成长中的一步。渴望、焦虑、恐惧互相掺杂,在弱小的身体里激烈的冲撞。他变得象一只长鼻子小狗一样,一边掩饰着内心的惊恐,一边敏感的四下搜寻着那迷人的美人樱气味的痕迹。
除了那两个藏在枕头下的发圈,有几次,他甚至偷偷取下凉晒在后院里的教母的胸衣,回到自己的房间,将芳香的胸衣捂在脸上,完成了几次让他颤栗不止的高潮体验。然后在没被发觉之前,把胸衣又悄悄放了回去。
他甚至在湖边小屋的墙上钻了个不大容易让人察觉的洞眼,在洞眼外头再掩上一块木板。这个夏天,后来的每次游泳,露西小姐也一块去了,让他失去了在水里独自拥抱教母的机会,但挪开那块木板,他一次次窥视到了教母和露西小姐更衣的过程。每次小赵静安都要拼命压抑狂跳不止的心跳,每次看到女人们一丝不挂的裸体,都让他感到既兴奋好奇又不知所以。
还有几次,他甚至大胆到在凯蒂一个人午睡时,偷偷溜进了凯蒂的卧房。他站在教母的床前,偷偷的看着熟睡的教母的美丽的脸庞,心中痛苦到几乎要哭出声来。
终于有一次,凯蒂随谢福恩到镇上去了,临时决定第二天才回来。深夜,赵静安趴在窗台上,仰望着满天的星斗,楼里所有的人都入睡了,只有夏夜的虫鸣和夜风摇曳树梢的沙沙声。他在床上辗转反侧,知道今夜只有一个办法才能让他消除心中的焦虑。
赵静安从窗台上下来,赤着脚,穿过漆黑的走廊,悄悄闪进教父和教母的卧房。卧房很大,微风撩动白色的落地窗帘,蓝色的月光洒落一地。那张巨大的铜床静静的横亘在卧室的一侧,微光中,闪烁着古铜器特有的温暖光泽。
这张巨大的铜床比普通双人床的两倍还大,球型的爪脚, " C" 型的曲线,通体精致的叶蔓状纹饰,据说来自远古欧洲的某个王室,是老谢菲尔德四十年前建造这栋房子时,用半船刚从中国运来的新鲜茶叶从一个古董商人手里换了回来。
小赵静安不了解这些,他只知道每夜躺在这张床上的是他美丽的教母。此刻,他战战兢兢的俯卧在松软的床垫上,感觉整个身体都坠入了教母迷人体香的江洋大海之中。他感觉一股股热流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拽住他的身体下沉、再下沉。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本能的去抓救生圈一样,他本能的把手朝裆间伸了过去,把那胀热之处死死的握住。巨大的惊恐交织着同样巨大的负罪感,交织着教母赤裸的迷人幻影,顷刻间,将他送上了极乐的颠峰。
这一夜,小赵静安居然在大铜床上安然的睡着了,睡梦中没有了焦虑和恐惧,快乐和平静甚至挂上了他的嘴角。直到晨曦微露,几只早起的小鸟在窗外枝头嬉戏, 才将他早早叫醒。很幸运,佣人们还没有醒来,赵静安整理好一切,悄悄溜回了自己房间。
从此之后,小赵静安越来越难以控制自己,别的方式已无法带给他足够的快感。每天,他都不可救药的想着如何能避开屋子里的人,独自爬上那张大铜床上“再来一次”。
这样的冲动强烈到有几次晚餐时,他借口离开了餐桌,然后偷偷的溜进教母的卧房,爬上大铜床快速的完成了高潮,然后捂着弄湿了的裤子,回到餐桌旁继续吃他的晚餐。小赵静安知道,再这样下去,很快就会被人发现,但他毫无办法,绝望的等待着末日的到来。
但是,命运再一次改变了这个懵懂少年的人生轨迹。教会在山东的一所学校的校长患了重病,必须回国治疗,谢福恩答应去短期接替半年的时间,等待教会再派遣更合适的长期人选。
半年的时间并不太长,旅途却是如此的遥远、劳顿,谢福恩说服凯蒂在家等他回来。一天清晨,谢福恩带着穿戴整齐的赵静安和少量的行李,坐上了杰克的马车。
谢福恩和赵静安回过头来,向站在老屋门前的凯蒂和露西小姐挥手告别。他们都同时看到了老屋背后的天空上那几抹瑰丽的朝霞,金色的霞光映射到树林、草坪、屋顶和凯蒂美丽的脸颊上,显得世上的一切是那么的美好、安详,没有人预感这一回头竟是永远的绝别。
【 2 】
关于赵新民父亲和他爷爷奶奶辈的故事,大多数都是我编的,说完全瞎编也不尽然,应该说叫推测。
我认识赵新民是通过一个叫做知乎的网站,现在这个网站也还健在,也还是一群小众的人群在上面聚集,年轻的知识分子们。什么是知识分子?我理解大概就是知识的生物载体吧。我评价自己也算勉强掌握了一些知识,虽然已不年轻,但偶尔也在知乎上查阅些偏专业类的信息。有一次在知乎上看到一则广告,说要招募5个45岁以上的人参加一项抗衰老的实验,方法是基因干预,用一种对人体无害的病毒,携带基因片段进入人体,然后释放基因片段,启动化学反应,把染色体的端粒拉长,人就返老还童了。
染色体端粒的磨损是衰老的原因,这在中学生物课本里就有,所以我对这则招募广告的实验逻辑,选择了毫不怀疑的相信。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毫不犹豫的选择知识指引的方向。
用基因干预的方法拉长端粒,这个技术现在很稀松平常了,有钱人隔三差五就能打一针,拉一拉,但那时候还是个非常前沿的技术。我只在新闻里看到过,一家美国公司刚刚获准在哥伦比亚开始人体实验,因为美国还不合法,哥伦比亚可以。我很好奇这些奇幻的科学技术,更好奇的是这则广告说,招募的被试要长住南宁,实验是在南宁做。南宁是我居住的城市,是个亚热带的边陲小城,这里的人们只会种点甘蔗用来榨糖,或者从越南走私大米和冻肉,通过勾结高速公路上的检查员,贩卖到全国各地。南宁怎么可能有最前沿的基因技术呢?
我决定去会会发出这则广告的人,一是我怕死,白头发越来越多了,如果能让衰老的时钟往回拨拨,谁不愿意呢?二是我怕穷,老婆一直想换大一点的房子,我也很努力的去创业去赚钱,但创业创一个亏一个,眼看着就快年过半百,未富先老。老婆每每说哪里哪里的房价又涨了多少多少,真后悔当初没有咬咬牙去交了首付,我总回嘴说高房价是向老百姓征的重税,让老百姓生而为人的同时,就注定了终身为奴。老百姓不得不到劳动力市场上去出卖自己的体力和时间,乞讨着换来一份卑微的工作,而食物链的顶层则因为拥有了充足的劳动力,榨取到了马克思说的剩余价值,供养他们穷奢极欲。再说房价这么高了,这么大的泡沫了,是泡沫就总有破的一天。
老婆每次听我这么一说也就不做声了,低头接着看她的手机,或者转身去厨房淘米做饭,好像真的是被我说服了,但我看着他低头专注淘米的背影,每次心里都愧疚得无以复加。老婆的白发比我的还多,儿子也拉扯大了,都可以交女朋友了,如果有一天未来的儿媳要上门来看看,如果没有一套大房子,会让她这个做婆婆的觉得脸上无光。我想给老婆换个大点的房子,我想,这个用基因技术逆转衰老的项目,应该是个能赚大钱的买卖。
加了广告上的微信号码,简单核对了一下基本信息,对方就发过来了面试地址的定位。我骑了辆共享单车,屁颠屁颠就去了。那是一个幽静的院子,在一个景区的半山腰,坐北朝南依山傍水,面对着流经这个城市的一条宽阔的河流。一条两车道的柏油路连接着院子和山脚下一片神秘的办公楼,办公楼高墙环绕,大门摆置着防恐袭的大型铁马,还有军人站岗,据说是某军区的陆军司令部。这个院子虽然没有在部队大院的围墙里,但说不定也是军产的一部分,而且是在景区里这么好的位置,院子主人的身份显得特殊而神秘。
后来知道,这个院子只是赵新民私人财产中极微小的一点,他拥有的财富远远超出了我的估计和市井平民的想象力。当天,赵新民亲自面试了我,高高瘦瘦,浓重的北方口音,看上去像个70来岁的精神矍铄的老头儿,看不出他那时已经有120多了,但说实话,我那时也没见过120岁的老人是个什么样子。赵新民问我知不知道端粒,我说知道,中学课本上有,而且我正在吃烟酸、β—烟酰胺单核苷酸这些东西,据说是NAD+(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的前体,进入人体后转化为NAD+,NAD+能减缓端粒的磨损,就好像给汽车发动机添加机油,保护发动机少磨损。
看着我半懂不懂的样子,赵新民说:“那就好,正好美国专家在南宁,他过两天就要走了,如果没什么问题,明天我们就做注射,你如果担心安全性,可以看着我先做,我也参加这次实验。”
我说:“好吧,明天需要我几点过来?”
后来知道,给我们做注射的是个顶级的华人生物学家,是个广东人,叫陈海峰,他在美国弄了个公司,为全世界提供最好的AAV技术,这技术的大意是,用一种叫做“腺相关病毒”的病毒做载体,运送各种基因片段进入人体。这种病毒不单能骗过人体的免疫系统的查杀,还能对人体无害。陈海峰还有个身份是美国基因与细胞治疗协会基因病毒运载技术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个委员会掌握着当时最顶级的生物技术。
怎么说呢,那时候的AAV技术安全性是没问题了,但量化控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得心应手,给我注射的这第一次就搞过量了。按端粒学说,拉长端粒,原先随年龄的进程而陆续失去活性的一些基因组,就会被重新恢复,重新启动,这个过程叫去甲基化。基因组失去活性,失去表达,则叫甲基化。这次去甲基化,去得太多了,直接启动了哺乳期的基因组。结果就是,搞得我对母乳又恢复了哺乳期的敏感度,闻到点奶味就抓狂,虽然心里知道这是基因干预起了作用,但理智是无力控制来自DNA的驱动的,人们习惯把这种驱动叫做本能。
虽然后来给我注射了反作用的抑制剂,最终控制住了吃奶的冲动,但这个过程持续了有小半年的时间,这段时间我完全不敢出门,担心见到乳房鼓胀的女人,就会做出失控的举动。呆在家里吧,家里还有老婆,老夫老妻这么多年了,本来已经很久没有性爱了,她对我那小半年在家里的举动虽然很吃惊,但也可能心里还是欢迎的。那小半年里,我的饮食口味也变得很尴尬,顿顿牛奶泡饭,牛奶煮面条,炸薯条不是沾番茄酱,而是沾奶粉,只有这样吃到撑的时候我才敢出门走走。饿的时候出门,走在大街上,我猜闻到点奶味,我就会抓狂失控。
总之吧,我就是从那时开始跟随赵新民,开始了这些基因技术的实验。后来技术稳定了,衰老的问题解决了,他又开始琢磨上了另一个更难缠的问题:意识。
不衰老不等于不会死,比如车祸、地震、鱼刺卡了喉咙等等意外,都会要了人命。虽然都是很小很小的小概率,但再小的概率,只要你活得足够长,也就一定会遇得上,这就是真理。这时候,一般的逻辑就会想,如果肉体注定死亡,那把意识备份就好了,只要意识还在,肉身就无所谓了,肉身只是意识的载体,可以再换个新的。
这叫“我思故我在”,这种老套的哲学思辨老祖宗们其实已经讨论了几千年了,并不新鲜,但真正落实到用人体去研究这个事情的时候,第一个面对的问题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烧钱。
很多年前,有个叫陈天桥的中国富豪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捐赠了一个项目,专门研究这个事情,每年捐1亿美元,连续10年。陈天桥是靠第一个引进网络游戏(精神鸦片)发的财,他成为中国首富的时候,只有30来岁。那时候的钱还比较值钱,10亿美元对任何一个普通人来说都是一大笔天文数字。这个项目进行了几年以后,不知什么缘故暂停了,估计最后还是没钱了,赵新民主动联系了这个项目,把它买了下来。
赵新民接手的时候,这个项目遇到了技术上的瓶颈。项目已经做了几年,已经做到可以观测和计量人脑的电流信号,也能实施干预,但所用技术必须直接接触大脑,这就意味着一定要打开人的头骨。打开头骨,大脑就会暴露在空气中,空气充满了微生物,失去了免疫系统的封闭保护,就会迅速感染、死亡,这可能是项目进行不下去的原因。
赵新民让我参与了这个项目的讨论,我提了个想法,这个想法后来改变了世界。我说,既然直接接驳大脑行不通,那能不能有间接的办法?比如,能不能把什么物质加入到血液中,血液携带这些物质流经大脑的时候,大脑的电信号能在这些物质上写下记录,然后在血管里回收这些携带了记录的物质,读取它们。
这些记录是记录在化学载体上的化学信号,再想办法把这些化学信号转译为电信号。到了电信号这步就好办多了,把电信号转换为光信号,光信号再转为图像,这都是很成熟的常规技术了。这套技术路径涉及把脑电信号转化为血液里的化学信号,再把化学信号收集起来,转化为电信号、光信号,听起来很复杂,实现起来就更复杂,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是,只要有足够的钱,总还是可以请科学家们试试看。赵新民最终采纳了我的这个想法,这些年他一直让我跟着他,就是觉得我的脑子还有点用。
这个项目后来又进行了很多年,耗费超级巨大,每年数亿数十亿美元的投入,简直堪比美国在1960年代的阿波罗登月计划。耗费巨大,连赵新民这样的居于食物链顶层的财阀都要想着再去赚些钱,维持研究的投入。做这些事情,需要有信得过的助手协助,所以我才有了机会,进入到了赵新民日常而又隐秘的生活,协助他完成那些日常而又隐秘的操作。这个阶段,我们朝夕相处无话不谈,我对他的了解才渐渐完整了起来。当然了解是相互的,这个过程我也几乎把我的每一个想法,甚至大脑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坦露在了他的面前。我们互相信任,甚至互相欣赏,当然,赵新民对我的欣赏主要是觉得我的学习能力没有让他失望吧,而我所学的来源,则多是来自他的亲自传授。
这个无比烧钱的项目每取得一点确定的进展,消息传来,赵新民总是很兴奋的要亲自测试,这些测试我又总在他身边协助。每次,当他在躺椅里躺好,当我把收集化学信号的探针插入他的血管,这时候他脑海里的记忆就一点一点的还原成了影像,投射在了我们眼前的显示器上。
我记得,当第一帧略微成型的图像出现在监视器上的时候,我们都兴奋到欢呼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