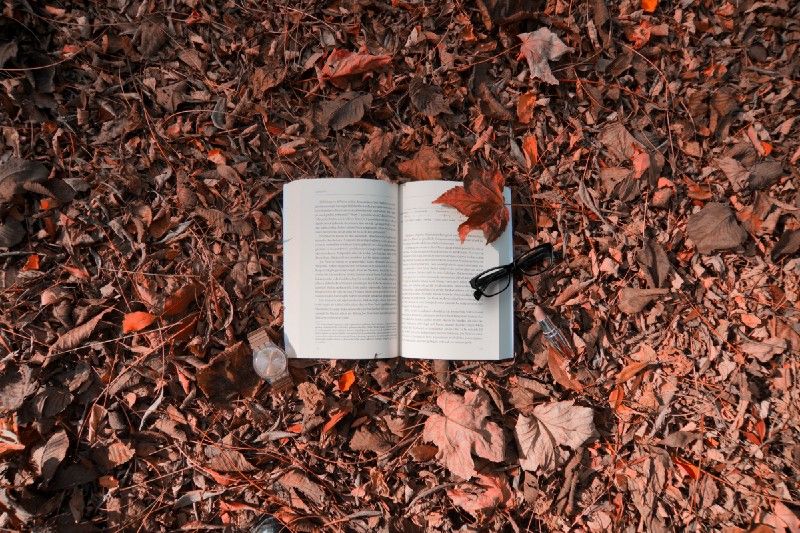學生時期熱衷參加文學比賽。
文學比賽徵求體裁很多元,有小說、新詩、古詩、散文、品德文。
每次參加比賽,看到小說項目就直接略過,
要寫什麼題材,要如何鋪陳、進展,還沒開始寫,光想想就覺得壓力山大。
而且最基本字數都要寫上數千字,這可不是一時半刻可以寫出來的。
但喜歡寫作,應該或多或少,都會對小說這體裁有野心吧?
雖然喜歡看小說,但感覺對寫小說一竅不通,所以一得知選修課裡有現代小說,毫不猶豫地選下去。
開始上課的時候是興致勃勃地,上到半途,換了個老師,講課方式迥異,充實感直線下降。選修課的最後,急急忙忙地要繳一篇小說,作業成績慘不忍睹,且得到了一個很哀傷的評語:「那不算是小說,更像是篇散文。」
學期結束了,還是對小說怎麼寫,不是很了解。
選修課程,幫助甚微。
往惡的方向說還是種打擊,覺得邯鄲學步,有種自己這輩子是寫不了小說的絕望感。
離開校園之後,秉持著某種奇怪的信念,想著寫小說也不需要有那麼多規範吧,為自己而寫,自己看就沒什麼限制了吧。降低心裡門檻後,陸續寫過幾次小說,雖然屢屢開頭,屢屢斷尾,還是能感覺快樂。
古詩體裁,也略過。畢竟對文言文沒興趣,連上課都沒認真的那種學渣類型。
打從心底,覺得自己會畫虎不成反類犬,不可能寫得好。
新詩倒是寫了不少,當時可能是把新詩當成不完整的散文來寫。
前因後果都相對模糊地,越是抽象描述,越能感受書寫自由。
且每一次閱讀理解的方式不同,就能收穫不同感受。
這也是極為少數,人們不會特地詢問創作的枝微末節。
說到底,新詩寫得是種感覺。
大學期間陸陸續續寫了不下百首,努力不輟地投稿了幾屆,屢戰屢敗也越戰越勇。
皇天不服苦心人,最後有幸第三名的佳績,雖然僅有一次。
品德文大概是怕來稿率太差,故某堂課,課堂作業要求每人皆需完成一篇且投稿完成。
那次應付交差地寫寫而已,居然拿到佳作,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現在想來,日常就是散文,日記也在寫散文啊。
如果當時不設限,好好寫,成績可能會更好也說不定。
除了學校時期的投稿經驗外,後來也陸續關注其他文學獎。
但是看了看題材,實在是無法為寫而寫,腦袋一片空白。
近期幸運地和友人們一起挑戰更新一百天,也算是在方格子重拾寫作興趣了。
沒有成就也沒關係,至少沒有放下表達這件事情,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