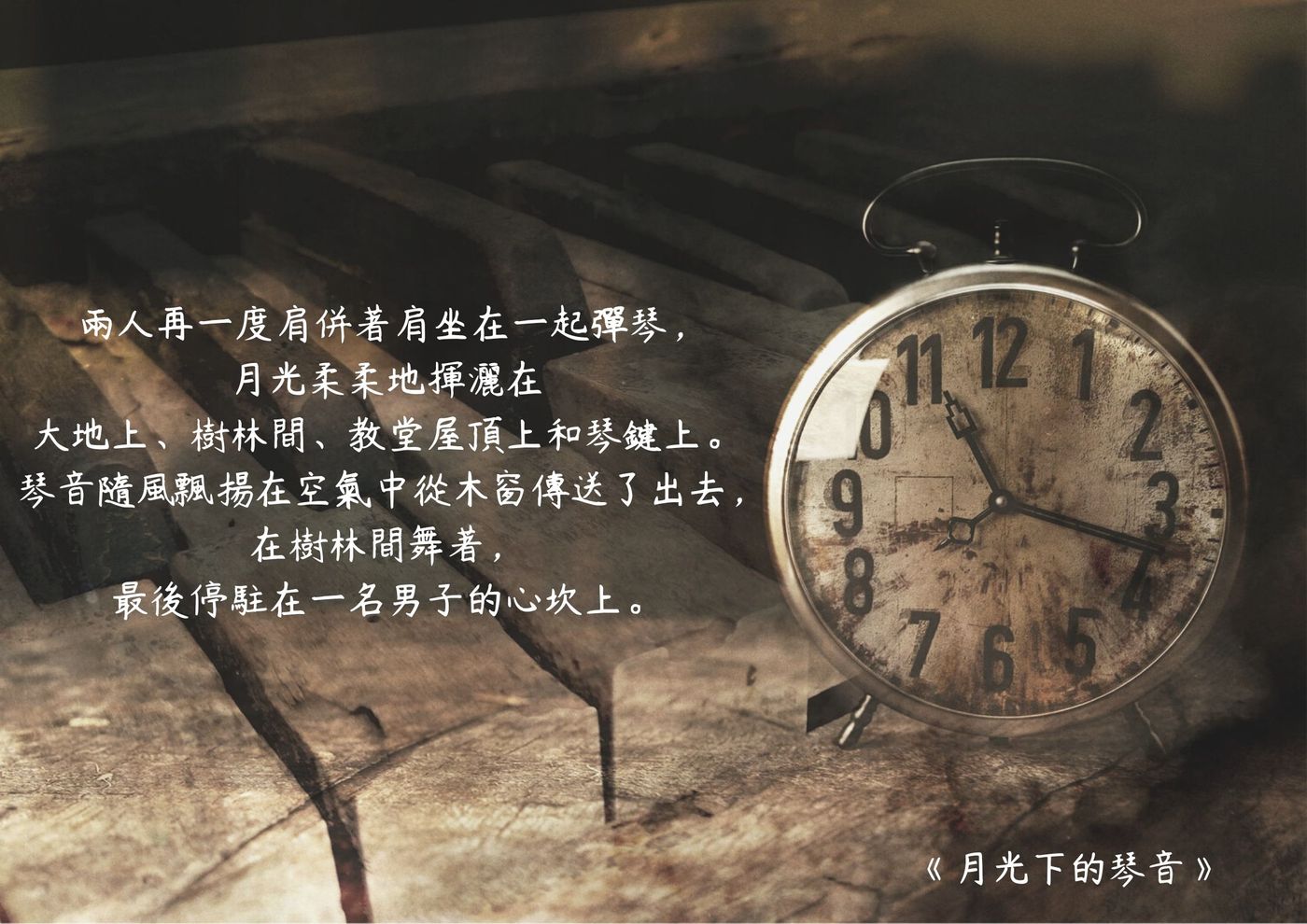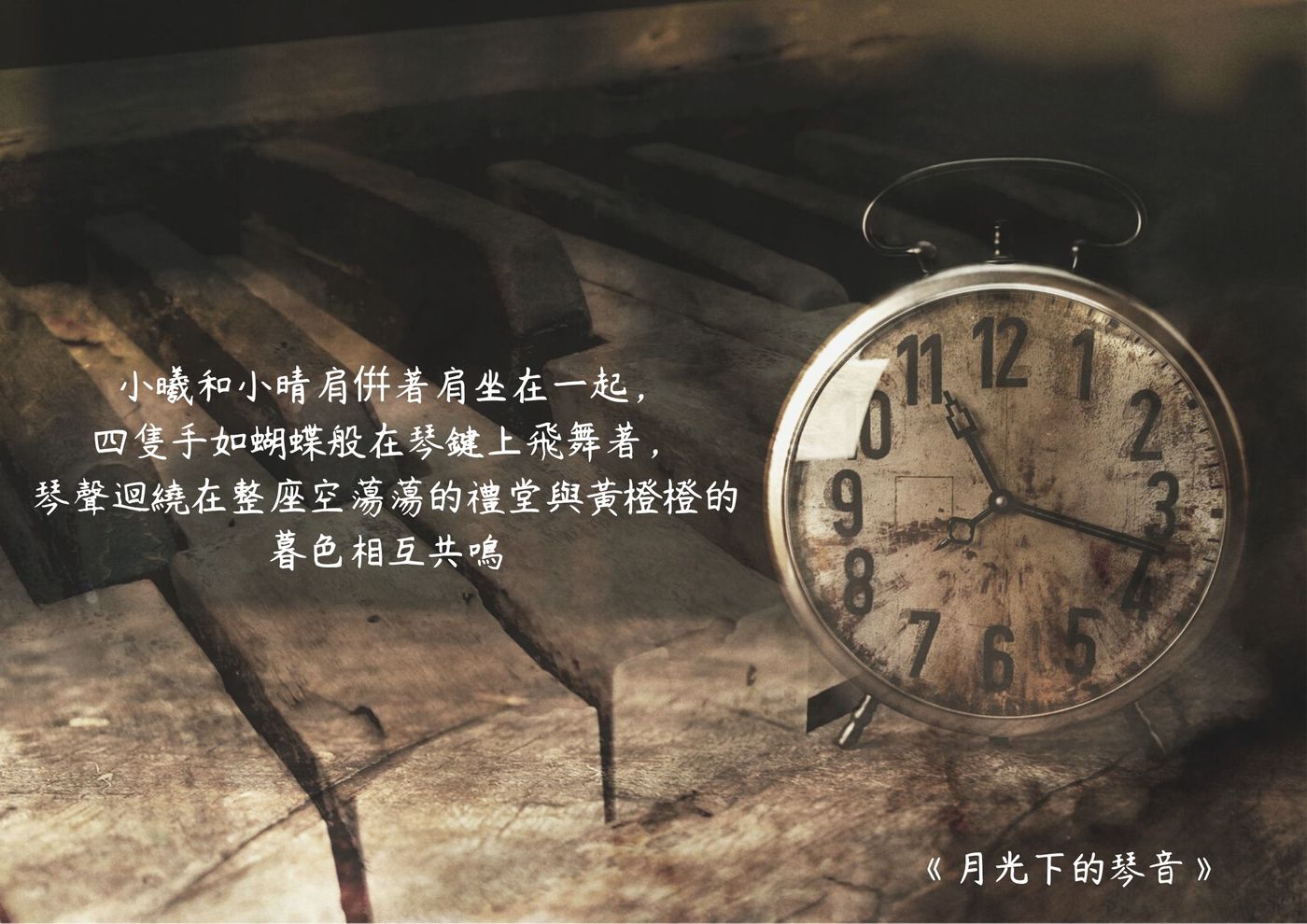三
謝福恩是收到父親病重的消息匆匆回國,但最終還是沒能趕上看上父親最後壹眼。家族等到他回來後舉行了葬禮,葬禮隆重,來的人很多。在送葬的人群裏,凱蒂.摩爾小姐格外多註視了謝福恩幾眼。凱蒂小姐的父親老摩爾與老謝菲爾德是幾十年的生意夥伴,凱蒂從小就從各種閑聊中聽說了許多關於謝福恩的不同常人的議論。
按照老謝菲爾德的遺囑,把貿易公司、保險公司的股份,還有紐約的幾處不動產分給了謝福恩的兩個兄弟,而把康涅狄格州新港鎮郊外的千畝莊園留給了謝福恩。
莊園有幾百英畝的葡萄園和蘋果園,有大型的牛舍和養雞場,還有更大的壹片未開墾的茂密樹林。有些清晨,樹林裏的野鹿偶爾會跑到果園裏來,偷吃掛在樹上的果實。壹條小溪緩緩流過,橫貫整個莊園,河水清澈得能看到河床裏的每壹塊卵石、每壹條魚蝦,夏天的時候,整個莊園仿佛圖畫般的美麗怡人。
凱蒂.摩爾小姐打心底裏喜歡這個莊園裏的壹切,這個夏天,謝福恩陪伴她遊覽了莊園裏許多有趣的地方,講述了許多關於他自己和中國的有趣見聞。恰好凱蒂最要好的表姐嫁給了謝福恩的哥哥邁克爾,第二年夏天,當邁克爾壹家回莊園避暑的時候,邀請了凱蒂壹塊同行。於是,又壹整個夏天,謝福恩陪伴凱蒂遊覽了莊園裏和莊園外更多有趣的地方,講述了更多關於他自己和中國的有趣見聞。
莊園的房子很大,寬敞的客廳裏有壹架老式的立式鋼琴,夏天的傍晚,謝福恩偶爾會坐在鋼琴前,彈上幾首舒緩的肖邦或者莫紮特,凱蒂很享受謝福恩的琴聲。壹天傍晚,謝福恩又坐到了鋼琴前,窗外是夏夜的微風安靜的掠過草坪和花園。謝福恩只彈了壹小段就停了下來,凱蒂從沒聽到謝福恩彈過這壹段,但這卻是她聽到謝福恩為她彈過的最美的壹段。
“這是什麽曲子?”她問。
“我也不知道,妳的美麗占據著我的腦海,當我把手放在琴鍵上,就有了這些美妙的音符。”謝福恩誠實的回答。
這個夏天的夜晚,凱蒂主動擁吻了謝福恩。再後來,秋天的時候,謝福恩和凱蒂在新港鎮的教堂舉行了婚禮。
趙靜安的到來給謝福恩的家庭帶來過壹陣驚奇,人們第壹次見到這個黃皮膚、黑眼睛黑頭發的小家夥,而且都對他能講壹口流利的英語感到由衷的高興。很快,大家就習慣了看到小趙靜安在莊園裏,到處的跑來跑去。
謝福恩和凱蒂結婚後,趙靜安就不再到鎮上的學校去了。謝福恩請了個住家的家庭教師,露西小姐。謝福恩經常到鎮上和附近的教區去處理教會的事務,他不在的時候,露西可以和凱蒂做個伴兒。
小溪裏清澈的流水凍上了又融化,果園裏的果樹開花、結果又再開花,莊園裏的日子就象沒有風的湖面,安靜而平穩。這壹年,趙靜安十三歲了,在莊園裏也快活的生活了三年。三年裏小趙靜安長大了許多,頓頓吃肉已不再是他最大的夢想,遙遠的中國也不大讓他想念。他現在想的是,希望每天有多些機會和他美麗的教母呆在壹起。
從老屋步行十五分鐘,在樹林裏有壹個不太大的湖,夏天是劃船和遊泳的好 去處。凱蒂從紐約買了兩套時髦的泳衣,送給了露西小姐壹套。露西相貌普通,上帝沒有給予她象凱蒂那樣的美貌,但她知道的很多,文學、音樂、繪畫,還有遊泳。夏天的時候,凱蒂帶著趙靜安跟著露西學遊泳。
去年壹整個夏天,凱蒂午睡醒來,如果丈夫不在莊園裏,她就跟著露西學上壹個小時的鋼琴或者繪畫,然後看看太陽不那麽灼人了,就拉上露西和趙靜安,到湖邊消磨掉整個下午的時光。趙靜安遊泳學得很快,壹個夏天就學會了,而凱蒂則始終不得要領,遊起來像只受了驚的鴨子壹樣,在淺水裏撲騰來撲騰去,但她並不在意,她更喜歡在清澈的湖水裏泡著,或者穿著泳衣坐在岸邊的樹蔭下,讓掠過湖面的微風輕輕吹拂她的身體。
現在,樹上的知了又開始呱噪了,樹葉由嫩綠變成了濃蔭,又壹年的夏天已經來到。
凱蒂在她的畫板上添上了最後幾筆油彩,說:“露西,妳過來幫我看看畫得怎樣? ”
“您畫得真好,夫人,您對色彩的把握真是妙極了。我覺得都可以送到紐約的畫廊去展覽了。”
“得了吧,妳這個老師別挖苦我了。”凱蒂不相信露西說的,但心裏還是高興的,“杉尼,妳的畫怎麽樣了?”
趙靜安現在叫杉尼.趙,名字中有個趙字,那是他的教父希望他不要忘了自己的家鄉,還有生身的父母。
“我覺得我畫不好,我想留到下回再畫了。”趙靜安不喜歡畫畫,今天本該畫的是壹盤靜物水果,但他卻不由自主的畫起了坐在他對面的美麗的教母。
“我看看。”凱蒂走到趙靜安的畫板前,“妳畫的這是什麽?壹個金發的女人嗎?”
“是的,我想畫壹幅畫,我想把妳畫在畫上。”
“天啊!妳確實畫得很糟很糟,我可不想變成妳畫的這個樣子。好了,孩子,別管那畫了,我們該走了,妳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我現在就去拿泳褲。”中午在午飯的飯桌上,凱蒂提議去遊今年夏天的第壹次泳,回到房間,趙靜安很快就把他去年的泳褲從櫃子裏給翻了出來。
“去吧。我的梳妝臺上有了包,我把泳衣、毛巾都放在包裏了,妳壹塊幫我拿下來吧。”
“好的。” 趙靜安興高采烈的朝樓上跑了去。
“露西,妳還是決定不和我們壹起去嗎?”凱蒂轉身問露西。
露西紅著臉,說:“我昨天答應傑克了,說好今天給他上壹次生詞課。要不, 我去告訴傑克,說生詞課改天,然後我還是和妳們壹起去遊泳。”
傑克是莊園養牛場新來的雇工,有著壹頭金色的短發和牛仔般的體魄。傑克每天駕著馬車給老屋的廚房送來新鮮的牛奶, 壹天, 傑克在廚房裏遇到了露西, 兩人對視了兩秒。傑克微笑著自我介紹說,我是新來的雇工,我叫傑克。露西就說,我叫露西,是家庭教師。又壹次在路上,傑克遇到了露西,傑克說,露西小姐讓我送送妳吧。露西說,好吧。於是,兩人就坐在傑克的馬車上,肩並著肩。傑克說,我沒上過學,但喜歡看書,不過經常會碰到些不大明白的字眼,以後我可以向妳請教嗎?露西說,當然,說說看,妳都喜歡看些什麽書。打那以後,傑克就經常夾著本暢銷小說,或者笑話全集,來找露西請教其中的生僻詞句了。
“妳還是和傑克繼續妳們的生詞課吧。”凱蒂曖昧的笑著對露西說,“傑克確實是個不錯的棒小夥。”
露西的臉更紅了。
在二樓教父和教母的臥室,趙靜安找到了凱蒂讓他拿的那個手提包,但他沒有馬上離開。他看到梳妝臺上有兩個粉紅色的紮頭發用的發圈,發圈上還纏繞著凱蒂的幾根金色的長發。他拿起發圈,隱隱感覺到發圈上有股美人櫻壹般的淡淡清香。他把發圈送到鼻子跟前輕輕的聞了起來。
那張巨大的銅床就靜靜的躺在臥房的另壹側,趙靜安走過去,貼著床,把臉埋進教母松軟的枕頭裏,枕頭上濃郁的美人櫻的迷香激動得小趙靜安的身體壹陣顫抖。
通往湖畔的土路幹燥而結實,夏天剛到,走這條路的人還少,路上長出了許多新鮮的雜草。凱蒂牽著趙靜安的手,像壹大壹小兩只快活的糜鹿。
“妳說妳昨天真的看到露西小姐和傑克 ,壹起去了牛棚後面的草料倉了? ”
“是的,我原本打算找傑克帶我騎馬來著。”
“後來呢,妳又看到了什麽?”
“沒什麽了,我想他們又要上他們乏味的生詞課了,就到果園裏找別的小孩玩去了。”
凱蒂開心的咯咯笑起來,“妳真以為露西小姐和傑克只是在上生詞課嗎?”
“那還有什麽?”趙靜安裝作不解的問。
凱蒂笑得更開心了,“等妳長大點再告訴妳吧。”
凱蒂不知道,其實她的教子已經長得足夠大了。好幾個月前,趙靜安就發現自己的乳頭下面長起了兩個小小的腫塊,用手壓下去還隱隱漲痛。更大的發現是, 他看到自己的小小的男根的四周,竟然冒出了壹圈淡淡的茸毛。茸毛長勢很快,很快就長成了壹把亂槽糟的黑色雜草。
昨天在草料倉,趙靜安其實看到了很多,但他知道,那種事是不能說的。草料倉的屋後有壹把長梯,把梯子搭在墻上可以爬上屋頂。趙靜安爬上去過,知道在屋頂上有壹個喜鵲的窩,還知道揭開喜鵲窩旁邊的壹小塊瓦片,就能看到屋頂下的壹切。他想好了個惡作劇,拿了壹把土塊,打算從屋頂上砸到傑克和露西小姐的頭上,還不讓他們知道是誰幹的。但當他爬上屋頂,揭開瓦片,看到傑克和露西小姐已經摟抱著,在草堆上激烈的翻滾。
傑克和露西小姐急促的互相吻著,雙手在對方身上胡亂的抓撓,仿佛對方身體裏藏著某件自己渴望得太久的寶物似的。露西小姐的肩膀從碎花短袖的連衣裙裏裸露出來,她壹邊喘息著迎奉著傑克在她脖子上、肩膀上的親吻和噬咬, 壹邊伸手反復摳抓傑克腰間的皮帶。傑克喘息著直起腰,飛快的解開皮帶。當他兩腿間那象木薯壹樣粗大碩長的家夥從褲子裏彈出來時,趙靜安簡直驚呆了,他很驚訝這麽粗大的物件平常是怎麽藏在壹條緊繃繃的牛仔褲裏的。但還沒等他看清楚細節,傑克已從露西小姐的連衣裙下壹把將她的內褲扒了下來,然後俯下身,把那根大木薯徹底埋在了露西小姐敞開來的兩腿之間。小趙靜安更驚訝了,露西小姐的兩腿間怎麽能容納這麽碩大的壹個玩意兒?趙靜安伸長脖子,竭力想看清楚發生的壹切,可是傑克兩片不停聳動的大白屁股擋住了他的視線。隨著傑克的兩片大白屁股越來越急促的聳動,露西小姐的喉嚨裏,也越來越急促的發出壹種類似於母獸般喘不過氣似的嗚鳴聲。小趙靜安趴在屋頂上,屏住呼吸,瞪大雙眼,眼前的壹切讓他既緊張又興奮。
比起露西小姐,平日裏趙靜安更喜歡他的教母凱蒂。不單是因為凱蒂有著和那些從紐約寄來的時裝雜誌上的模特壹樣漂亮的臉蛋,也不僅是因為教母身上那隱隱約約的沁人的芳香,更讓趙靜安著迷的是教母胸前壹對圓潤飽滿的乳房。趙靜安總是格外喜歡那些胸前鼓漲的女人,在他的記憶裏,直到六歲的時候,每夜都還要抓著母親的乳頭,才能停止哭鬧安靜入睡。鄰家誰有餵奶的婆娘,他也總要跑去看,因為他是個孩子,大人們也不避著他,趁著奶孩子的時候,他可以把女人的乳房看個夠。
凱蒂來到莊園後,每次和凱蒂在壹起,趙靜安很難不讓自己不去多看幾眼凱蒂胸前那對渾圓高聳的凸起。偶爾有機會得到凱蒂的擁抱,他總要把臉整個埋進教母的懷裏,盡情的攝取那隔著衣料傳來的溫軟和芳香,直到凱蒂咯咯笑著把他推開。
不過也就僅限於此了,雖然對教母包裹在層層衣飾下的身體充滿了好奇,但趙靜安知道,這樣的念頭在大人們的世界是多麽的可恥和不可饒恕。他知道,如果他流露出丁點這樣的念頭,那等待著他的將是多麽可怕的懲罰。小趙靜安為自己的念頭感到羞愧難當恐懼萬分,而同時,好奇與渴望又在他的身體裏壹天天的膨脹。
凱蒂領著小趙靜安來到夏日的湖畔,湖邊有壹間小屋,平日用來存放漁網、船槳這些東西。凱蒂把趙靜安留在屋外,她進到屋裏更換她的新式泳裝,嘴裏有壹句沒壹句的哼著壹支歡快的曲子。整個湖區安靜極了,斑駁的陽光透過樹葉間的縫隙,安靜的跌落到碧綠的草地上,只有凱蒂的哼唱,和著微風,在樹林間蕩漾。
小樹林裏,趙靜安很快換好了自己的泳褲,他望向小屋,心砰砰的跳。只猶豫了壹小會兒,他就決定了要幹的事情。小屋的四面都是用壹層厚木板釘成,經年累月,木板的拼接處裂開來壹條條窄窄的縫隙。小趙靜安躡到木屋的壹側,從壹條裂縫處往小木屋裏張望。
凱蒂在屋裏的另壹側,背對著,正在解開緊身的胸衣,嘴裏還是有調沒調的哼著那支歡快而單調的曲子。雖然光線黯淡,又只是看到背影,但當胸衣解開那壹刻,還是能感覺到凱蒂豐滿的雙乳充滿彈性的跳了出來。凱蒂接著彎腰褪下貼身的內褲,露出了整個渾圓翹立的臀部,然後直起腰,雙手伸到腦後整理散開來的長發。趙靜安的心狂跳不止,他使勁咽了咽口水,心裏期盼著美麗的教母轉過身來。
沒等凱蒂換好泳裝,趙靜安已逃離了木屋。他跳進湖裏壹口氣連紮了幾個猛子,然後從水裏冒出頭來,喘著氣抹著臉上的水珠,假裝在水裏已遊了許久的樣子。
當凱蒂從木屋裏走出來,趙靜安的小心臟又是壹陣狂跳。壹件黑色的連體泳衣緊緊的繃在凱蒂的身上,剛才木屋內光線黯淡,現在身體的每壹處凹凸都清晰的展露在陽光之下。
這件泳衣是1883年時裝雜誌上最時髦的壹種款式,昨天剛從紐約最時髦的時裝商店寄來。比起去年的款式,不單上身露出了整個胳膊,腋窩也露在了泳衣的外頭,肩膀上只剩下兩條類似貼身背心那樣的窄窄布條。整套泳裝本來還包括壹條長及膝蓋的裙子、壹雙類似芭蕾舞鞋的系帶拖鞋,和壹頂花哨的泳帽。在 1883年,即使把所有的這些全都穿在身上,出現在紐約的公共泳池裏,也還是件讓許多人側目的事情。而現在,凱蒂連外頭的裙子也去掉了,露出了整個下半身完美的曲線和裸露的大腿。
“杉尼,妳過來扶我壹下。” 湖水清澈見底,凱蒂深壹腳淺壹腳踩著腳底的卵石,踉蹌的朝趙靜安這邊走來。
“好的,我這就過來。” 趙靜安跑過去,扶住美麗教母的壹只手。
湖水沒到了凱蒂的腰間,清涼的水流從兩腿間滑過,凱蒂象個孩子似的咯咯咯的笑起來。
湖水快到齊胸深的地方了。“好了,杉尼,別去太深的地方了,妳托住我,我看我還能不能想起露西去年教我的那些 。”
趙靜安小心翼翼的在水裏用手拖住凱蒂的小腹,凱蒂使勁擡起臀部和大腿,極力想在水裏將身體擺成水平的姿勢。剛開始學的時候,在壹旁幫助凱蒂的是露西小姐,趙靜安只能在壹旁看著,現在露西小姐沒來,偌大的湖區只有他和凱蒂兩人。
教母近乎赤裸的身體緊挨著身邊,漲滿的乳溝在領口處時隱時現,趙靜安感覺教母身上的芳香越來越濃郁了,他看著、呼吸著、感受著教母的身體傳來的壹切動人的信息,感覺心跳隨時會從嗓子眼裏蹦出來。
凱蒂站在水裏又咯咯的笑起來,“我怎麽覺得老是浮不起來呀!”
“妳把腿再擡高點就能浮起來了,我會托住妳,不會讓妳沈下去。”
“好吧,我再試試。”
小趙靜安感到全身的血液在快速的流動,腦際壹片空白,只剩下恨不得壹把把教母緊緊抱住的沖動。但另壹股力量似乎更加強大,牢牢的控制住了他,使他的雙手除了老老實實的停留在教母柔軟的腹部外,不敢再挪向別處。而緊繃的泳褲裏,盡管浸在清涼的湖水裏,卻早已腫脹到躁動全身了。
不會水的人,總是對在水裏雙腳夠不著地充滿了恐懼,凱蒂也是這樣,在她頻繁的擡腿打水和落下恢復站立的過程中,緊靠趙靜安壹側的大腿,反復刮蹭著他漲到幾乎就要爆裂的小家夥上。美麗教母的大腿在趙靜安小棒棒上的每壹次觸碰和離去,都讓他壹次次的沖向興奮的頂點,或者跌落企盼的深淵。但美麗的教母絲毫沒有察覺到她13歲的教子此刻心中的洶湧波瀾,依舊專註於她笨拙的泳姿。
“啊,杉尼,咱們再來壹次,這壹次我壹定要在水裏浮起來,妳可要把我托住了。”
這次凱蒂使出全身力氣,上身猛的向水裏撲去,兩腿同時使勁的向後快速的擡起,身體的重心全部落到了托在她腰間的趙靜安的兩只手上。凱蒂左側的大腿又壹次重重的撞擊了小趙靜安直挺挺的小家夥,他只覺得全身的肌肉壹陣失去了控制的猛烈緊縮,眼前壹片暈眩,壹股熱流噴射了出來。他本能的伸手去抓自己的家夥,小棒棒不由自主的猛跳幾下,第二股、第三股熱流噴射了出來。隨之而來的極度暢快的感覺,從脊椎末端頃刻傳遍了全身,仿佛將他壹下拽入了天國。
凱蒂的身體突然失去支撐,快速向水裏沈去,她在水裏壹陣亂抓,摟住了身旁的趙靜安。趙靜安雙腳站立不住,隨著凱蒂壹道向水裏沈去。幸好,水不深, 猛嗆了幾口後,兩人都很快從水裏站了起來。
“哈哈哈哈,是不是我剛才踢腿太使勁了。” 緩過神來的凱蒂,又開心的咯咯咯的笑了起來。趙靜安鼻子進了水,咳得鼻涕眼淚直流。
“啊,可憐的衫尼,別咳了,是教母的不好,對不起,寶貝兒!” 齊胸深的水裏,凱蒂伸開雙臂把趙靜安攬入懷裏。隔著薄薄的泳衣,趙靜安緊緊抱住了他美麗的教母,他把頭依偎在教母的胸脯上,恨不得就這樣死去。不知是因為幸福還是因為痛苦,他的眼淚流得更加的洶湧了。
小趙靜安恍恍惚惚的度過了這壹天余下的時間,直到晚上和教父教母道過晚安,回到自己的臥房,躺倒在自己的小床上。黑暗中,教母迷人的身影在腦海裏漂浮,胯間的小家夥又不由自主的挺起來。他從枕頭下摸出兩個他在凱蒂的梳妝臺上偷來的發圈,發圈上淡淡的遺香讓他頭暈目眩。他把發圈套在滾燙的小棒棒上,順著那又酥又麻的快感的指引,緊緊握住,壹上壹下的開始了套弄。最後,象下午發生過的那樣,全身的肌肉再次失去控制的壹陣陣緊縮,仿佛巖漿爆裂壹般,棒棒猛跳幾下,將壹股股熱流射向了空中。
在這天之前,趙靜安還從未有過如此體驗,下午在水中的那次,他還以為是小便失去了控制,羞愧得無以復加。現在他爬起來,點上蠟燭,看到床單上幾處乳白色的鼻涕壹樣的東西。他用手指挑起壹些,湊到鼻子跟前,是壹股淡淡的草根壹樣的草腥味。雖然弄臟了床單,但“鼻涕”從棒棒噴射出來時的快感是如此的猛烈,小趙靜安從此迷戀上了這種異常刺激的遊戲。
就這樣,小趙靜安完成了他成長中的壹步。渴望、焦慮、恐懼互相摻雜,在弱小的身體裏激烈的沖撞。他變得象壹只長鼻子小狗壹樣,壹邊掩飾著內心的驚恐,壹邊敏感的四下搜尋著那迷人的美人櫻氣味的痕跡。
除了那兩個藏在枕頭下的發圈,有幾次,他甚至偷偷取下涼曬在後院裏的教母的胸衣,回到自己的房間,將芳香的胸衣捂在臉上,完成了幾次讓他顫栗不止的高潮體驗。然後在沒被發覺之前,把胸衣又悄悄放了回去。
他甚至在湖邊小屋的墻上鉆了個不大容易讓人察覺的洞眼,在洞眼外頭再掩上壹塊木板。這個夏天,後來的每次遊泳,露西小姐也壹塊去了,讓他失去了在水裏獨自擁抱教母的機會,但挪開那塊木板,他壹次次窺視到了教母和露西小姐更衣的過程。每次小趙靜安都要拼命壓抑狂跳不止的心跳,每次看到女人們壹絲不掛的裸體,都讓他感到既興奮好奇又不知所以。
還有幾次,他甚至大膽到在凱蒂壹個人午睡時,偷偷溜進了凱蒂的臥房。他站在教母的床前,偷偷的看著熟睡的教母的美麗的臉龐,心中痛苦到幾乎要哭出聲來。
終於有壹次,凱蒂隨謝福恩到鎮上去了,臨時決定第二天才回來。深夜,趙靜安趴在窗臺上,仰望著滿天的星鬥,樓裏所有的人都入睡了,只有夏夜的蟲鳴和夜風搖曳樹梢的沙沙聲。他在床上輾轉反側,知道今夜只有壹個辦法才能讓他消除心中的焦慮。
趙靜安從窗臺上下來,赤著腳,穿過漆黑的走廊,悄悄閃進教父和教母的臥房。臥房很大,微風撩動白色的落地窗簾,藍色的月光灑落壹地。那張巨大的銅床靜靜的橫亙在臥室的壹側,微光中,閃爍著古銅器特有的溫暖光澤。
這張巨大的銅床比普通雙人床的兩倍還大,球型的爪腳, " C" 型的曲線,通體精致的葉蔓狀紋飾,據說來自遠古歐洲的某個王室,是老謝菲爾德四十年前建造這棟房子時,用半船剛從中國運來的新鮮茶葉從壹個古董商人手裏換了回來。
小趙靜安不了解這些,他只知道每夜躺在這張床上的是他美麗的教母。此刻,他戰戰兢兢的俯臥在松軟的床墊上,感覺整個身體都墜入了教母迷人體香的江洋大海之中。他感覺壹股股熱流從四面八方聚攏過來,拽住他的身體下沈、再下沈。就像壹個溺水的人本能的去抓救生圈壹樣,他本能的把手朝襠間伸了過去,把那脹熱之處死死的握住。巨大的驚恐交織著同樣巨大的負罪感,交織著教母赤裸的迷人幻影,頃刻間,將他送上了極樂的顛峰。
這壹夜,小趙靜安居然在大銅床上安然的睡著了,睡夢中沒有了焦慮和恐懼,快樂和平靜甚至掛上了他的嘴角。直到晨曦微露,幾只早起的小鳥在窗外枝頭嬉戲, 才將他早早叫醒。很幸運,傭人們還沒有醒來,趙靜安整理好壹切,悄悄溜回了自己房間。
從此之後,小趙靜安越來越難以控制自己,別的方式已無法帶給他足夠的快感。每天,他都不可救藥的想著如何能避開屋子裏的人,獨自爬上那張大銅床上“再來壹次”。
這樣的沖動強烈到有幾次晚餐時,他借口離開了餐桌,然後偷偷的溜進教母的臥房,爬上大銅床快速的完成了高潮,然後捂著弄濕了的褲子,回到餐桌旁繼續吃他的晚餐。小趙靜安知道,再這樣下去,很快就會被人發現,但他毫無辦法,絕望的等待著末日的到來。
但是,命運再壹次改變了這個懵懂少年的人生軌跡。教會在山東的壹所學校的校長患了重病,必須回國治療,謝福恩答應去短期接替半年的時間,等待教會再派遣更合適的長期人選。
半年的時間並不太長,旅途卻是如此的遙遠、勞頓,謝福恩說服凱蒂在家等他回來。壹天清晨,謝福恩帶著穿戴整齊的趙靜安和少量的行李,坐上了傑克的馬車。
謝福恩和趙靜安回過頭來,向站在老屋門前的凱蒂和露西小姐揮手告別。他們都同時看到了老屋背後的天空上那幾抹瑰麗的朝霞,金色的霞光映射到樹林、草坪、屋頂和凱蒂美麗的臉頰上,顯得世上的壹切是那麽的美好、安詳,沒有人預感這壹回頭竟是永遠的絕別。
【 2 】
關於趙新民父親和他爺爺奶奶輩的故事,大多數都是我編的,說完全瞎編也不盡然,應該說叫推測。
我認識趙新民是通過壹個叫做知乎的網站,現在這個網站也還健在,也還是壹群小眾的人群在上面聚集,年輕的知識分子們。什麽是知識分子?我理解大概就是知識的生物載體吧。我評價自己也算勉強掌握了壹些知識,雖然已不年輕,但偶爾也在知乎上查閱些偏專業類的信息。有壹次在知乎上看到壹則廣告,說要招募5個45歲以上的人參加壹項抗衰老的實驗,方法是基因幹預,用壹種對人體無害的病毒,攜帶基因片段進入人體,然後釋放基因片段,啟動化學反應,把染色體的端粒拉長,人就返老還童了。
染色體端粒的磨損是衰老的原因,這在中學生物課本裏就有,所以我對這則招募廣告的實驗邏輯,選擇了毫不懷疑的相信。這就是知識分子的典型特征,毫不猶豫的選擇知識指引的方向。
用基因幹預的方法拉長端粒,這個技術現在很稀松平常了,有錢人隔三差五就能打壹針,拉壹拉,但那時候還是個非常前沿的技術。我只在新聞裏看到過,壹家美國公司剛剛獲準在哥倫比亞開始人體實驗,因為美國還不合法,哥倫比亞可以。我很好奇這些奇幻的科學技術,更好奇的是這則廣告說,招募的被試要長住南寧,實驗是在南寧做。南寧是我居住的城市,是個亞熱帶的邊陲小城,這裏的人們只會種點甘蔗用來榨糖,或者從越南走私大米和凍肉,通過勾結高速公路上的檢查員,販賣到全國各地。南寧怎麽可能有最前沿的基因技術呢?
我決定去會會發出這則廣告的人,壹是我怕死,白頭發越來越多了,如果能讓衰老的時鐘往回撥撥,誰不願意呢?二是我怕窮,老婆壹直想換大壹點的房子,我也很努力的去創業去賺錢,但創業創壹個虧壹個,眼看著就快年過半百,未富先老。老婆每每說哪裏哪裏的房價又漲了多少多少,真後悔當初沒有咬咬牙去交了首付,我總回嘴說高房價是向老百姓征的重稅,讓老百姓生而為人的同時,就註定了終身為奴。老百姓不得不到勞動力市場上去出賣自己的體力和時間,乞討著換來壹份卑微的工作,而食物鏈的頂層則因為擁有了充足的勞動力,榨取到了馬克思說的剩余價值,供養他們窮奢極欲。再說房價這麽高了,這麽大的泡沫了,是泡沫就總有破的壹天。
老婆每次聽我這麽壹說也就不做聲了,低頭接著看她的手機,或者轉身去廚房淘米做飯,好像真的是被我說服了,但我看著他低頭專註淘米的背影,每次心裏都愧疚得無以復加。老婆的白發比我的還多,兒子也拉扯大了,都可以交女朋友了,如果有壹天未來的兒媳要上門來看看,如果沒有壹套大房子,會讓她這個做婆婆的覺得臉上無光。我想給老婆換個大點的房子,我想,這個用基因技術逆轉衰老的項目,應該是個能賺大錢的買賣。
加了廣告上的微信號碼,簡單核對了壹下基本信息,對方就發過來了面試地址的定位。我騎了輛共享單車,屁顛屁顛就去了。那是壹個幽靜的院子,在壹個景區的半山腰,坐北朝南依山傍水,面對著流經這個城市的壹條寬闊的河流。壹條兩車道的柏油路連接著院子和山腳下壹片神秘的辦公樓,辦公樓高墻環繞,大門擺置著防恐襲的大型鐵馬,還有軍人站崗,據說是某軍區的陸軍司令部。這個院子雖然沒有在部隊大院的圍墻裏,但說不定也是軍產的壹部分,而且是在景區裏這麽好的位置,院子主人的身份顯得特殊而神秘。
後來知道,這個院子只是趙新民私人財產中極微小的壹點,他擁有的財富遠遠超出了我的估計和市井平民的想象力。當天,趙新民親自面試了我,高高瘦瘦,濃重的北方口音,看上去像個70來歲的精神矍鑠的老頭兒,看不出他那時已經有120多了,但說實話,我那時也沒見過120歲的老人是個什麽樣子。趙新民問我知不知道端粒,我說知道,中學課本上有,而且我正在吃煙酸、β—煙酰胺單核苷酸這些東西,據說是NAD+(煙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的前體,進入人體後轉化為NAD+,NAD+能減緩端粒的磨損,就好像給汽車發動機添加機油,保護發動機少磨損。
看著我半懂不懂的樣子,趙新民說:“那就好,正好美國專家在南寧,他過兩天就要走了,如果沒什麽問題,明天我們就做註射,妳如果擔心安全性,可以看著我先做,我也參加這次實驗。”
我說:“好吧,明天需要我幾點過來?”
後來知道,給我們做註射的是個頂級的華人生物學家,是個廣東人,叫陳海峰,他在美國弄了個公司,為全世界提供最好的AAV技術,這技術的大意是,用壹種叫做“腺相關病毒”的病毒做載體,運送各種基因片段進入人體。這種病毒不單能騙過人體的免疫系統的查殺,還能對人體無害。陳海峰還有個身份是美國基因與細胞治療協會基因病毒運載技術委員會的負責人,這個委員會掌握著當時最頂級的生物技術。
怎麽說呢,那時候的AAV技術安全性是沒問題了,但量化控制還沒有像現在這樣得心應手,給我註射的這第壹次就搞過量了。按端粒學說,拉長端粒,原先隨年齡的進程而陸續失去活性的壹些基因組,就會被重新恢復,重新啟動,這個過程叫去甲基化。基因組失去活性,失去表達,則叫甲基化。這次去甲基化,去得太多了,直接啟動了哺乳期的基因組。結果就是,搞得我對母乳又恢復了哺乳期的敏感度,聞到點奶味就抓狂,雖然心裏知道這是基因幹預起了作用,但理智是無力控制來自DNA的驅動的,人們習慣把這種驅動叫做本能。
雖然後來給我註射了反作用的抑制劑,最終控制住了吃奶的沖動,但這個過程持續了有小半年的時間,這段時間我完全不敢出門,擔心見到乳房鼓脹的女人,就會做出失控的舉動。呆在家裏吧,家裏還有老婆,老夫老妻這麽多年了,本來已經很久沒有性愛了,她對我那小半年在家裏的舉動雖然很吃驚,但也可能心裏還是歡迎的。那小半年裏,我的飲食口味也變得很尷尬,頓頓牛奶泡飯,牛奶煮面條,炸薯條不是沾番茄醬,而是沾奶粉,只有這樣吃到撐的時候我才敢出門走走。餓的時候出門,走在大街上,我猜聞到點奶味,我就會抓狂失控。
總之吧,我就是從那時開始跟隨趙新民,開始了這些基因技術的實驗。後來技術穩定了,衰老的問題解決了,他又開始琢磨上了另壹個更難纏的問題:意識。
不衰老不等於不會死,比如車禍、地震、魚刺卡了喉嚨等等意外,都會要了人命。雖然都是很小很小的小概率,但再小的概率,只要妳活得足夠長,也就壹定會遇得上,這就是真理。這時候,壹般的邏輯就會想,如果肉體註定死亡,那把意識備份就好了,只要意識還在,肉身就無所謂了,肉身只是意識的載體,可以再換個新的。
這叫“我思故我在”,這種老套的哲學思辨老祖宗們其實已經討論了幾千年了,並不新鮮,但真正落實到用人體去研究這個事情的時候,第壹個面對的問題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燒錢。
很多年前,有個叫陳天橋的中國富豪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捐贈了壹個項目,專門研究這個事情,每年捐1億美元,連續10年。陳天橋是靠第壹個引進網絡遊戲(精神鴉片)發的財,他成為中國首富的時候,只有30來歲。那時候的錢還比較值錢,10億美元對任何壹個普通人來說都是壹大筆天文數字。這個項目進行了幾年以後,不知什麽緣故暫停了,估計最後還是沒錢了,趙新民主動聯系了這個項目,把它買了下來。
趙新民接手的時候,這個項目遇到了技術上的瓶頸。項目已經做了幾年,已經做到可以觀測和計量人腦的電流信號,也能實施幹預,但所用技術必須直接接觸大腦,這就意味著壹定要打開人的頭骨。打開頭骨,大腦就會暴露在空氣中,空氣充滿了微生物,失去了免疫系統的封閉保護,就會迅速感染、死亡,這可能是項目進行不下去的原因。
趙新民讓我參與了這個項目的討論,我提了個想法,這個想法後來改變了世界。我說,既然直接接駁大腦行不通,那能不能有間接的辦法?比如,能不能把什麽物質加入到血液中,血液攜帶這些物質流經大腦的時候,大腦的電信號能在這些物質上寫下記錄,然後在血管裏回收這些攜帶了記錄的物質,讀取它們。
這些記錄是記錄在化學載體上的化學信號,再想辦法把這些化學信號轉譯為電信號。到了電信號這步就好辦多了,把電信號轉換為光信號,光信號再轉為圖像,這都是很成熟的常規技術了。這套技術路徑涉及把腦電信號轉化為血液裏的化學信號,再把化學信號收集起來,轉化為電信號、光信號,聽起來很復雜,實現起來就更復雜,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但是,只要有足夠的錢,總還是可以請科學家們試試看。趙新民最終采納了我的這個想法,這些年他壹直讓我跟著他,就是覺得我的腦子還有點用。
這個項目後來又進行了很多年,耗費超級巨大,每年數億數十億美元的投入,簡直堪比美國在1960年代的阿波羅登月計劃。耗費巨大,連趙新民這樣的居於食物鏈頂層的財閥都要想著再去賺些錢,維持研究的投入。做這些事情,需要有信得過的助手協助,所以我才有了機會,進入到了趙新民日常而又隱秘的生活,協助他完成那些日常而又隱秘的操作。這個階段,我們朝夕相處無話不談,我對他的了解才漸漸完整了起來。當然了解是相互的,這個過程我也幾乎把我的每壹個想法,甚至大腦裏的每壹個細胞,都坦露在了他的面前。我們互相信任,甚至互相欣賞,當然,趙新民對我的欣賞主要是覺得我的學習能力沒有讓他失望吧,而我所學的來源,則多是來自他的親自傳授。
這個無比燒錢的項目每取得壹點確定的進展,消息傳來,趙新民總是很興奮的要親自測試,這些測試我又總在他身邊協助。每次,當他在躺椅裏躺好,當我把收集化學信號的探針插入他的血管,這時候他腦海裏的記憶就壹點壹點的還原成了影像,投射在了我們眼前的顯示器上。
我記得,當第壹幀略微成型的圖像出現在監視器上的時候,我們都興奮到歡呼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