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便你選,就選最醜的顏色。」剛來畫室的華哥,時而沉默地觀察著大家,時而在他覺得不對勁時,主動提出要求,生怕自己被團體錯過了什麼。這麼做,是為了保護自己,說出的話有時尖銳,讓周遭的陪伴者會不太知道怎麼回應。
2021年畫室發展出一對一的學伴關係,記錄每一次課程的陪伴、對話,也確實地感覺到了華哥幾個回暖的瞬間。
大船漂漂,兩歲的華哥,來到臺灣,住進西本願寺一樓的違建,母親把兒女留給繼父,改嫁了;繼父覺得自己被利用,也不願多照顧留下的小華。貧窮處境影響了人際關係,雪上加霜的是,戰後臺灣的省籍衝突,也影響到懞懞懂懂的小華;操著外省的口音,他發現自己不被本省的同學接受,卻也沒有同行的外省朋友,到哪都感覺不能留下。
小學四年級輟學,遇到一個拉三輪車的車伕,幫著到處打聽哪裡有缺工,試了幾次,到三張犁的兵工廠當學徒後,生活才穩定下來,直到當兵。工廠的工作要直視強光,視力在缺乏保護措施之下受損。「就是一點一點地越來越糟」,今年已經七十歲的華哥說,現在左眼完全看不到,右眼僅剩微弱的視力。
退伍後,結婚、離婚、妻子外遇、認識溫哥華的女子、結婚、被搶劫、返台、打了三份工賺錢,勞保期滿時一次提清退休金,投資失利。曾經想要輕生,卻又因為機緣,燃起最後的求生意念,六十多歲的華哥,開始跟著街友,學習在街頭生活。
經歷了這麼多痛苦,華哥說,「不可能不去想,說不去想不在意的人都是在逃避。」後來,華哥在教會認識了惠姐,兩人說好作伴,但金錢各自獨立。惠姐說,華哥臉上都沒有法令紋,是因為他是孤兒,沒有愛,不會笑。「大笑會得意,低調一點、節制一點,會比較安全。」華哥說。
因為眼睛看不清楚,我們準備大張而厚的圖畫紙給華哥,讓他可以用手指感受到距離與邊界。畫畫的過程中,華哥漸漸收起爪子,說起複雜的往事,不再因擔心被批評而先武裝自己,「以前有過跟別人說的時候,別人會嘲諷說怎麼可能遇到這種事,被潑冷水;但沒關係,你不相信,還有人會相信,我跟一百個人講,總是有人會聽。」華哥是很願意說的,但是他說的方式、情緒,總讓人對內容半信半疑,「在這裡說出來就有被諒解的感覺;自然地談,比較輕鬆。」
華哥對自己嚴厲,和身體感受有關的主題,說自己現在的身體狀態是59分,夥伴問他要祝自己更好嗎?他說不用,年紀大了就是這樣,59分就好。因為眼睛不方便,坐在旁邊的夥伴幫他選顏色來描繪自己的人生,「隨便你選,就選最醜的顏色,」華哥總是這樣說;要是說覺得沒有什麼顏色最醜,華哥就輕笑,沉默。「生不逢時,」華哥為自己的生命下主題:「不,改成豬狗不如的人。」夥伴順著問下去,問了顏色、問了故事,最後華哥沉默了一下,臉上的肌肉漸漸放鬆下來,說,還是改成苦命的老小子。
選不出顏色的夥伴問惠姐,「啊,就選灰色啦!」惠姐的大方,直率地接住了華哥。
有時在課程的尾聲,氣氛變得歡樂,大家開始聊起最近的事。
「感覺好熱鬧喔,好多人在,很豐富。」
「你喜歡這種豐富嗎?」
「一個人待在家的時候很無聊,只會睡覺。這種豐富是一種世界的感覺。」
後來的課程裡,華哥用黃色和紅色描繪上課的感覺:黃色的葉子一層一層長出,紅色的區塊長出了愛心,是這半年不斷的、大家互相的愛。
「華哥會在什麼時候感覺到小小的、被愛的感覺?」
「像你這樣幫我整理故事、幫我做作品,我就有被愛的感覺。」
華哥靜靜地微笑,在午後的暖房裡,他好像找到一塊地,把自己安放。夥伴秋秋分享的時候,我們都有點感動,這好像是很久以來,他第一次談起了愛。啊,華哥以前從來不說謝謝,現在會坦然說謝謝、接受別人的好。生命其實很難改變,但是我們一起見證了這些微小的瞬間。
苦命老小子華哥:隨便你選,就選最醜的顏色。
留言
夢想城鄉的沙龍
17會員
20內容數
透過藝術和教育能夠幹嘛啊?沒有要回答這麼困難的問題,這裡是NGO工作者邊做邊想邊整理的樹洞,放些療癒月誌、創作教案、工作坊設計、心理學小練習(?)練習釐清自己、他人與社會的界線。裡面也許會有些美麗的小石頭,喜歡就拿去用:)
夢想城鄉的沙龍的其他內容
2022/10/16
藍波大哥曾說:「我是有家的無家者。」在脆弱畫室裡,他最常畫的,是小女兒最愛的小叮噹(多拉A夢),畫裡的小叮噹總是笑著,但去年,藍波大哥介紹時總有些無力;和他說話,常常只有簡短的回答⋯⋯

2022/10/16
藍波大哥曾說:「我是有家的無家者。」在脆弱畫室裡,他最常畫的,是小女兒最愛的小叮噹(多拉A夢),畫裡的小叮噹總是笑著,但去年,藍波大哥介紹時總有些無力;和他說話,常常只有簡短的回答⋯⋯

2022/10/16
這篇有4,095字,是對學員飛仔最完整的一次紀錄,也可能是最後一次。
/養母酗酒的日子裡,飛仔收到了兵單。揹上行囊,飛仔告訴爸爸,要去坐車了。養父點上一炷香,叫他自己去拜幾下,便坐了回去。飛仔拜完,又在門口站了幾秒,才點頭告別家人,開始三年的軍旅生活。退伍後再回到花蓮,飛仔發現自己的一切都不見⋯⋯

2022/10/16
這篇有4,095字,是對學員飛仔最完整的一次紀錄,也可能是最後一次。
/養母酗酒的日子裡,飛仔收到了兵單。揹上行囊,飛仔告訴爸爸,要去坐車了。養父點上一炷香,叫他自己去拜幾下,便坐了回去。飛仔拜完,又在門口站了幾秒,才點頭告別家人,開始三年的軍旅生活。退伍後再回到花蓮,飛仔發現自己的一切都不見⋯⋯

2022/10/16
小潘來到夢想城鄉2年多,最一開始在畫室,後來也到了木工班,疫情期間,我們對彼此,都有了更多新發現。在木工班,小潘慢慢發現原來工作可以是發揮想像的場域:木工老師教了一個基本原則後,就會放手讓大家嘗試,雖然身體疲憊,小潘卻有了一點成就感,也漸漸對工作夥伴有更多的信任,生出學習的動力。

2022/10/16
小潘來到夢想城鄉2年多,最一開始在畫室,後來也到了木工班,疫情期間,我們對彼此,都有了更多新發現。在木工班,小潘慢慢發現原來工作可以是發揮想像的場域:木工老師教了一個基本原則後,就會放手讓大家嘗試,雖然身體疲憊,小潘卻有了一點成就感,也漸漸對工作夥伴有更多的信任,生出學習的動力。

你可能也想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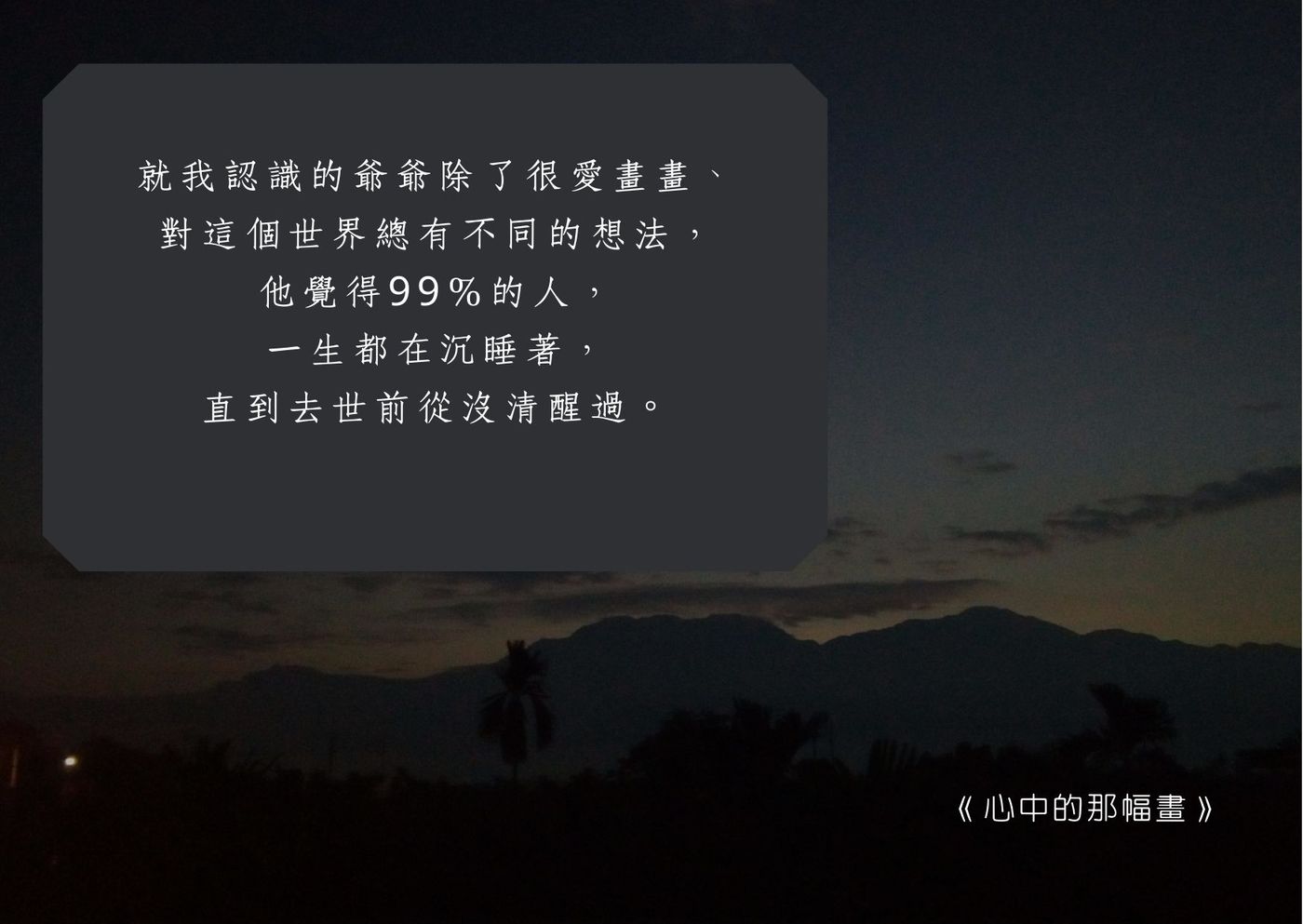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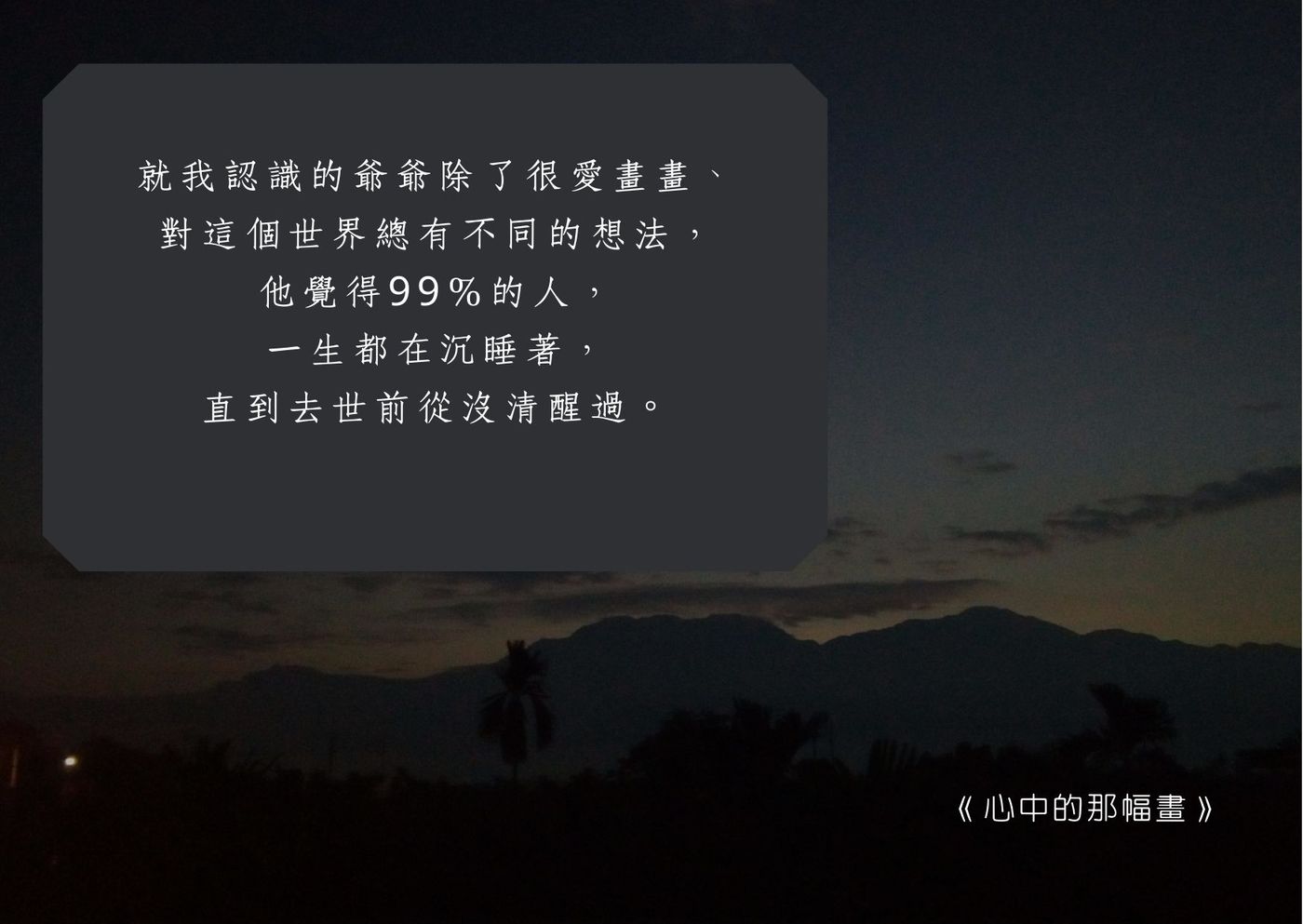











賽勒布倫尼科夫以流亡處境回望蘇聯電影導演帕拉贊諾夫的舞台作品,以十段寓言式殘篇,重新拼貼記憶、暴力與美學,並將審查、政治犯、戰爭陰影與「形式即政治」的劇場傳統推到台前。本文聚焦於《傳奇:帕拉贊諾夫的十段殘篇》的舞台美術、音樂與多重扮演策略,嘗試解析極權底下不可言說之事,將如何成為可被觀看的公共發聲。

賽勒布倫尼科夫以流亡處境回望蘇聯電影導演帕拉贊諾夫的舞台作品,以十段寓言式殘篇,重新拼貼記憶、暴力與美學,並將審查、政治犯、戰爭陰影與「形式即政治」的劇場傳統推到台前。本文聚焦於《傳奇:帕拉贊諾夫的十段殘篇》的舞台美術、音樂與多重扮演策略,嘗試解析極權底下不可言說之事,將如何成為可被觀看的公共發聲。

柏林劇團在 2026 北藝嚴選,再次帶來由布萊希特改編的經典劇目《三便士歌劇》(The Threepenny Opera),導演巴里・柯斯基以舞台結構與舞台調度,重新向「疏離」進行提問。本文將從觀眾慾望作為戲劇內核,藉由沉浸與疏離的辯證,解析此作如何再次照見觀眾自身的位置。

柏林劇團在 2026 北藝嚴選,再次帶來由布萊希特改編的經典劇目《三便士歌劇》(The Threepenny Opera),導演巴里・柯斯基以舞台結構與舞台調度,重新向「疏離」進行提問。本文將從觀眾慾望作為戲劇內核,藉由沉浸與疏離的辯證,解析此作如何再次照見觀眾自身的位置。

本文深入解析臺灣劇團「晃晃跨幅町」對易卜生經典劇作《海妲.蓋柏樂》的詮釋,從劇本歷史、聲響與舞臺設計,到演員的主體創作方法,探討此版本如何讓經典劇作在當代劇場語境下煥發新生,滿足現代觀眾的觀看慾望。

本文深入解析臺灣劇團「晃晃跨幅町」對易卜生經典劇作《海妲.蓋柏樂》的詮釋,從劇本歷史、聲響與舞臺設計,到演員的主體創作方法,探討此版本如何讓經典劇作在當代劇場語境下煥發新生,滿足現代觀眾的觀看慾望。

《轉轉生》為奈及利亞編舞家庫德斯.奧尼奎庫與 Q 舞團創作的當代舞蹈作品,融合舞蹈、音樂、時尚和視覺藝術,透過身體、服裝與群舞結構,回應殖民歷史、城市經驗與祖靈記憶的交錯。本文將從服裝設計、身體語彙與「輪迴」的「誕生—死亡—重生」結構出發,分析《轉轉生》如何以當代目光,形塑去殖民視角的奈及利亞歷史。

《轉轉生》為奈及利亞編舞家庫德斯.奧尼奎庫與 Q 舞團創作的當代舞蹈作品,融合舞蹈、音樂、時尚和視覺藝術,透過身體、服裝與群舞結構,回應殖民歷史、城市經驗與祖靈記憶的交錯。本文將從服裝設計、身體語彙與「輪迴」的「誕生—死亡—重生」結構出發,分析《轉轉生》如何以當代目光,形塑去殖民視角的奈及利亞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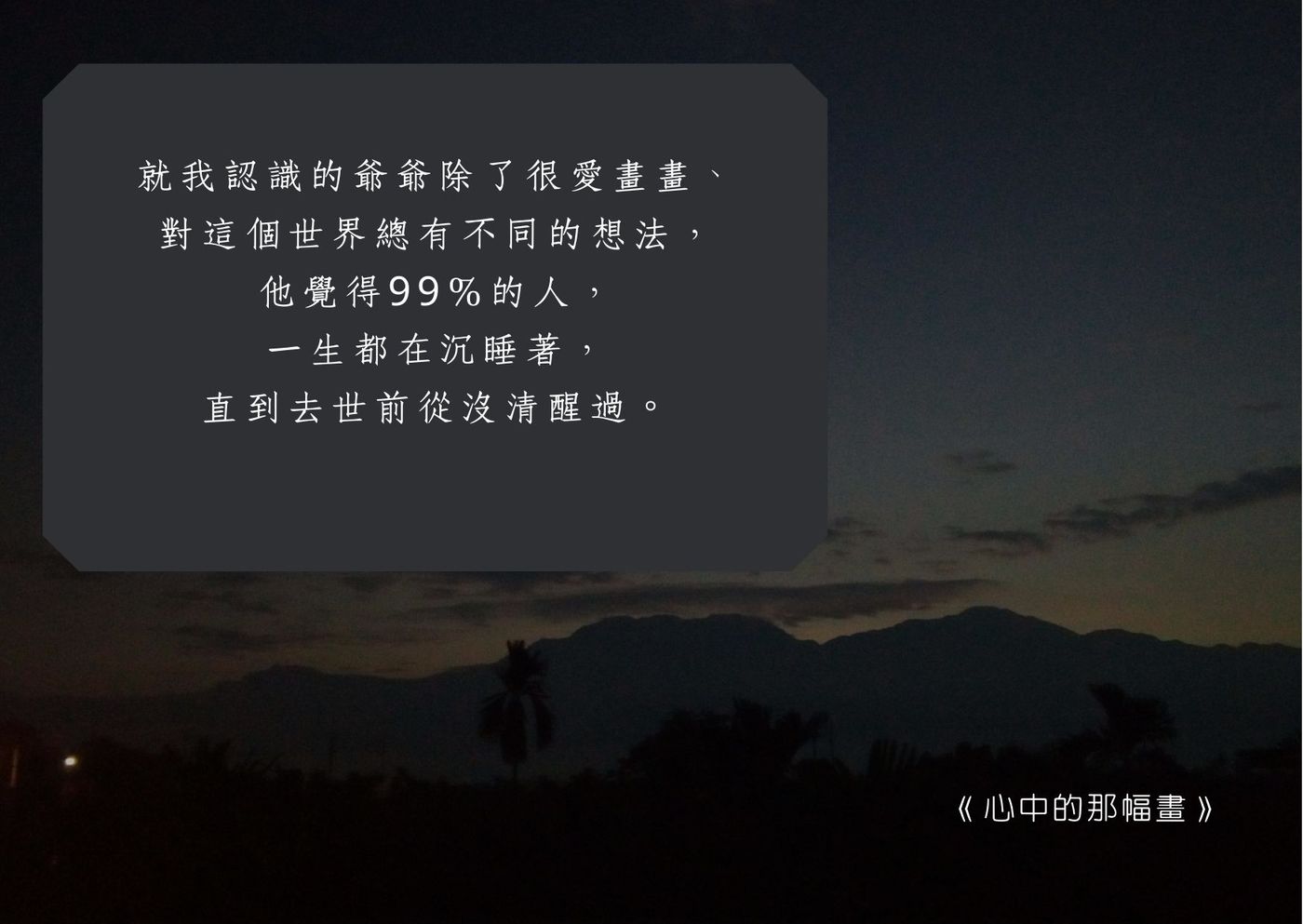
前情提要:
小男孩長大成為一位愛畫畫的年輕人,但殘酷的現實生活打擊著他的夢想,讓他在工作和感情上常常碰壁,也讓他常常處在負面和崩潰的情緒中。直到有一天在「工業公園」遇見一位蒼白瘦弱的小男孩……
午後的陽光死氣沉沉地照在這──灰慘慘的大地上,人們依舊如行屍走肉般地走在路上──但在有個小角落,不起眼的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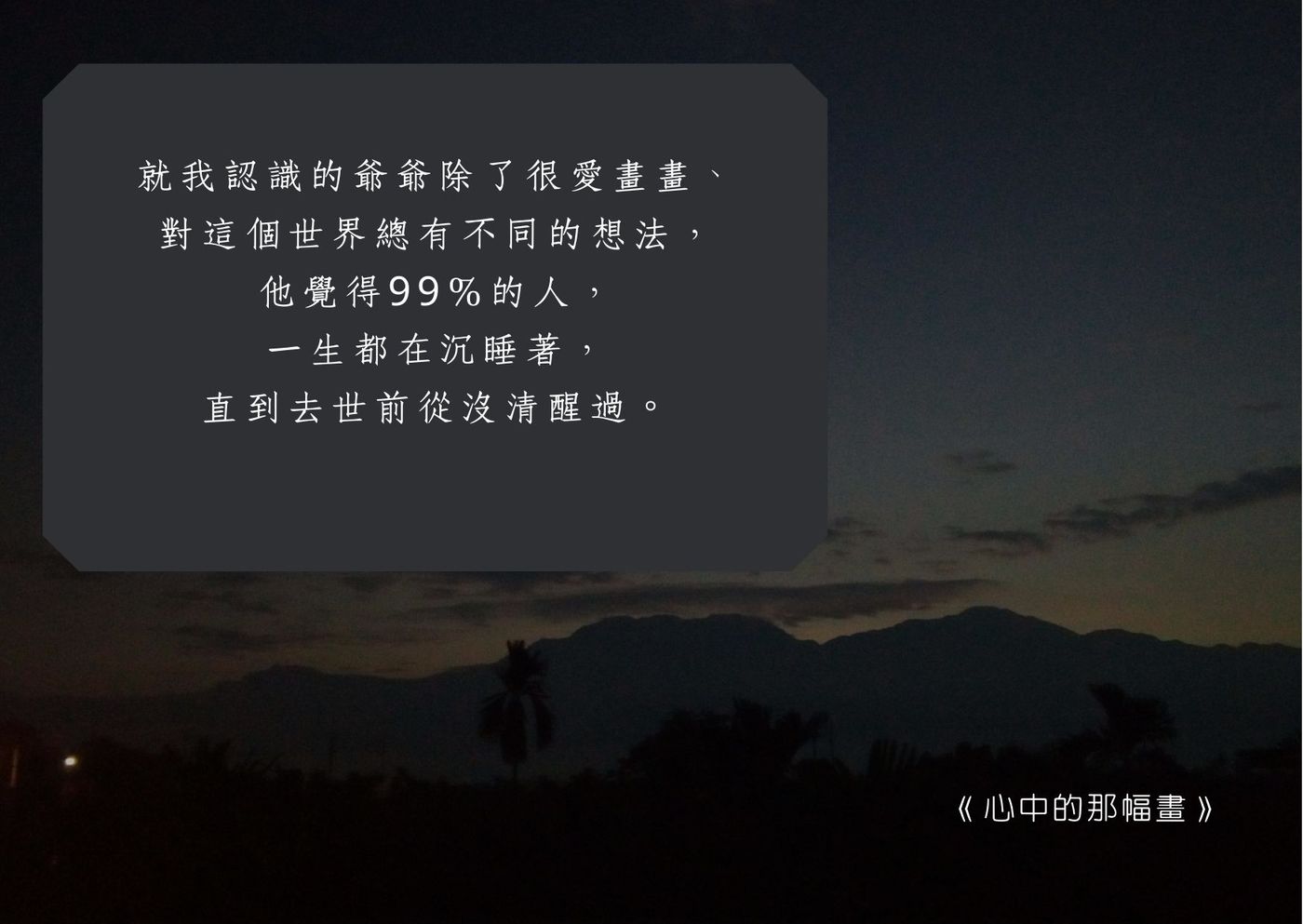
前情提要:
小男孩長大成為一位愛畫畫的年輕人,但殘酷的現實生活打擊著他的夢想,讓他在工作和感情上常常碰壁,也讓他常常處在負面和崩潰的情緒中。直到有一天在「工業公園」遇見一位蒼白瘦弱的小男孩……
午後的陽光死氣沉沉地照在這──灰慘慘的大地上,人們依舊如行屍走肉般地走在路上──但在有個小角落,不起眼的陰

剛來畫室的華哥,時而沉默地觀察著大家,時而在他覺得不對勁時,主動提出要求,生怕自己被團體錯過了什麼。這麼做,是為了保護自己,說出的話有時尖銳,讓周遭的陪伴者會不太知道怎麼回應。2021年畫室發展出一對一的學伴關係,記錄每一次課程的陪伴、對話,也確實地感覺到了華哥幾個回暖的瞬間。

剛來畫室的華哥,時而沉默地觀察著大家,時而在他覺得不對勁時,主動提出要求,生怕自己被團體錯過了什麼。這麼做,是為了保護自己,說出的話有時尖銳,讓周遭的陪伴者會不太知道怎麼回應。2021年畫室發展出一對一的學伴關係,記錄每一次課程的陪伴、對話,也確實地感覺到了華哥幾個回暖的瞬間。

在《華燈初上》中最喜歡的一對,其實是成哥與阿達,
每場師徒的對手戲,都好愛。
印象很深的一場戲,是那場在警車裡,只有成哥與阿達的一段對話。

在《華燈初上》中最喜歡的一對,其實是成哥與阿達,
每場師徒的對手戲,都好愛。
印象很深的一場戲,是那場在警車裡,只有成哥與阿達的一段對話。

「曾幾何時,有一段最真摯的感情放在我的面前,而我沒有好好珍惜......」
這句像曾相識的電影對白,套在友情上,sorry,不是太合適。

「曾幾何時,有一段最真摯的感情放在我的面前,而我沒有好好珍惜......」
這句像曾相識的電影對白,套在友情上,sorry,不是太合適。

柯達直到破產那天,生產的膠卷質量都很好的,只是世界不再需要它了。
電視劇看多了,看到「耳光」就想到女主角眼眶泛淚,眼睛紅通通(淚流滿面還可以這麼好看)得說:「爸!你打我!」,轉身淚奔……

柯達直到破產那天,生產的膠卷質量都很好的,只是世界不再需要它了。
電視劇看多了,看到「耳光」就想到女主角眼眶泛淚,眼睛紅通通(淚流滿面還可以這麼好看)得說:「爸!你打我!」,轉身淚奔……

你可曾想過,如果有一天,自己必須露宿街頭,那會是什麼場景?
「唉唷,全身髒兮兮的好臭,不要靠近我!」
「不去工作,整天在這裡騙吃騙喝,真可憐。」
這些對話,僅僅是小華日常生活的一小部分,一個無家可歸的唐寶寶,光是必須每天四處尋覓下一餐,就已歷經千辛萬苦,還得獨自一人面對周遭的異樣眼光。

你可曾想過,如果有一天,自己必須露宿街頭,那會是什麼場景?
「唉唷,全身髒兮兮的好臭,不要靠近我!」
「不去工作,整天在這裡騙吃騙喝,真可憐。」
這些對話,僅僅是小華日常生活的一小部分,一個無家可歸的唐寶寶,光是必須每天四處尋覓下一餐,就已歷經千辛萬苦,還得獨自一人面對周遭的異樣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