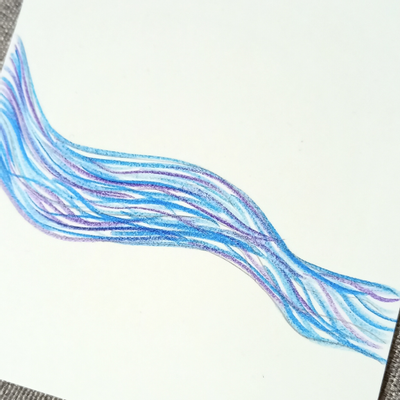寧靜的海面逐漸吞噬黃昏的餘暉,一對年輕男女被夜色驅趕前行,一路上肆意地述說愛意,女人告訴男人,他應該要跟女友分手,男人則以笑回應。那一晚的雷克雅維克如常地隨著規律的呼吸聲陷入沉睡,整座城市的意識潛入黑暗之中,等待下一道晨光從洞口透出,然而就是那樣稀鬆平常的早上,隧道中迸發的火光佔據了車窗外的視野,有的人則再也沒有醒來過。

原先要前去與現任女友分手的Diddi不幸地於意外中喪命,而現任女友Klara不但對此毫不知情,還在得知死訊後隨即飛奔前來,作為地下情人的Una,不得不一邊面對失去愛人的悲慟,一邊安撫Klara,同時還要在眾人面前掩飾自己真正的心情,複雜而幽微的念想,散落在不經意的細小言行之中,《薄暮微光》表面上談論的是人們的「失去」,實際上更體現出的是「擁有」,失去同一個男人的兩個女人,Klara自高中便與Diddi交往長大,理所當然擁有作為正宮傷心的權利,而更為理解Diddi內心的Una,則擁有他最毫無保留的此時此刻,實際上從Klara批判行為藝術與Diddi創作理念的態度,確實不難想像為何Diddi的內心更傾向Una。

或許是因為這段出軌從未說破,抑或是兩人多少都對對方的底細心知肚明,原先乍看應當對立的Una與Klara,在相處的過程裡,不但逐漸放下敵意與質疑,也像是透過對方的眼淚,間接療癒了自己失去的那一部分,如同Una課堂上三個纏滿膠帶的人所呈現的行為藝術,無法擺脫的交集在經歷失衡、碰撞與擠壓的掙扎之後,還是有辦法隨著互動取得彼此都能接受的折衷,而Una在教堂前飛行的敘述性詭計,玩弄的概念是「垂直來看高不可攀的事物,只要改變焦點,換作水平視角也能是俯視」,即便對她而言這只是為了讓Klara理解觀看藝術的視角,但她當時沒意識到的是,這點套用在「自己究竟能否以戀人的身分悲傷」這件事本身也是成立的。恍惚之間,曖昧的窗光勾勒出擺盪的樹影,不約而同出神的凝望,在錯視與透視的角度裡彷彿交疊出了同一個身影,各別握有過去與現在的兩人,在失去了交集的男人後竟也變得互補而平等。

另一方面,Una兩次踏入Diddi與Gunni的家的身份轉換相當有意思,最開始作為地下情人的她奪取了Diddi的牙刷,並笑著「允許」他用Gunni的牙刷,在愛人面前展現著「女主人」的權勢,而當Diddi不在時,自己卻只能狼狽地從後門翻牆逃跑避免被Gunni發現,再到第二次跟著Klara回到這個家時,礙於身份,Una只能表面裝作陌生,端詳著Klara的臉色並唯唯諾諾地跟在她身後,而在同一個浴室的刷牙場景裡,兩個人則同樣因為這個家沒有屬於她們的牙刷,而平等地用手指各自抹上牙膏,牙刷的所有權巧妙地闡述了不同身分對應的關係,而兩人整齊劃一的動作也像是再次強調了彼此的對等。

Klara在等待日落時,覺得那樣的過程像是在跟Diddi告別,於我來看其實是點題了「一個人終究無法屬於任何人」的事實,如同太陽的遙不可及,也如日暮時分不會因為任何人的眼淚而停留在那一刻,失去愛人的痛苦宛如在她心上刨掉一塊血肉,但Klara不知道的是,Diddi的心裡早已沒有了她,而對Una而言,她曾冀望那份讓關係見光的名份能讓她擁有說愛的自由,然而這樣的念想卻讓她因此失去了愛人。在失去與擁有的流轉之間,她們以為自己擁有的,其實從不真正屬於她們,逝去的故人已然黯淡,來自身旁的擁抱卻依然溫暖而真切,日復一日,薄暮的微光終將消逝,也始終會再度來臨。

不過若要以我的喜好來說,《薄暮微光》整體實在有些過於平淡,因全片更聚焦在角色細微的言行舉止,沒能更加以利用唯美的自然風光,或是利用災難元素去做延伸還是不免讓我覺得有些可惜,雖然電影選擇了很不一樣的角度來談失去與擁有,而我也認為其中隱約感受到的關係角力是有趣的,但本片也就僅止於最簡單的敘事並始終保持克制,能帶給觀眾多少的感受很取決於每個人的敏銳度,而對我來說,大概只算是很有意思,但不至於在內心激起太多波瀾的作品。
IG:閣樓的放映室(@theater_in_the_at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