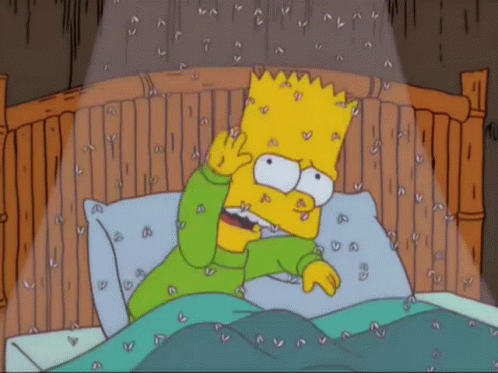每到暑假,藝文活動百花齊放,紛紛從都市的水泥罅隙中冒出。不讓台北專美於前,繼高雄創價美術館之後,嘉義故宮南院也延續這股熱潮,接棒推出【江戶浮世之美】,聲勢浩大,一派熱鬧。
我趕在「江戶名所圖屏風」展期最後一天趕到,適逢週日,人潮可想而知。為了給自己一點喘息空間,也為了偷一點不那麼喧囂的展場品質,我刻意把入場時間延後到下午五點。沒想到一走進去,就被眼前一左一右、彎彎繞繞的兩條人龍嚇得呆立原地。詢問現場人員,才知道:一條通往屏風、一條通往海浪。

我有些踟躕。想到當年在京都市美術館的葛飾北齋展,一個人興致勃勃地買票,加入隊伍尾巴,拉長脖子等待入場。那日陽光太盛,在牆邊曬到頭有些發昏,好不容易轉進大廳,才發現又是另一幅排隊地獄景象。
三個小時的入場等待,換來華麗而完整的作品清單,當然、也包含舉世聞名的「富嶽三十六景」。那次看得酣暢淋漓,但也落下了對人潮的陰影。如今回到台灣,實在不願重陷那彷彿無止盡的煉獄。於是,我悄悄鑽進隊伍後方無人駐足的展台。
主題多元,但件數有限。從歌舞伎、美女特寫「大手繪」、掀開屋頂窺視吉原遊廓的繁花與疲倦,到江戶人的生活日常,故宮還特別應景地選了數幅夏季的風物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