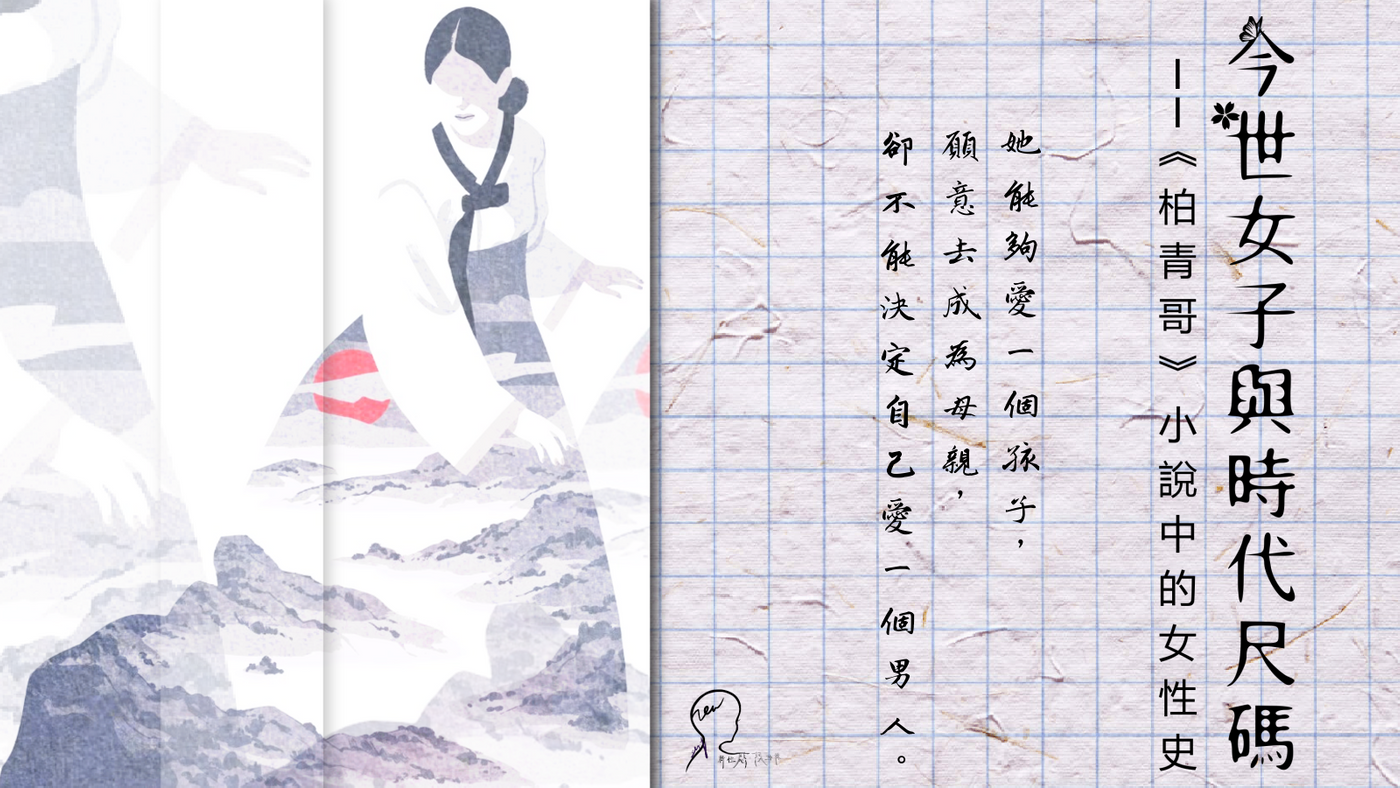她能够爱一个孩子、愿意去成为母亲,却不能决定自己爱一个男人。这是历代女性共同的困境,像是每一个东亚女人生来就受到的诅咒。
这一期谈变迁的爱情观,我相信,事物发生改变的主因不一定是时间,但时间一定承载着这种变迁。爱情这个小东西,好像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但又是最绚丽夺目的,它可以解释那些无法被解释的一切,是命运的齿轮中最精巧的一环。
我选择的例子是小说《柏青哥》中的四代女性跨越了六十年、有过苦楚,但分别闪耀着的爱情。这部小说因近期开播的美剧《弹子球游戏》而炙手可热,讲述的是朝鲜半岛上一个普通家庭从战争年代起历经四代人的移民故事。它有一条清晰的时间线,而我在其中捕捉了爱情,我只对这一样着迷。
其实说是“四代女性”是不够准确的,因为我要讲述的这些女性,她们几乎没有血缘关系,好像只是在最初、或者在枝桠的末端以虚线相接,因为共同爱着一些男性而走到了一起,但并不妨碍她们的光芒闪烁。第一代:“女人天生就是受苦的命”
第一代女性生长自20世纪初日本殖民时代的朝鲜渔村,她叫杨金,因为家境贫困而被父亲早早打发嫁人。由媒婆上门说亲,十五岁的杨金嫁给了二十八岁的候奈,他天生唇腭裂,有一只脚畸形。新郎和新娘在婚礼当天才见第一面,此时也谈不上什么爱情,杨金只是感觉自己不害怕这个男人,她的丈夫。
小说正面刻画杨金的部分并未提及他们对彼此关于爱的想法,所谓“爱情”的细节,好像两人所有的爱都付出给了不断夭折的孩子。“只剩下杨金和她的长子单独在一起时,她用食指划过婴儿的嘴部轮廓,吻了吻孩子的嘴;她从来都没有像爱她的孩子那样爱过任何人。”杨金变成了一个母亲,这个身份好像比“妻子”更加强烈。所以在几个孩子都不幸夭折之后,她独自去找了巫医,最终诞下第四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孩顺子。
顺子十三岁时,候奈去世。年轻的寡妇杨金毕生的心愿变成了抚养女儿顺利长大,而她对候奈的那些心事也就无从知晓了。往后只是通过顺子的回忆看到他们相处的细节,候奈尊重自己的妻子,即便有客人,也与她们同桌吃饭。顺子认为那是父亲对母亲的爱,我们也不能狡辩说不是,毕竟她活在小说中,活在杨金与候奈之间,要比我们更明白这一点。但母亲呢,顺子知道母亲爱着父亲吗。好像没有,她依赖他,在遭遇困境时会想起他,但也许这是一种爱情,只是不那么强烈,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发生在每一个普通人身上。
第二代:“妻子必须忠于丈夫”
第二代女性自然是顺子,她可以算作是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前前后后的故事几乎都由她串联。在小说中,顺子与已婚的掮客高汉秀相恋,“你有心上人吗?”到这里,我们好像终于看到了不同于第一代女性所经历的爱情——没有人曾问过杨金,你有心上人吗,她很快就被仓促嫁给了一个并不相识的人,并坦然接受自己的命运。
小说花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顺子对高汉秀的爱情,她并不知道如何才能让自己变得可爱,以此吸引自己的心上人,但是她想过,她始终让自己保持干净整洁。“她见他的次数越多,他在她心里就越显得生动。”但是在得知对方已婚、自己只剩下当情妇一条路时,这个十多岁的少女、和她母亲结婚时一般年纪,毅然决定斩断他们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她想起自己的父亲,想起他如何爱自己、爱母亲——也许这是一种征兆,她不再信任这种滚烫的感情了,而选择复归于过去父母所经历过的那种平淡。当即将前往日本大阪的牧师白伊萨向她提出求婚、要做孩子的父亲时,她同意了。
为了娶顺子,白伊萨与另一位申牧师关于上帝的辩论很精彩,但是一落到这桩具体的婚姻上不免世俗,甚至有些可怖。顺子“意识到这桩婚姻是有条件的,但很容易接受;可惜他没有办法考验她的忠诚。你如何证明你爱上帝?你如何证明你爱你的丈夫?她永远不会背叛他;她会努力照顾他,她能做到这一点。”顺子年轻的爱情夭亡,她选择了和母亲同样的路——或者又根本不是她自己选的,母亲当初也没得选。
后来随白伊萨移民到日本,体质本就孱弱的白伊萨被卷入政治,在监狱中饱受折磨而死,留下沉默、坚韧的顺子。此时高汉秀又不断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她偶尔想到亡夫白伊萨,也只是因为困惑,她的心上人是高汉秀还是白伊萨?她摆脱不掉高汉秀,一如摆脱不了自己对他的爱情。但是她仍像母亲,将所有的爱付出给两个孩子。“顺子的确相信。她以前爱高汉秀,后来,她爱着白伊萨。然而,她对两个儿子诺亚和摩撒的爱,要胜于她对那两个男人的爱——两个孩子就像她的命。”因为要保卫孩子,她坚韧地活着,作为一个母亲。
顺子的嫂嫂庆熙虽然没有成为一个母亲,但是她在面对两个男人的爱情时也做出了相同的抉择,和她们的上一代别无二致。但上一代似乎还没有机会经历动荡的爱情,所以勉强能够平淡如水地过下去,可以别无所求。但顺子与庆熙涉足了另一片水域,沾湿了鞋袜似的又重新退回来,知道自己不能再往前一步了,这种退回来的坚守足以让她们痛苦一生。
第三代:被男人憎恨的好奇心
第三代女性是由于与上一代共同爱着一些男性而走到一起,走进我们的视线。顺子生下的两个孩子诺亚和摩撒长大成人,相比起前两代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他们的生活好像终于有了起色。
诺亚勤勉好学,考上了早稻田大学,人生寄托是英语文学。他遇到的第一位女性叫付牧明子,是学校的“美女激进分子”,非常聪明。小说并没有过多对于明子的正面描写,她爱上这个有点忧郁的、沉默的朝鲜男人,会在床上要求他用朝鲜话夸她漂亮。因为有大量来自诺亚的角度对这段关系和这位女性的评价,看起来她似乎爱上的是一个朝鲜人,她在乎他作为朝鲜人的身份(诺亚讨厌的也正是这一点)。但可以从他们相处的时光来看,这是一段美妙的爱情,在上一代女性之中似乎还未来得及发生。也许是因为出身背景的不同,明子上大学,在课堂上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哪怕是尖锐的、惊世骇俗的,“你觉得女人会因为到了六十岁就不想要性生活了?”故而她选择自己所爱也是,像是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跳。
但是诺亚没能逃出对他身份的诅咒,他深陷这一点而无法自拔,表面上看是向上一代人发起挑战,隐姓埋名过上自己选择的生活,但他放弃明子,而去选择一种更安全的关系,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可怕的复归。诺亚的第二位女友,也是最后一位,里莎出现了,她和诺亚是同事,负责管理一家柏青哥游戏厅的档案室,后来也用这种能力管理自己与诺亚生下的四个孩子。小说仍是没有正面描写里莎,我们只知道诺亚被她漂亮的手写体所吸引(它是浪漫的,似乎只有这一点符合诺亚曾经寄托的东西)。从诺亚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婚姻关系很稳定,一转眼就过去了八年。这对夫妇从不吵架。诺亚对里莎的爱与他对大学女友的爱不一样,但他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他发誓,他再也不会让别人伤害自己。”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在丈夫诺亚不堪忍受、自我厌弃,最终选择饮弹自尽的情况下,里莎可以像上一代女性一样,沉默而坚韧地,独自将四个孩子抚养长大。她将自己的爱情隐姓埋名,使自己成为一个永恒的母亲。或许这也是诺亚选择里莎的原因。
与哥哥不同,摩撒早早放弃学业,开始经营柏青哥游戏厅。他遇到的第一位女性由美,出身贫寒,刻苦地学习英语,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语言,美国是最好的国家。由美与摩撒相恋,他们相处的细节与上一代顺子和高汉秀竟有几分重合,但缺少了阻碍。她向往搬到美国,摩撒则不然,但最终由美意外去世了,好像不该有这种梦想。第二位女性是惠津子,因出轨而被逐出家庭。她有过许多男人,但并不接受摩撒的追求。从摩撒的角度来看,惠津子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不使孩子恨她而作出的这个决定。但经由惠津子的女儿花子之口,我们终于懂得,惠津子之所以不愿嫁给摩撒,是因为她不想被人评判。“你以为自己是受害者,其实不然。你离开是因为你害怕,你和那些男人上床是因为你害怕变老。”
惠津子与摩撒之间的爱情已经没有什么强大的阻碍,似乎只要她说愿意,就能得到一个圆满的结局。这似乎也回应着第二代女性顺子的爱情和选择,但是惠津子说不,她还是选择自己能够接受的方式与摩撒相守,虽然未能结合,但他们也一辈子没有分开,直到死亡。
这一代女性中还有一位令我印象深刻的,她就是彩女,嫁给了男同性恋春希,过着日复一日单调贫乏的生活,却自以为是幸福的。直到某一天偶然撞见了丈夫在树林里与另一个男人做爱,有些东西在她心底悄然改变。
彩女是被春希的母亲选中的女性,服从,忍耐,与上一代女性有着强烈的相似性,她们都会沉默着吞下秘密,终其一生都会为他人犯下的过错承担责任,受尽苦难。当她意识到自己无法与丈夫发展爱情,甚至连一个孩子都不能养育,于是加倍地将母爱付诸于春希那患病的弟弟身上。
但稍微不同的是,彩女曾试探性地踏出一步,尝试求索关于“性”的秘密。在撞见丈夫与他人做爱的那个树林里,彩女受到了一个年轻女孩的引诱,她忍不住再次踏足那片土地,却不是为了丈夫,更像是寻找内心的答案。“尽管她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却再也不能在澡堂简简单单地洗澡了。彩女每时每刻都想起那个女孩:做金色松糕的时候,擦家具的时候,无不如此。”彩女最终走出家门去了,去赴那个女孩的约。但就在她们之间要发生点什么的时候,彩女突然崩溃了,大骂着逃离现场。也许是因为女孩提到了钱,令她感觉到羞辱;或者想起自己的丈夫也会在这个地方做这种事,她出于愤恨而想要与之划清界限。总之,彩女的试探失败了,她最终又退了回去,假装无事发生,并继续那日复一日枯燥无味的生活。
第四代:被诅咒的东亚女性
小时候就立下志愿要生五个孩子的摩撒,最终只得到了所罗一个;而对此不曾言语的诺亚与妻子里莎一共诞下了四个孩子。但当诺亚选择自杀——或许更早之前,他选择离开家人、过一种隐姓埋名的生活时,他就注定从这株家族树中隐去。
从第一代的杨金到顺子传承下来的男性血脉不断凋零,最终只剩下所罗,他从十四岁起就爱上了上一代女性惠津子叛逆的小女儿花子。父母分开后,花子与母亲保持着关系,但毫无起色。她深爱着母亲,甚至去商场的香水柜台寻找母亲身上的气味。
这位生长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的女性,却莫名重演了与第二代女性相似的命运。花子第一次出场,是打电话给母亲,说是自己怀孕了,希望母亲协助解决这件事。相比起第二代女性顺子的遭遇,这个年轻女孩身上具有一种“轻快”,但也许造成她痛苦的原因正是这种“轻快”,任何一样东西都来得又薄又快,让人绝望,应接不暇的绝望。十几岁的花子早早步入欢场,看似享受又十分痛苦,无论怎么选都挣脱不了。有人形容她身上有“嬉皮士”的作风,结合她的年代再加上种种行为,似乎并无差错。但真的这样就能概括吗?花子的问题也许来自上一代女性未能解决的困境。
花子曾尖锐地说出了对母亲惠津子的了解,认为母亲只在乎自己是否被他人评判,致使其无从选择自己的爱情。所罗很早就接受了惠津子,希望她成为自己的母亲——惠津子能够爱一个孩子,却仿佛不能决定自己爱一个男人。这就是与前几代女性相似的困境,像是每一个东亚女人生来受到的诅咒。
被说成是拥有“嬉皮士”作风的花子试图逃脱这种梦靥,但她还是不能够爱所罗。或许是因为她已经清楚地察觉到所罗身上笼罩着的强大命运,知晓他最终会走向某种复归,选择具有沉默、保守、坚韧的品格,港湾和寄托式存在的女性,才能使家族或者是国族顺利绵延下去,按所有坚守下来的人所设想的那样。
花子必须成为一个幽灵,不仅仅是死亡,她活着的时候就必须成为幽灵,只能偶尔飘进这个家族,小心躲避人群,与所罗偷偷约会。她是被排除在外的,因为她不能像自己的母亲,也不能像这个家族历代所述的每一个坚守下来的女性:她们沉默而坚韧,经历挫折后将爱情隐姓埋名,义无反顾地选择成为母亲。
于是我们也想起第三代中被诺亚舍弃的明子、摩撒那向往美国最终意外身亡的妻子由美,她们都成了相同意义上的幽灵。
这一代的最后一位女性是所罗后来的女友菲芘,她的祖先虽然是朝鲜人,但她完全来自一个崭新的世界,仿佛不曾受到与前几代女性相同的“诅咒”。于是就在所罗作出要继承父亲的游戏厅产业的决定时,她终于毫不犹豫地结束了这段关系。
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是,菲芘最终会回到自己熟悉的世界中去,相比起那些不愿意接受命运便会成为“幽灵”的女性,她似乎有更好的结局,她的爱情仍会生长。
写在最后
看完这部小说后,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想要讲述小说中不同时期女性的爱情故事,并以《今世女子与时代尺码》为题。这个题目是偶然所得,拆开来分别是街上两家不同的招牌,但就在同一天晚上接连闯进了我的视线。我默念着,它们好像就连在了一起:“今世女子”与“时代尺码”,它们像是在强迫我注视着什么。小说《柏青哥》里交代过的每一位女性在我心中不断闪现,她们仿佛对应着自己的“时代尺码”,或者可以说是掌握着自己的“时代尺码”,总而言之,她们是不同的,各自闪耀。或者又被相同的命运牵引和束缚,最终得到了,又不可避免地失去些什么。
我擅自挪用了街边招牌和它们的字面意思,从而生造了像“一个女人和她的时代尺码”这样的句子,或许是因为就连我自己都还不明白内心的冲动是为什么。透过前述的这些女子群像,我心中的波澜还是经久不散,但或许可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了。无数女性的命运组成了我们,过去的未来的,我们不仅向身后看,她们也会在弯腰捡起什么的瞬间看向前方。
但请原谅,我并没有谈到“今世女子”,因为我只认得这个时代的我自己,以及少部分的女性,甚至都还谈不上认识。我只是在体会“她”,然而还不能够发现“她”并评价“她”的特点。但“今世女子”又是确实存在的,她就是你我,通过回望过去的一些女性,现实的、文学的,她们如何分辨、思考、选择,这就构成了她们的“时代尺码”,尽管并不是由她们自己来言说的,我们因此也可以确信,有些东西正随着时代在起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