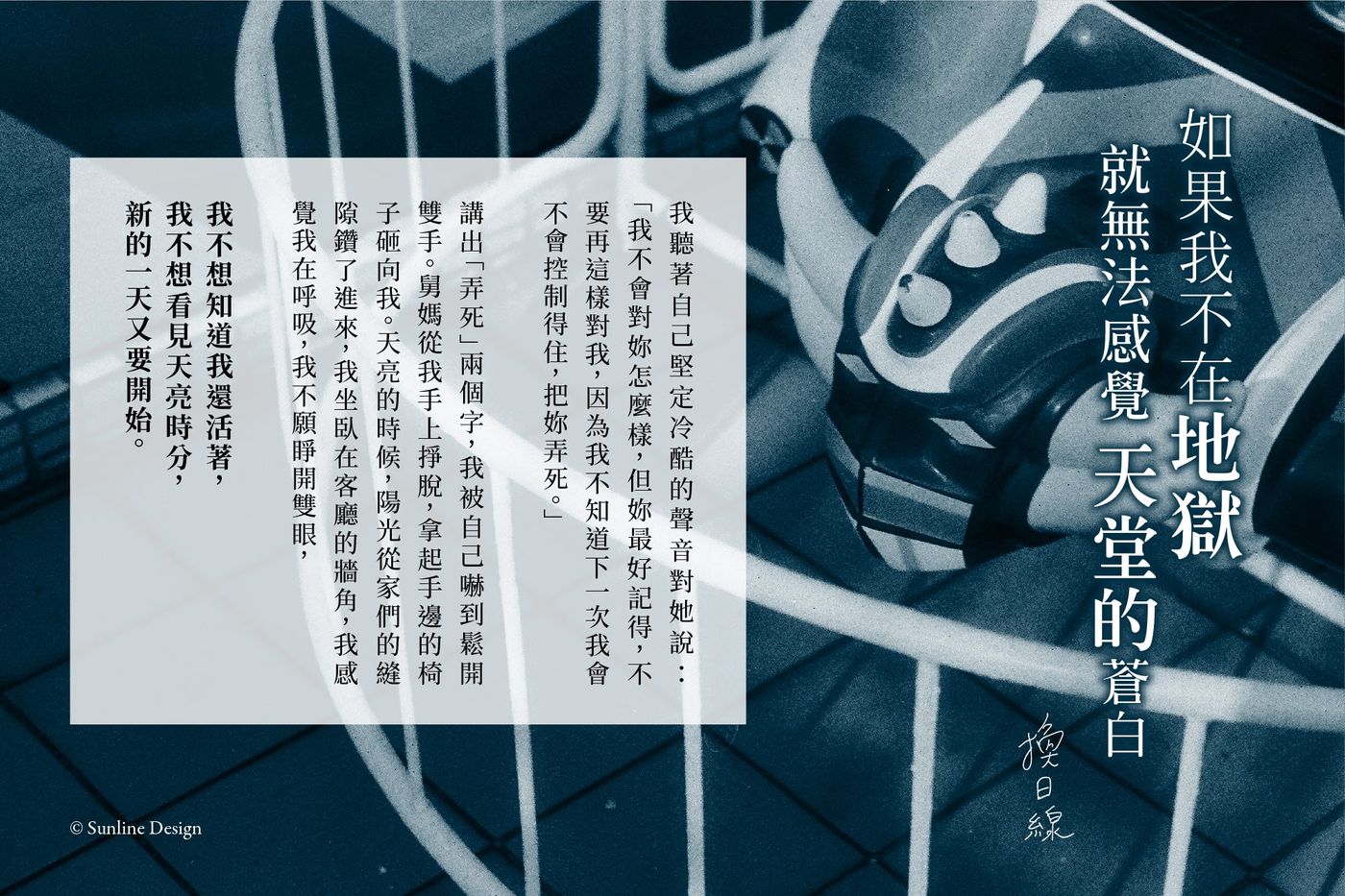「倩雲... ...」
眼前的天正仍然是一臉溫柔與我對望。
「我要走了... ...」
我如夢初醒:「甚麼?你要去哪兒?」
他掛上一個平淡的笑容。
「永別了... ...」
隨之然後,他的臉被黑布幪上... ...
這時,我才意識到將要發生甚麼事——阿正的脖子已被套上索環。
「不要... ...不要!」
阿正好像鏡頭被拉遠,很快離我很遠。
「Thump!」
他就這樣掉下去。
「啊!」
我彈起來大叫。
「倩雲!」天正也彈起來——從他的聲音之中,我聽出他之前睡得十分熟。
我立刻緊抱他——不讓他離開我半分。
天正感覺到我的驚恐,就用他那強壯的手臂圍著我,柔聲道:「別怕!別怕!我仍在。」
我仍是牢牢地抱著他——他輕輕地拍拍掃掃,用以安撫。
正式來說,他整個身體都在安慰我——並且十分有效。良久過後,我的心情逐漸平伏過來。
而他也曾經在我受到巨大震撼時如此安慰我。
「來,來,咱們坐起來好嘛?」
「嗯!」我點點頭。
在天正的撐扶之下,我們依在床板坐起來——而我依然像一個小女孩抱著玩具熊那般抱著我的丈夫。
「幸好嗣揚被爸爸抱回他的宿舍... ...」
「否則連他也被嚇醒。」我接道:「大家都不能再睡覺。」
「明天是星期天,咱們也可以在這兒休息... ...我星期一才要回囚室。」
「嗯。」
我嗅著天正身上的肥皂香氣。爸爸容許我為他購買日用品,並且沒有牌子限制——只是只可以買肥皂而不可以買梘液。
我曾經詢問原因。爸爸就說:「就是防止自殺——雖然囚犯也可以吞肥皂自殺。」
「正... ...」我懶洋洋說:「你從來沒有想過自殺?」
「沒有... ...」他的語氣也是懶洋洋。
他的鼻子湊過來,嗅著我的頭髮。
「剛才你做甚麼惡夢?」
「夢見你被處決。這一回,你真是掉下去。」
聽到我如此說,阿正將另一隻手放在我的身上。他將手指扣在一起,將我圍起來 ——現在大家都在彼此的懷抱之中。
「對不起... ...」
「為甚麼要道歉?」
「如果不是我那一個要求,上次你也不需要在刑場看著我要被處決... ...」
之前當阿正的死刑執行日期確定的時候,他提出可否讓我在最後時刻為他拉奏小提琴。在我立刻答應的同時,爸爸也允許他這一個「最後要求」。
「想不到,爸爸挺寵我... ...」
「他也寵我... ...」
「他寵你是應該的!」阿正迅速接道:「可是,我只是一個終生囚犯。現在更是一個死刑犯... ...」
他深呼吸一口氣。
「我知道他不想我受到有幫會背景的囚犯騷擾... ...才安排我做晚間清潔工作。」
「所以你星期六上午不用工作?」
「嗯!」他點點頭:「星期一至五,我就在木工場工作八小時;然後是三小時的晚間清潔工作。如果學校需要找代課老師,我又會被安排去那兒工作。」
「聽起來挺忙碌... ...」
「我們是最便宜的勞動力嘛... ...」天正自嘲著:「不像外面的工廠需要付市場的工資。」
「難怪那天你說以之前的工資是不可以買長笛... ...」
「嗯... ...」
「我真是想不到你會懂得吹長笛... ...」
的確,阿正不時都會給我意外驚喜:第一次送小禮物給我﹑「利用」我去「乘亂逃獄」﹑求婚... ...以及那一天的小小演奏。
我知道他所有行動都是在爸爸容許之下而做... ...
「對了!爸爸要我去學校當數學老師。」
「啊?他沒有跟我提過... ...」
「可能他覺得這是小事一宗,不需要說吧。我跟他說過,將我的工資存入你的戶口。」
「甚麼?」我驚訝:「那麼... ...」
「我現在要錢來幹甚麼?一日二十三小時待在囚室,一小時在外活動... ...三餐都是監獄供應... ...我甚至連香煙都節省下來!」
「香煙?」我愕然 ——阿正應該沒有抽煙的習慣;至少他沒有在我面前抽煙。
「你好像不抽煙?」
「沒有... ...可是囚犯之間是用香煙做交易——在剛哥的指點之下,我轉為煙民去領香煙。否則我不可能買雕刻工具製作那小項飾。」
「原來你不是在工場製造的?」
「怎有可能?一不想獄警們注意,二是覺得工場的工具不就手。就拜託剛哥幫忙。」
以前我與天正只是每個星期在爸爸的辦公室之中為他拉奏小提琴時才見面。當時,我看不出他單人匹馬去殺掉四個黑幫頭目(應該說,他看來不像)。即使後來成為夫妻,我仍不知道因由何在——直到那一日,我們到醫院去探望他那仍然昏迷的妹妹,我才知道箇中因由。
「我有時覺得我從來沒有進入你的生活圈子之中,卻成為你的丈夫... ...真是十分不足。」
我何嘗也不是沒有這一個想法——以前總會有一種「憐憫者」的「傲慢」,大家都談不上是「朋友」。
「如果,當日我真是被處決,一定會跟惡魔們討價還價... ...」
「你肯定是惡魔來接你走?不可以是天使?」
「怎可能是天使?天堂怎有地方容納我這種罪人... ...」
他這樣一說,令我感到內疚。
「那麼,我也可能會跟你落地獄... ...」
「甚麼?」阿正稀奇。
「我算是犯了『七宗死罪』之中的『傲慢』。」
「你不算!」
「以前我如此任性要為你拉奏小提琴... ...該是一種『傲慢』吧。」
「就看對方介意與否... ...」阿正悠然道:「剛巧我不介意。」
「如果你不是一個囚犯,會不會介意?」
「介意些甚麼?」他微笑著:「不過忠勁會取笑我;而遇教授會覺得我一反常態。」
「天正... ....」
「甚麼?」
「可不可以讓我聽你的心跳聲?」
「好的。來吧!」
天正放開懷抱,讓我移近一點。
我將頭髮撥開,將耳朵貼在他的胸膛上,聆聽他的心跳聲。
噗通,噗通,噗通... ...
充滿生命的節奏——配合阿正溫暖的身軀,令我感到十分安全。
「感覺如何?」
「充滿活力,節奏感十足... ...令人感到生命力的同時也令人感到安心的。」
「可是,我是一個殺人犯... ...」
「你又想說甚麼?」
「沒有甚麼特別意思... ...只是道出事實而已。」
「我現在無法想象聽不到這心跳聲的日子如何度過。」
「倩雲... ...」
天正像是欲言又止,呼了一口氣來。
我不是第一次如此做。上一次是我們新婚之時。那時,我用「要好好記住這聲音及感覺」去體會——因為我知道我只有一次機會,我就告訴自己要好好珍惜這個機會。
當時,爸爸讓我們共處一個星期作為蜜月,之後就回復一星期見面一次。
「實在,我現在也有點迷惘... ...要做的事已經做了,要說的話已經說了... ...我應該沒有遺憾。」
聽到他這一句仍有「準備就義」感覺的說話,我或多或少有點失望。
「仍是一盞『牛皮燈籠』!」
「上次你說你會為我守寡,我受寵若驚。」
我驚訝:「為甚麼?」
「我不值得你如此做... ...」
我想反駁,可是他比我更快:「就是因為你是我的妻子,我才會如此說。」
「可是,我也是因為對你的愛,才會作出『守寡』的決定。」我幽幽回道:「 一個帶著孩子的女人很難有男人接受... ...再者,這個世界應該沒有一個男人做到你做出來的事。」
「嗯... ...」阿正抿著嘴:「可是,我不可以將更好的留給你... ...」
我止住他的說話:「不!你已經給我最好的!」
「我是一個階下囚,根本是不可能有甚麼東西留下來... ...反而為你留下一個惡夢。下一次還是... ...」
「正!」
他因為我這一聲輕叫而呆住。
我望著他。一直以來,我知道阿正為了我被人強姦的事而自責——他認為只要他被處決,就可以抵銷這一個罪疚。
但是,他沒有想到他這樣做也會為關心他的人留下一個無法填補的空虛。
「既然你知道那個惡夢是甚麼,你就應該明白你在我的人生之中佔一個如何的位置!」
阿正面露驚訝之色——他明白我的意思。
「我更會自責... ...」
「我不是這一個意思... ...」
見我急於辯白的樣子,阿正溫文地抿嘴而笑。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我知道我這輩子不可能得到自由... ...即使我真是可以活下來,我仍是被關在監獄中,怎麼樣與你繼續下去?」
「阿正,你的心腸太好了!」
「吓?」
見到他那副「丈二金剛」的樣子,我感到十分滑稽。
「你休想再耍流氓嘴臉!」我啐道:「你根本不是一個流氓!」
阿正抿抿嘴,搖搖頭,嘆了一口氣。
「上次我不能將你罵走... ...真是失敗!」
「事後,你都是心軟。」
當日他試圖與我中斷關係,令我大為激動而暈倒——當時我不知道自己已有身孕。胤哥負責押送阿正回囚室。從他口中得知,這傻子在囚室裡為我忐忑不安,手腕更因此而被手銬刮傷。
我的手向上移動——由他的胸背到他的頸背,繼而從後溜到他的臉頰。
現在的他將鬍鬚刮得十分乾淨,摸上去沒有刺手的感覺。
「合格嘛?」
「蠻好... ...有鬍子或是沒有鬍子都十分好看。」
在他「脅持」我,在森林之中暫避時間,阿正刻意留鬍子以掩藏自己的臉目,不讓別人容易認出來。後來我們「回到」文明世界,他就扮作啞巴。
「記得我正式第一次聽你拉奏小提琴的事?」
「記得!當時我們因為你被單獨囚禁而押後一個星期 ... ...而我最有印象是你要求不解開手銬... ...」
「我始終是一個囚犯嘛... ...」
「作為局外人的我不會明白。」
「就當我要取信於獄長。」
的確,爸爸當時也覺得阿正在應對方面太死板。
不過,不得不承認阿真是正取得爸爸的信任。他曾經對我說:「如果不是他『脅持』你,我真是一萬個心都放不下。但是,我知道只有他才會這樣做。」
「直到現在,爸爸只說你打傷其他囚犯,卻沒有將細節具體告訴我 ... ...」
「我將幾個差點要雞姦志航的變態犯打傷... ...就是這樣。」
「其實,單獨囚禁是怎麼樣?」
「嗯... ...可以說甚麼都沒有... ...睡在石地板上:夏天蠻好一點,冬天我就不敢想像了。三餐都是一塊麵包和白開水一杯,不可能洗澡... ...」
「那麼... ...」
「如廁的事?」
我點著頭。
「就是在污渠上開一個洞,在那兒解決。」他完全不當一回事,掛上笑容說:「所以在跟你見面之前,我要先去洗澡及換上乾淨的衣服才到來。」
即使沒有人跟我說,我也可以想像監獄生活的艱苦。
這也是我為阿正拉奏小提琴的動機——希望用音樂去安慰他。
可是,到頭來,是他來保護我,安慰我。
「真希望我們有機會一起玩音樂... ...」
「我那是幼稚園級別... ...」
「而我更想為你生孩子... ...」
「甚麼?」
「既然我已經跟你結婚,就沒有不為你生孩子的道理!」
「這個嘛... ...星期一就跟爸爸商量留精子的事!」
「幹甚麼說這個?」
「好歹都要有兩手準備嘛!」
真是一盞「牛皮燈籠」!
「爸爸都拉你去學校當老師,我相信不是沒有理由!」我啐道:「你就安安分分去教學生!」
「遵命!」
「應該會見到小耀和志航?」
「嗯!他們應該在同一級... ...如果在課室中遇到他們,就希望小耀不要製造麻煩。」
「我相信他不會... ...上一次見小耀時,我覺得他成熟了不少... ...」
「矣?那小子還是一個小孩子... ...」
口在諷刺著自己的小弟,其實阿正心知肚明。
「還記得以前小耀常常跟獄警作對,常常被單獨囚禁,令我變相沒有同房。」天正郁動身子:「我真是沒有想到他會脫離游擊隊——他以前常以自己身為『戰俘』為榮... ...」
在誕下嗣揚時,爸爸來醫院探望我時興沖沖地告訴我一件荒唐事:小耀在得悉阿正仍活著之後,就去向爸爸提出由他代替阿正進死牢。未待阿正動手,爸爸就將他丟去單獨囚禁。
而我在出院之後,也語重心長跟他談了好一會。之後小耀再沒有任何出格的行為。
「難得小耀和志航在這兒有你這一個大哥哥。」我有感而發:「有時候,有些地方看似是不幸的地方,卻因為不同原因而改變意義。」
「我相信我現在已經被人取笑了。」
「誰要取笑我的大英雄?」
「英雄?梟雄才對嘛?監獄無英雄。」
真虧他可以說出這話來!
這時,我打了一個大呵欠。
「希望你以後不要因為我而做惡夢... ...即使我不在,也不要... ...」
「你已經為我跨過一個惡夢... ...可是我最大的惡夢是失去你... ...」
我的眼瞼再不撐起來。
「好好睡吧... ...」
聽到阿正這句溫柔說話時候,我感到他輕輕地將我更加拉進他的懷中。
「晚安!」倚在他的擁抱中,嗅著他的體味,我半睡半醒地回道。
翌晨醒來,第一種嗅到的氣味是早餐的氣味。
「倩雲,醒來沒有?去梳洗之後就有早餐吃。」
「哦。」
梳洗過後,三人份早餐已經放在飯桌上。
「爸爸還未到?」
「還未!」
我心裡咕嚕著,在想著爸爸該將嗣揚抱過來。剛好有人敲門。
甫打開門,見到的是抱著兒子,穿著便服的胤哥站在門口。
「嫂子早安!」
「早安!爸爸呢?」
「我不知道。雖然他口就說一會兒跟我來,不過都是著我帶嗣揚前來。」他吃吃笑著:「我看昨天他睡得不好... ...」
之後,胤哥小心翼翼將嗣揚遞給我。
「咦!胤哥早安!」天正拿著牛奶出來:「給你煮早餐!」
「矣... ...」
「我看你今日不是當值,過來坐下吧!」
「也好!」胤哥坐下來:「難得可以嘗到你親自下廚!」
天正又回去廚房,打算去多煮一分早餐... ...
「天正!你也坐下來吧!我相信咱們吃完之後,獄長都未到來。」
「啊?」
「我去到的時候,獄長還未完全醒來 ... ...昨晚他為了安頓嗣揚差不多一整晚沒好好的睡。」
聽到胤哥這一句說話,我和阿正不約而同噗通一笑。
「哈哈哈哈!早想跟他說別逞強!」阿正開懷地大笑。
接著,他望上上方一個角落——是一個黑色圓型的半球狀的閉路電視。
「沒想到這兒有這東西... ...」
「我相信上週末他因為看到嗣揚半夜哭起來,要我起床安頓他... ...」
「是不是在你們... ...」
我跟阿正面面相覷,然後阿正跟胤哥點點頭。
胤哥張開口,食指在空中亂舞了好一會;他才用力吸一口氣,大聲回道:「啊!明白!」
阿正悠然地拿起牛奶來喝。
「做父母就不會怕那些麻煩... ...我覺得上一次只是不熟悉周遭環境才驚醒過來... ...」
「不過,這鏡頭只是擺一擺而已... ...」
「甚麼?」
「至少我們死刑號的小隊不會看到... ...」
「唉!我這一個外父真可愛!」阿正搖搖頭笑著:「我還是跟他說讓嗣揚留在這兒... ...反正他是想我們好好建立關係才讓我這一個根本沒有資格使用這套房的死囚在這兒跟太太和兒子度週末!」
「我明白的。」胤哥和議點:「不如咱們猜猜獄長何時到來!」
「你真是無聊!」阿正啐道:「吃你的早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