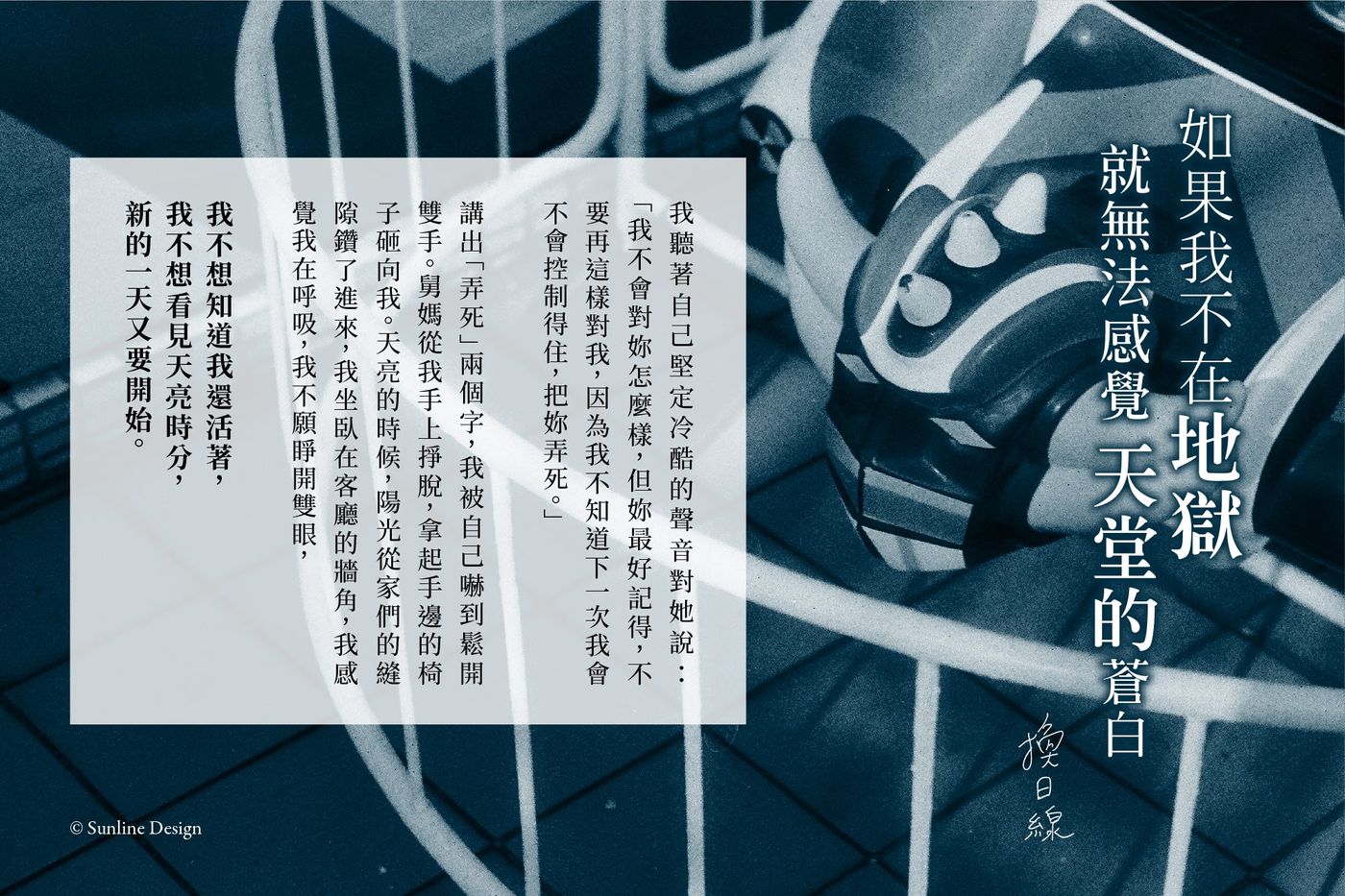我在十四歲那年分化成O,那時父親和母親都感到相當訝異,畢竟身為A的父親和身為B的母親結合,會生出O的機率是非常小的,而且煉獄家從未有分化成O的先例。當我得知自己是O時,我十分的傷心…原以為自己只要勤加練習劍術,有一天就能夠幫上兄長的忙,現在看來根本是不可能了。可是兄長依然安慰我說:
"我只要每次回家的時候,看到千壽郎笑著對我說「歡迎回來」、吃著千壽郎準備的美味的飯菜,身上的疲憊就會煙消雲散,所以不管千壽郎是什麼樣的身份都能夠幫上兄長的忙的! "
聽完兄長這麼說,我也漸漸接受自己是O的身份。
那一天,我和父親、母親匆忙地來到蝴蝶屋,兄長在任務中受了重傷,雖然搶救回來了但仍處於昏迷狀態,兄長的床邊還坐著一名與我年紀相仿的少年,他說他是灶門炭治郎是一同參與任務的隊員,兄長曾與我提到過他的事。在兄長昏迷的這段日子裡他也總是來幫我一起照顧兄長,於是我們便熟絡了起來。他的妹妹彌豆子在晚上時也會出來找我,她似乎很喜歡摸我的頭,大概是想起自己的家人了吧…父親和母親注意到我與炭治郎的互動便時常問我對炭治郎的看法,但我每次都是呼弄過去,我知道父親母親怎麼想,可是我的心裡面早就住了一個人,那人便是兄長…這份情感我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但我知道我必須將它埋藏在心裡的最深處。
很快的,兄長就從昏迷中甦醒過來,他依然很有精神,似乎感覺不到身上的疼痛。這些日子,我和兄長總是在家中和蝴蝶屋往返,兄長很努力地在做復健,想盡快恢復狀態繼續工作,我們偶爾也會遇到灶門兄妹,他們依舊喜歡摸摸我的頭,不過在離開後,兄長跟我說,看著我們如此親密,他的心裡有點不是滋味,對此我倒是忍不住笑了起來,就這樣持續了幾天,兄長已經全然康復,他很快又踏上了旅程。
幾天后,我依舊待在家打掃,突然我的視線開始模糊,體內的溫度不斷上身,我努力的想移動身體去拿抑止劑,但下一秒我就整個癱軟在客廳,我開始感到害怕,父親和母親也因為出遠門的關係都不在家,兄長也是…
"兄長…"
我不停啜泣,不停喊著兄長。
"千壽郎!"
兄長?是兄長的聲音!太好了…
在一片模糊中,我感覺到兄長將我抱到房間,不停地翻找抑止劑,後來他又靠近我喊了我一聲,但我已然失去意識了,後來怎麼樣我也都不記得了,只聞到甜甜的蕃薯味。
再次醒來已經是隔天早晨了,我的衣衫凌亂,身體也佈滿了曖昧的痕跡,我又伸手去摸自己的脖子,已經被標記了…我頓時感到手足無措,指尖感到冰涼,難道自己與兄長…
"千壽郎!你好一點了嗎?"
兄長拉開房門,手上端著一鍋稀飯走了進來。
"兄長…我、我們…"
兄長知道我要問什麼,他也毫無顧忌的告訴我昨天的事。原來在他要給我餵藥時,我在毫無意識的情況下直接抱住了他,不斷地哭泣不斷地訴說我這些年來隱藏在最深處的感情,而兄長對我也是如此。
"實在難以想像兄長與我有著相同的親感…"
"千壽郎願意讓我知道真是太好了!兄長我會對你負責的!"
兄長親吻了我的手背,惹得我臉紅。
"可是父親母親那邊…"
"我會去說服的!不管他們會給我什麼樣的懲罰!"
當父親和母親知曉我與兄長的事情后,眼神裡無一不是憤怒跟擔憂,但母親很快就接受了這件事,她知道不管如何拒絕,兄長都會一直堅持下去,母親一接受,父親自然也不好再說什麼,只丟下一句你們想好就好。
但因為很快就要迎來最後戰役,所以我與兄長的婚事也尚未定下來,但兄長卻在臨走前向我求了婚,我想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幕,他在月光之下單膝跪地,拿出一枚金黃色的戒指套在我的手指上,並且說著許許多多的承諾。
戰爭結束後幾天,煉獄家舉行著婚禮,所有鬼殺隊的親朋好友紛紛前來祝賀,那是個特別的日子,是屬於煉獄杏壽郎和煉獄千壽郎獨特的婚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