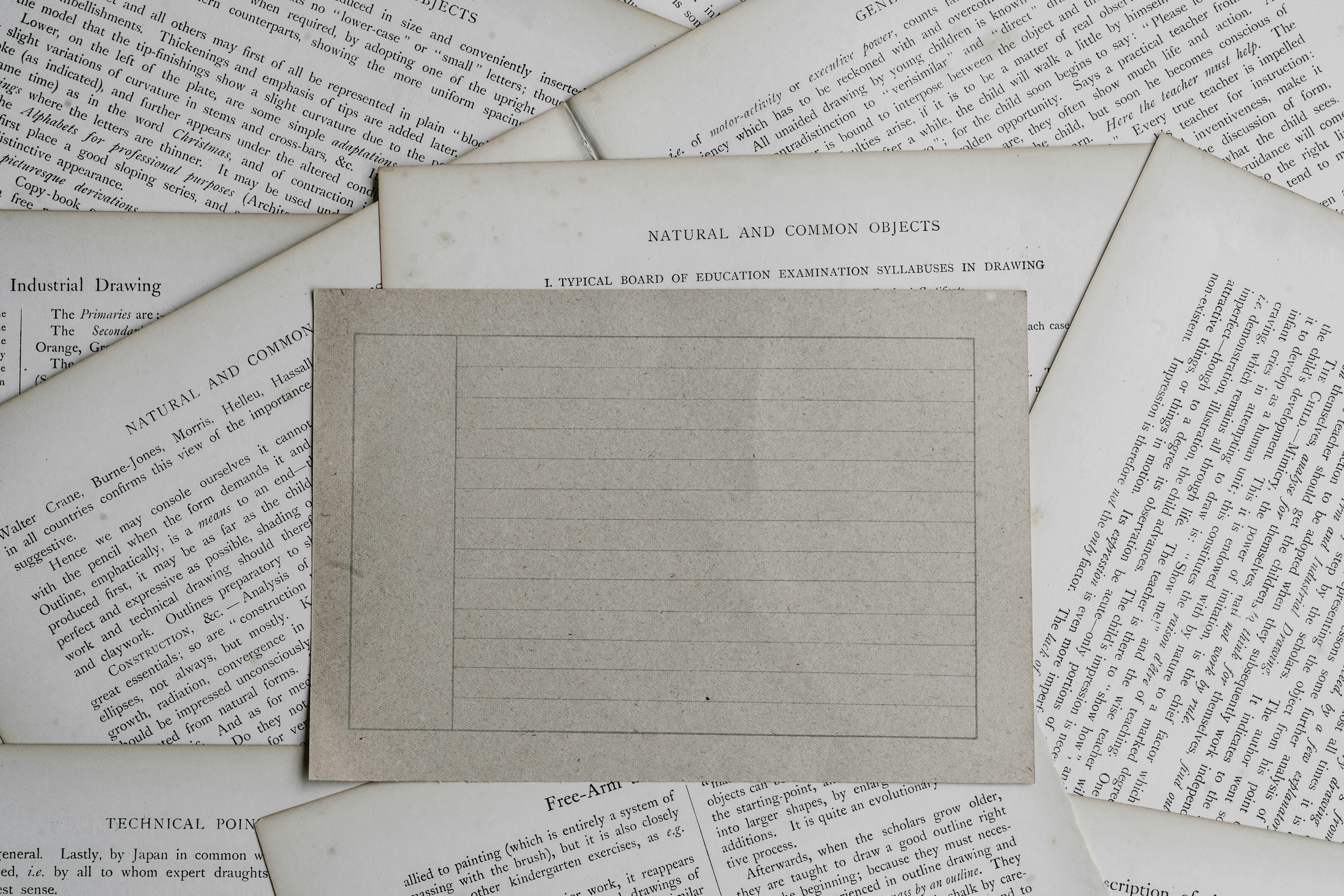我,阮靜雪,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普通人,過著三點一線的平凡生活,沒有可憐的身世,就很普通。
「啊啊啊!憑什麼這樣又可以把我頭爆了。」
「妳可能頭太大了。」我朋友小韓笑笑的說。
「大頭大頭下雨不愁,人家有散,爆我大頭。」
朋友的笑聲從我的左右耳輪流傳來。
「笑什麼,我很有天賦欸。李白是我師父欸。」
「笑死。」這是所有人對這句話的評價。
這是我每天的日程,算是一個比我的數學課還頻繁的課程。
困在遊戲的世界,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所以才會有許多穿越進去遊戲世界,然後過得如世界末日的那種生活,來告訴你說其實遊戲世界沒有那麼幸福,但有多少人信服,為什麼大家覺得不好的事情,卻有另外一些"大家"覺得沒有這些事情活不下去?
但我剛好是那個"大家"的一分子,所以這件事情是我活下去的其中一個動力。
但是孤單的遊戲,並不能稱為遊戲,頂多算個獨角戲,所以朋友也算是遊戲中重要的一環。
說起我的朋友,其實都是一群奇葩的人,或許是有相同的病情才常駐在某間診室,又或者是就像鎂遇到空氣一樣,一碰就燒起白色的火光。
我跟他們相處一直是這樣,直到我的發條轉到生鏽為止。
那是一個普通的晚上,幾人分的遊戲,幾人分的安靜,大家都隔著薄薄的電腦螢幕,玩起了科技冷漠,在深夜的寂靜裡。
「我跟你們說喔,我今天錯過了公車呢!那台公車就跟我相隔對望,而我看著它通過那個剛從綠轉紅的燈,我跟在它的屁股後面,那是一個超絕望的距離欸。」
「哈哈哈,笑死。」這是他們的回答。
「聽說礦泉水上印的日期不是水過期的日期,而是瓶子欸。」
「真的喔,好酷喔。」這也是他們的回答。
「聽說...」
「笑死。」
「聽說...」
「是喔!」
我好像回到國小時期,那個用"聽說..."照樣造句的年代,他們像是活在螢幕裡,一問一答的Ai工具,但沒有不鏽鋼的意志,生鏽的鐵發條也無法順利的運轉。
玩"遊戲",重要的固然是"遊戲",所以將每日不管苦水或是甘水傾洩而出後,也只能剩下遊戲中的反覆內容。其實遊戲只是我課後的社交手段,希望在課後發生的"這些",能夠成為早上課上的"那些","希望自己成為一個別人眼中有趣的人"。
遊戲對我的重要性,幾乎是我的氧氣一樣,缺了它就會感到窒息,遊戲是我暫時離開這嘈雜世界的花園,那個進入異世界的感覺,是多少人如此渴望的一件事,更深入了解那些存在那個世界的角色,與他認識、與他相處、與他共情,我好像第一次那麼去了解一個人,所以我成癮了,去了解了更多人。
他們說這樣是逃避世界,應該多多看看現實,但其實他們也看起來不喜歡現實,只是礙於榜樣,或者不想讓自己沉淪在他們不認可的世界,但可能他們就像魚一樣,知道最後不回水裡一定無法呼吸,所以不能一直活在繁華的都市,或者是幽靜的田野小村。
"他們長大了!"
而我,卻困在從前,其實我也想過這樣不行,但太美好了,所以沉溺。
說起"遊戲朋友相處",其實對我來講太過於矛盾了,當自己不在承擔"有趣的人"時,會有一瞬間的疲累,不想說話,不想社交,開始實施科技的冷漠,"累"是那時候的代名詞,是遊戲不好玩嗎?我會問自己,但不是...遊戲好玩,但就像發條生鏽了一般,一瞬間暫停...
「靜雪,你覺得呢?」
「挺好。」
然後頭像旁邊就恢復了麥克風加上一條小斜線,然後...阮靜雪就徹底從他們的世界裡消失了,他們一定覺得阮靜雪是一個很討厭的人,但聽我解釋..."我累了",並不是打遊戲的累,而是我的嘴巴被某個壞壞的名為"小雞蛋"的怪獸縫起來了,他是專門將可能會亂講話的人,用他精湛的否認(縫紉)技巧給瘋子起來的怪獸呢!
「你不有趣!」
「你還是不講話好!」
「吵死了!」
這是小雞蛋的叫聲。而我也有一套驅逐他的辦法,就是等待,等到送走遊戲中的最後一個陪自己朋友後,他就會消失了,也就送走這個壞壞的小怪獸了。
而在獨自一個人的時候,第二隻怪獸也登場了,他叫做"大鉸鍊",他是必定出現的每日boss,難度我給到20顆星,是很難對付的怪獸之一,他會複盤人一整天的行為舉止,然後進行糾錯與批判,舉例來講:
今天阮靜雪本來用"照樣造句"來得到許多笑聲,但最後卻停止說話,導致他人有可能誤會阮靜雪任何情緒或者行為,可能使之怪物"大鉸鍊"去尋找他人進行攻擊,或者導致以後減少"遊戲朋友"關係,以上判處阮靜雪"有罪"。
"大鉸鍊"也會提供多種解決方法,例如:
解決方法一,停止遊戲時間,直到"遊戲朋友"主動去找你,如"遊戲朋友"放棄你,那就停止遊戲時間。
解決方法二,在社交媒體留下令人好奇的貼文,等待"遊戲朋友"回覆或表示後,回歸正常遊戲時間模式。
解決方法三,隔天主動尋找"遊戲朋友",開啟遊戲時間,回歸正常遊戲時間模式。
解決方法四,放棄"遊戲朋友"。
而要趕走令自己又想起白天四選一地獄的"大鉸鍊",唯一的解決方法是,閉上眼睛,等他自行離開。
進入夢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