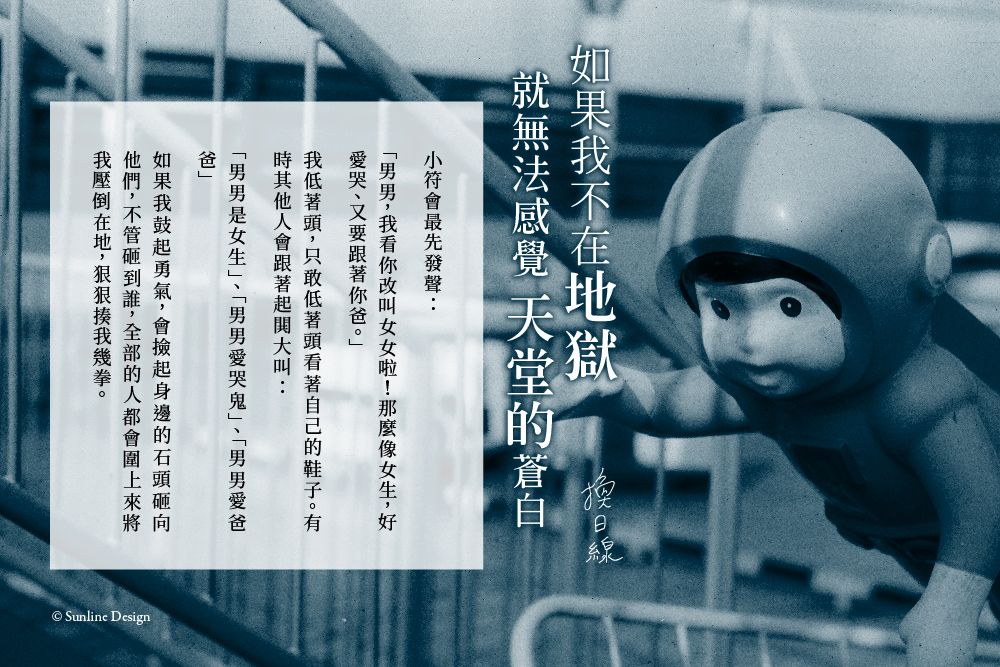三
我和阿生爸爸在客廳裡呆了足足有十分鐘,大部分時間我們都默默無語,而且,一直也沒再有阿生家的親人或什麼朋友到來。還是在最開始,阿生爸爸簡單和我說了幾句,告訴我他們是在要叫阿生吃午飯時發現他沒了的。“他就躺在地上,一動不動……他媽拚命叫他,可他……後來120來了又走了……怎麼會這樣……他就要參加高考了呀……”他斷斷續續地說著,聲音嘶啞。我只好不住安慰他。但到最後,我們都不說話了。
殯儀館的車終於來了。工作人員全副武裝,連連打探死因,直到確認死者並無任何發熱咳嗽腹瀉等症狀且被基本確診為過勞死才似乎鬆了口氣。接著他們開始和我們簡單地探討了流程,用備好的衣服給阿生穿戴,又把他裝入紙棺,這才準備抬走。
在這整個過程中,阿生媽媽始終沒有出現,和她的姐妹留在另一間臥房。而我幾乎成了他們一家的全權代表,負責與殯儀館工作人員交涉,只在有重大事項需要決定時才把詢問的目光投向阿生爸爸,在他費力地思索並微微點頭或搖頭之後才根據揣測的他的意見接受或者重新商討。
但是在紙棺將要被抬出屋子時,阿生媽媽忽然又從她的臥房裡衝了出來。“阿生沒死!我的寶貝兒子沒死!把他留下!誰也不能把他帶走!他……他還要參加高考呢!”她叫著,撲在紙棺上,用力拉斷了綢帶,幾乎掀起了棺蓋。我們三個人又是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把她給拉開,最後還是阿生爸爸把她像嬰兒一樣抱在懷裡送回了臥房。
殯儀館的工作人員退到一旁,全程沒有參與,也沒人勸慰。直到阿生爸爸反鎖了臥房門重新走出來,一位工作人員才公事公辦地說:“紙棺的綢帶斷了要再去拿來,這筆費用也要加進所有費用裡面去的,你們家屬沒有意見吧?”
沒有人說話。我朝那位工作人員點了點頭,他快步下樓去又拿了兩條綢帶來重新把紙棺綁好,然後幾個人才抬起紙棺下了樓。
我和阿生爸爸跟著下樓走出單元門,殯葬車就停在門外面。幾個年紀頗長、戴著口罩的男女剛剛大約在車頭的位置,這時退散到四下里去了。車子後面掀起式的車門被打開,工作人員抬了紙棺上去。我呆立在一旁,聽到不遠處的人們低聲議論著:
“真不是那個病……看,家屬都沒被帶走,也沒怎麼防護。”
“說是個男孩,才十八,今年高考,唉……”
“慘啦慘啦,這爹媽怎麼受得了?”
“就是,白白供養了十八年啊!嘖嘖,這些年上學得多少錢?”
“不會是自殺吧?前兩天看新聞就有個高考生自殺的……”
話語聲不斷,聲音也漸大。我因為久已練得耳音聰明才能從最開始就聽得到,阿生爸爸開始時卻是似乎完全沒留意。他彎了身子,探頭向前,似乎要鑽進殯葬車去陪伴兒子。一位工作人員半側了身攔在他身前。而剛才那人剛才的那句話聲音更大了些,其中“自殺”二字尤其鮮明。阿生爸爸猛地轉頭怒目四顧,像是要找出那胡說八道的人來。
退散開的人安靜下來,都若無其事地轉過頭去,但還有意無意瞥向這邊。我並沒有去看那些人,而是依然盯著已經被放入殯葬車的紙棺,心潮起伏。
猛然間,眾人頭頂上傳來一聲淒厲的大叫:“阿生!寶貝!我來陪你啦!”
我大吃一驚,抬頭看去,見阿生媽媽從窗口探出了大半個身子,似乎立刻就要跳下來。“嫂子不要!”我開口大叫。“映雪!你……你不能這樣啊!”阿生爸爸也吼了出來。但是他後面的話卻哽住了,只在喉頭滾動,我在他身邊才勉強分辨得出。
“有人要跳樓啦!”
“不好啦,又要出人命!”
人群轟動起來,四下都是嗡嗡聲,似乎人數瞬間多了幾倍,但我無暇去看。
這時阿生媽媽已經爬上窗口,忽然後面一個人把她抱住,向裡拖拽。她卻抓住窗口不肯鬆手。兩個人拉扯掙扎著,阿生媽媽不住口地大叫。阿生爸爸搓著手,啞了嗓子叫不出聲,只是瞪圓了眼睛向上看。我思量著要不要跑回樓上幫忙,但是想起我們出來時已經關了門,我上去也無法進屋,只好幹著急。
終於,後面阿生媽媽的姐妹占了上風,拉脫了阿生媽媽的手,把她拽下了窗檯。我不禁鬆了口氣,先看阿生爸爸——他的目光還盯著窗口,像是怕阿生媽媽再撲出來。我又轉著頭四下看——不少人正舉著手機對著阿生家窗口的方向拍攝,口中還叨唸著什麼。但人太多,我聽不清他們具體說了什麼。不過我並不理會,反正猜也猜得出。
這時一位殯儀館工作人員走過來問現在能走了嗎,又問誰跟著去辦理火化相關的手續。阿生爸爸看向我。我知道這件事他非去不可,但又擔心妻子在家出了意外。於是我告訴他說我可以留下幫忙照顧並且加意防範,一定不讓我嫂子出事。他這才點頭,留下家裡的鑰匙,跟著上了殯葬車。車子緩緩開動,朝小區大門駛去。我也轉回頭走向單元門。
“媽媽,媽媽你別擔心,我一定參加高考,一定考上大學讓你滿意!”
就在我走進單元門的那一瞬間,我忽然彷彿聽到身後有一個聲音在說話,那聲音像極了阿生。我急忙轉頭,身後什麼都沒有。不遠處,人們正意興闌珊地散開……
四
在這後來幾天發生的事情,我想沒有必要詳述了。我幫助料理了阿生的喪事,他的遺體被火化,骨灰盒暫時存放在家裡。然後,我也回歸自己的生活,重新開始工作了。我的幫忙令阿生爸爸媽媽非常感激,他們不住多謝我。但我想那也沒什麼,人之常情而已。
我叫阿生媽媽嫂子,當然是因為阿生爸爸算是我一個哥哥,只是血緣關係較遠,平時倒來往不多。而阿生能成為我的學生,是因為他小學時他爸爸媽媽想讓他超前學英語,恰巧我那時還在一家培訓機構講課,教的正是小孩子的英語。於是這兩位哥哥嫂子找到我,於是我也盡心盡力教阿生,於是我們才有那段時間較為親近的來往。
那時候我每週要給阿生上兩到三次課。阿生很勤奮,不必我像教別的小孩子一樣又費心又費力還未必有明顯的成效,所以我很喜歡阿生也教得很愉快。上課的費用阿生爸爸媽媽是絲毫不虧欠我的,他們還不時請我吃飯送我東西,讓我很汗顏,更加賣力。但是後來我不再教書,阿生也漸漸長大升學要學更艱深的功課了,我們的交往才稀疏了。不過我們還有一些來往,我也時常關注阿生的學業,這才跟他們一家保持了聯繫,也能瞭解阿生的一些情況。
但是這時候,在料理了阿生的後事之後,我沒再和阿生爸爸媽媽聯繫。這一方面是因為我比較忙,一方面也是因為我覺得他們需要安靜,慢慢學會接受現實,而這個階段似乎不該去打擾他們。
日子一天天過去,緊張的狀態有所緩和,封閉也漸漸解除,生活又彷彿恢復到了以往的樣子。然而我卻還是老樣子,基本都宅在家裡,似乎一切變來變去的變化都跟我不大相干。要不是有人忽然找我,我幾乎要“不知有漢,何論魏晉”了。
找我的人是一位老友。他的孩子也是今年高考,考場就在我家附近不遠。他拜託我高考最後一天結束的時候到考場外去找他,和他一起接孩子,然後去吃飯喝酒慶祝。卻不開情面只好答應,但隨即想起阿生——若他還活著,馬上也要高考了呀。他一定會考出個好成績,考上個好大學。唉,可惜!可悲!可嘆!
高考的最後一天到了。我不喜歡那樣的場面,但還是硬著頭皮去了考場外,而且提前了一點時間——這也是我的習慣,向來提前,從不遲到。
考場外,是一派熱鬧又安靜的景象——空地搭著無數帳篷,道路兩旁停滿車輛,到處是人頭攢動,但沒有人高聲叫嚷,有的,不過是竊竊私語、禮貌的寒暄和熱切但壓低了聲音的討論。畢竟嘛,考試還沒結束。
我找到了老友。他夫妻倆都在,汗流浹背但興奮異常,和我說著孩子前兩天考試的情況以及他們的預估,看來他們信心十足而且有點功德圓滿的感覺。我隨口應付,不得不替他們高興卻又有點言不由衷,儘力挨著時間。
散場時間終於到了,有孩子漸漸從考場中走出來,接著是大批的人潮洶湧地奔流而出。場外的人群也蜂擁向前擠向人潮,人人都伸長了脖子向人潮中看,尋找著自己的孩子。我被裹在人群中跟在老友夫婦身後,心中暗暗叫苦,但也不得不忍耐,企盼著老友的孩子馬上就出現,大家好調頭逃命,於是也不禁向迎面而來的人潮中瞥過去。
這一瞥之下我竟然看到了一個人,禁不住當即驚呼出來——“阿生!”但我立刻醒悟,我看到的那個人絶不會是阿生,阿生根本不可能出現在這裡。
然而,那人在我脫口叫出“阿生”之際馬上轉頭向我這邊看過來,臉上露出驚慌疑惑的表情。當他和我的目光相對,他似乎吃了一驚,又急忙轉過頭,匆匆地向另一個方向走去。
就在那一瞬間,我確信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阿生的臉。那就是阿生!臉色一樣的蒼白,但露出馴順然而堅定的表情,彷彿隨時待命準備去完成一切父母、老師交給他的使命。
我呆在那裡,無法挪動腳步。“那不可能!那不可能!我一定看花了眼!”我告訴自己。同時雖然我非常想追上去看個清楚,卻又根本無力行動。在那短短的時間裡,我周圍的一切都彷彿不存在了,只剩下我在虛空中,感到困惑和迷茫。
後來老友夫妻帶了孩子找到我,把我喚醒。我們去了一家酒店喝酒,席間我講起這件事以及阿生的死,老友夫妻都說我一定是看錯了。我沒有辯解,只是腦海中不斷閃過那張真真切切的阿生的臉。再後來,我就喝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