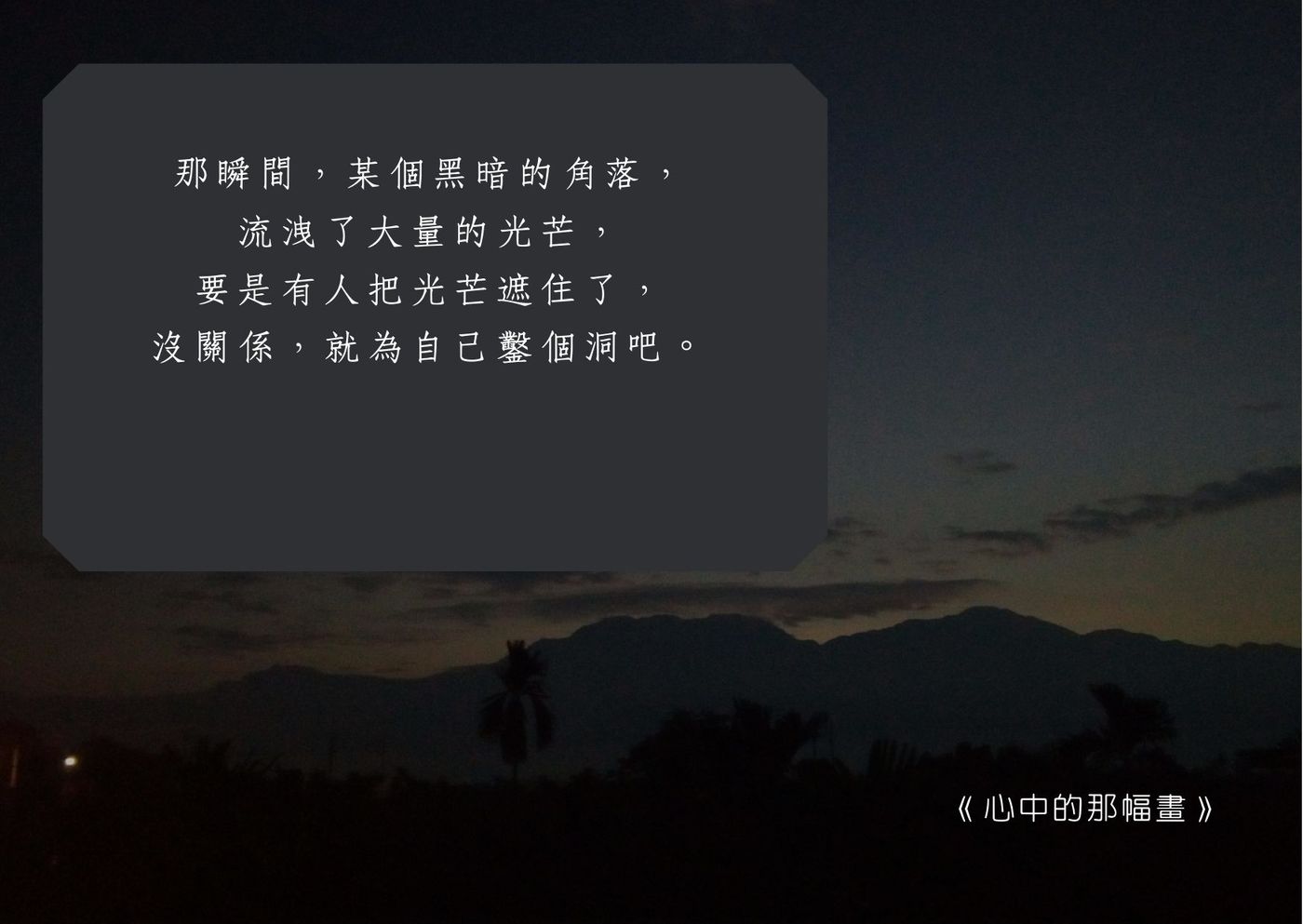某位哲學家曾說過,如果你在兩個選擇之間天人交戰的時候,那就兩個都不要選。
左邊的走廊,明亮的燈光照在米白色的拋光石英磚,太過於正常的景象反而在這詭異的一天顯得不正常。
而右邊的走道… 說是走道倒也太牽強,右邊的走道僅是一根巨大的樹幹,樹幹底下則是深不見底的一片漆黑。
阿尼靜靜地站著,不知為何,阿尼心裡很清楚這兩條道路將會把他帶到哪去。就這樣靜靜地站著,各種訊息像流水滲透進泥土般,像細絲般的拼圖在腦海裡編織著。
有的時候,人真的知道未來的道路是什麼樣子的…
右邊的詭異獨木橋,看似危機四伏,但只要一走過橋就是剛進入病院時的大廳;有著老舊的櫃檯,腐朽但卻敞開著的病院大門。只要踏出去,今天這詭異的經歷就可以結束。
左邊的明亮迴廊,只要一走到盡頭,就會開始變化成前所未見的生物。牆壁上光滑的白漆會掉落,露出裡面的腐爛血肉,明亮的日光燈會碎裂,變成屍沫從頭頂上撒下。然後{裹滿屍布僅露出一張嘴的怪物}會把自己撕裂吞嚥。
Leap of faith,
類似偏執的信念,比較常在宗教裡的狂信徒身上見到。執著地去相信看不見、無法被證實的東西。
阿尼雖然不能理解為什麼自己能夠預知兩條道路的結果,但是他不知為何,能夠堅信自己腦袋裡面的畫面。
在這個地方,只要相信,它就是真的。
阿尼這輩子從來沒有這麼猶豫過… 自己也搞不清楚為什麼會在這麼簡單的問題上掙扎著。
事物的本質跟表面上的差距,總是巨大到讓人驚嘆。
想要選擇正確的道路這件事,原本就是無意義的奢望。
活生生被撕裂成碎肉塊似乎是無法想像的痛苦,但是要這樣就回去原本的生活更是不可原諒的罪惡。
屈服在恐懼之下,逃回名為{正常}的堡壘;這是一種虐殺,對自己精神上的虐殺。
「我會一輩子都厭惡自己的…」
阿尼從獨木橋邊轉身,堅決地往後走去。
經過小庭院的時候,阿尼拿起牆角不知何時出現的鋼椅,猛力往沒有門的玻璃落地窗狠狠砸下。
破碎的玻璃碎片彈起來劃破了阿尼的手背,可以感覺到鮮血正隨著手臂的劇烈甩動而濺灑著。像發洩般,阿尼毫不在意地繼續砸爛剩下的玻璃落地窗殘骸。
回過神來,阿尼看向自己手背上的傷口,血液像紅色的蜈蚣般往傷口爬回。直到紅色完全在手上消失的時候,傷口彷彿跟{身體}隔離開似地,用肉眼可見的速度癒合著…
阿尼懂了一件事,原來肉體跟傷其實是分開的兩個東西。在正常時空裡,人依賴著肉體而活,但一旦精神與肉體被分離開來,兩者間的關係其實微乎其微,簡直就像是不同時空裡的無關聯東西。
肉體是有限的,而精神卻是無限的;肉體上的傷,都不能被稱之為傷。
此時此刻的這裡,並不是{肉體}能夠插手的場合。
阿尼看著面前的小庭院,閉上了眼睛,試圖與那不知名的{什麼}聯繫。過了許久,稍早能清楚感應到兩條不同方向道路的{什麼},在這小庭院面前,像烈陽下的冰塊般,消失得無影無蹤。
阿尼笑了,發自內心地笑了,彷彿回到嬰兒時期的清爽微笑。
(原來自己還有笑就單純只是因為想笑的時候啊…)
『如果當你在兩個選擇之間天人交戰的時候,那就兩個都不要選。』
某個沙啞的老太婆聲音從腦袋深處響起。
「然後選擇自己完全不知道會發生什麼的道路,對吧?」
阿尼笑著說道,大步往小庭院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