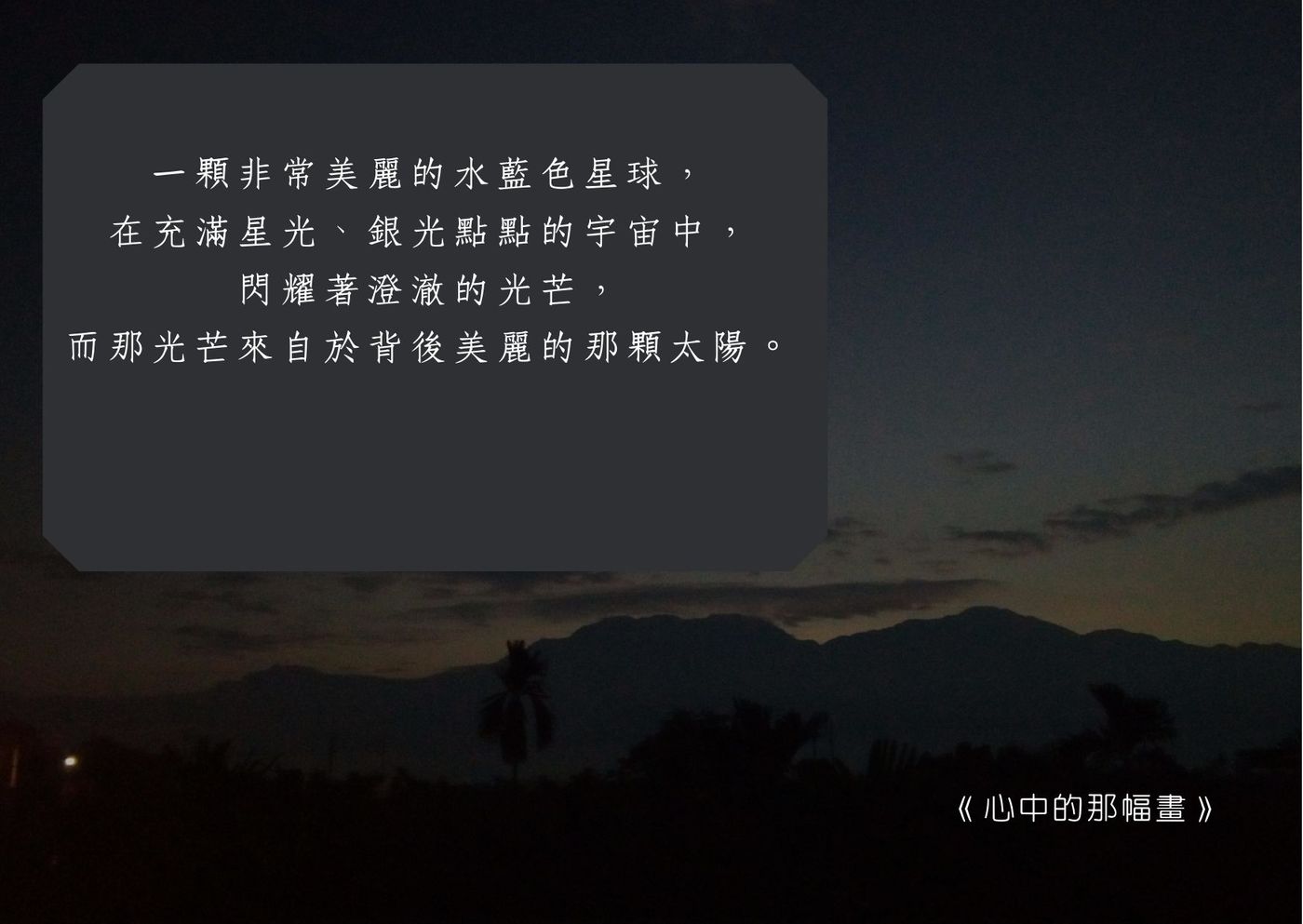飄著小雨的夏日台北,細碎的雨滴在陽光底下輕巧俐落地閃耀,整個畫面像有無數隻銀白小蟲穿梭遊蕩。
熾熱的柏油路上方20公分因為高熱而模糊晃動著,離地20公分的景色好像假的一樣…
阿尼胡思亂想著。
走在台北街頭,隨著小雨慢慢感受氣溫的降低,空氣的濃稠度漸漸變得稀薄。原本每走一步都像要在熱浪中往前推開前進,漸漸可以自在的行動。阿尼抬頭往天上看,直挺挺地站著往天上看了三分十四秒,經過的路人有兩個不自覺地跟著抬頭,阿尼偷偷笑了出來。
阿尼曾經想過一個問題,
千分之一跟千分之百萬,哪個大呢?
就數字來說,當然是同樣大。但是實際上,阿尼認為千分之百萬要大得多了。
這問題其實無關數學,而是關於人性。
一千個人站在一起,一個人抬頭往天上看,剩下的九百九十九人並不會跟著抬頭;
然而百萬個人當中,只要有一千個人抬頭往上看,剩下的九百九十萬九千人勢必跟著抬頭。
人,就是這種容易被愚弄的生物。
剛才那三分十四秒,身邊經過了12個人,有兩個人跟著抬頭了。
「我把千分之一變成六分之一了…」
阿尼覺得這是今天發生第一件值得開心的事。
在馬路前等著紅綠燈的時候,一個看起來七、八歲小女孩,輕輕地拉了阿尼的T-Shirt下擺。
『不…好意思,請問…尼亞病院怎麼走?』
「台北有這家醫院嗎?」阿尼心中如此想著,從嘴裡說出來的卻是:
『過這馬路,往右轉後一直走,第三個紅綠燈後,往左轉再走14分鐘,就在右邊的巷子裡…』
「怎麼回事? 怎麼…?」阿尼感覺炎熱的夏日突然降了幾度。
小女孩溫順地點了點頭,隨即理所當然地牽起阿尼的手,
綠燈亮起,兩人自然地往馬路對面走去。
阿尼順從地讓小女孩繼續牽著自己的手,兩個人沉默地一步一步往這理論上不存在的病院走去。
兩人的背影看起來,雖然像兄妹,卻莫名給人一種已經經歷半個世紀以上的老夫老妻感覺。
沉默了好久,阿尼在一片混亂的思緒中問道,
『我也必須去嗎?』
『嗯,我是來帶你去的喲,我是為了這件事所以我才存在著。』
小女孩帶著笑意回答,眼神一點都不像個六歲的孩子,反而有一種蘊含無限滄桑的豁達。
阿尼正想追問究竟為什麼自己非要被一個莫名其妙的小女孩帶去一間不存在的病院,小女孩在阿尼要開口前的瞬間說道:
『是你叫我來的啊,你呼喊的好大聲呢。好像世界末日前的最後嘶吼一樣,好大聲好大聲地呼喚我呢。』
『嘿,其實你並不是真的想問吧? 你只是覺得應該問一下罷了。』
阿尼沉默不語,靜靜地繼續往前走。
地表20公分的海市蜃樓靜悄悄地緩緩擴大著,從遠處看起來小女孩的下半身已經完全模糊,50公分的海市蜃樓,像漂浮在地面上的清水,有節奏地晃動著。小女孩的手,隨著越來越接近病院,越來越冰冷。那種冰冷與溫度無關,而是另一種更霸道更沒有道理的寒冷。
那是死亡的氣息。
在最後一個轉角,兩人走進巷口的瞬間,空氣突然變的濃稠,就好像在水底下走著,全身上下皮膚都被一層透明的布丁包覆著。
阿尼默默想著,或許所有的嬰兒在羊水裡就是這樣的感覺嗎?
嬰兒在母體中的安全感,是否只要離開那空間就不再有機會感受到了呢?
那麼人的漫長一生中,可以真正感受到完全的安全感,似乎只有那短短的幾個月呢。
空氣中隱約帶著一絲絲血腥味。
阿尼轉頭看看身邊的小女孩,女孩脖子以下已經完全模糊,僅剩那燦爛到刺人的笑顏是如此清晰。
『呵,終於到啦~ 現在只剩下一件事囉~』
小女孩牽著阿尼的手,放到自己的細小的脖子上,笑著說,
『扭斷我的脖子吧,這是最後的程序囉~ 沒有鑰匙你進不去的。』
阿尼正要拒絕的同時,手掌卻不自覺地用起力來,好像身體的細胞叛離自己的意識,被另一股力量掌控著;更糟的是,阿尼心中竟然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要去打從心底相信一件沒道理的事,需要的不是知識或智慧,而是心中那股接近真理的信念。
『我還會再見到妳嗎?』阿尼在扭斷女孩脖子前一秒問道。
脖子不正常地九十度歪向右側的小女孩,彷彿感受不到任何痛苦,笑地越發燦爛了。
『我們一直都在一起,不是嗎?』
咯啦一聲,小女孩軟軟地倒了下來。
阿尼面無表情地往病院走去,病院門口有一塊光滑的面板,阿尼把剛扭斷小女孩的雙手放在面板上。一段段亂碼在面板上閃現跳動後,病院的大門緩緩打開。
阿尼轉頭看小女孩的身軀,女孩像消融在空氣中逐漸淡化。
阿尼走進病院,彷彿回家似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