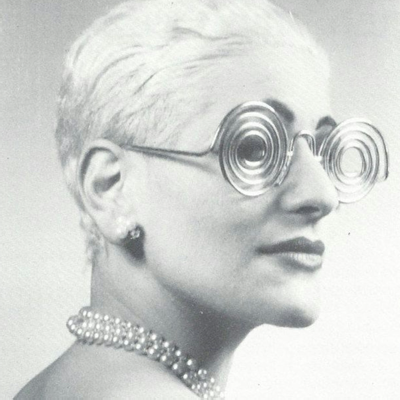我喜歡他展覽及作品的命名。
《難以捉摸的真實》(The Elusive Truth) 是赫斯特於2005年在紐約高古軒畫廊(Gagosian Gallery)辦的個展名。此展涵蓋了32幅「真實」的油畫('Fact' paintings),精確複製從報紙和科普期刊拍下欲作為創作題材的相片。赫斯特說明,此展意在探尋人與意象(imagery)間的關係:「⋯⋯報紙理應訴說真相,而你也確信自己從報上圖片中一覽真實世界,實際上卻不然:它們全是假的。」(“...newspapers are supposed to be about facts and truth, and you believe you get a true view of the world from these images when you don’t: they’re completely fake.”)[1]
作品《生者對死者無動於衷》(The Physical Impossibility of Death in the Mind of Someone Living)是一條浸泡在(分割成三等份的)裝滿稀釋甲醛溶液的玻璃櫃中的虎鯊,之後以另一種方式重置(玻璃櫃改為一體成型),以'The Wrath of Gods, terror is beauty' 命名。
一位名為史蒂芬・朱克(Steven Zucker)的評論家(?,不確定他的身份)說,當他看完標題再看作品中的鯊魚,便因「物理和詩意的矛盾撞擊」(“...and you have this clash between that physical and that poetic.”)對作品留下深刻的印象[2]。
我喜歡「物理和詩意的矛盾撞擊」這個說法。
將感覺轉換/再製成言語時常感到窒礙難行。一直覺得是我書讀不夠。五官受到刺激生成感觸,將之具體化是必要嗎?還是那些思想和情感本身已是具體的存在?
有時候會無法將抽象事物和對應文字相互連結。其中一本我拒絕堅持讀完的書裡寫道:「透過命名將無法理解的事物定位歸檔。」[3] 若將之視為一種可能,人貌似對能以言語表達的事物擁有全然掌控,事實可能反而背道而馳。
Terror is beauty. 恐懼是美。看到這個文字組合,立刻有了疑問:「在什麼樣的恐懼中能看見美?什麼樣的情況下能在恐懼中發現美?」感到恐懼時似乎無暇從中覺察任何美的成分。想了很久,今天終於有點頭緒——當我不得不正面迎擊恐懼,過了那段緩衝期,便會在與恐懼交戰時將自己抽離至恐懼之外——或許那種狀態是美的。
空然。
其實是我對恐懼束手無策。或許那是技術性軟弱,一種逃避的手段。
作品《對逃亡的後天無能》(The Acquired Inability to Escape)
[1] Damien Hirst—Exhibition—The Elusive Truth. damienhirst.com
[2] A beginn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art—Damien Hirst, The Physical Impossibility of Death in the Mind of Someone Living
[3] 出自《物理屬於相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