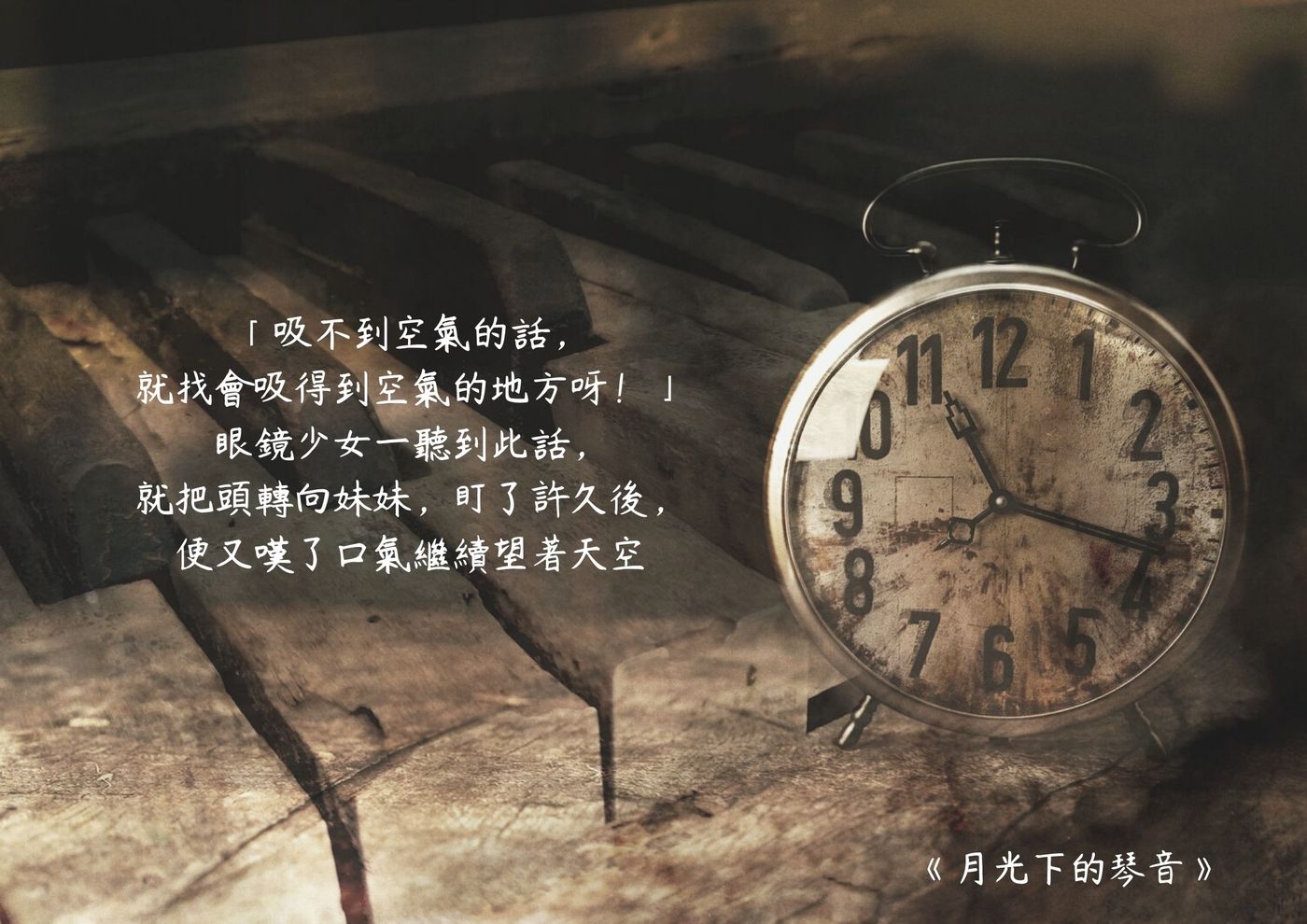前情
這是晏書彤將滿十八歲的那年夏天,余侍而也在裡面。
第一課
平井堅〈大きな古時計〉的歌聲迴盪整個校園,但無論他唱得如何賣力,桌上的同學們仍舊趴睡不醒,每個都像詞裡說的老舊大鐘,帶著神秘的死寂。
平井賭氣似地歌聲嘎然而止。睡意得勝,趕走歌聲後快速蔓延,校園又復沉寂。
細小的呢喃聲由風載著,鑽過窗簾穿進教室裡。
即使沒人回應仍自得其樂,一聲又一聲歡快地持續著。
我輕輕推開落地紗窗,迎向被午後陽光照得形影分明的遠山和田野,沒有一個人、甚至看不到一輛車,全世界都在午休一樣濃濃睡著,只有幾團小黑影,愉快地在靜置了的、陽光遍照的天與地間恣意潛泳。
牠們總是樂得反覆在同個八字裡迴旋,於轉彎處輕快一鳴,順便把高難度的急轉彎就這麼輕輕帶過去。
我總覺得這些技藝高超、動作優雅的燕子個個都是不出世的隱者,躲在這樹比人多的私校,日日對我這樣的小妮子表演特技,以明示自己與嘰喳亂叫的麻雀之不同為謀。我看得入迷,又慶幸天地間此刻只有自己得以觀賞牠們不願向世人展現的秘密。
正欣賞間,後面傳來開落地窗的聲音,侍而走了出來:「矮噁!是小彤彤」
我挑起一邊眉毛不置可否,然後繼續轉身看燕子。她自自然然地靠到我身側。
「好冷喔!」說著冰涼的左手便熟門熟路地鑽進我袖子裡,握著我的手臂取暖。即使午後陽光看似熱烈,初春空氣裡仍隱藏不了處處散發的寒氣,學校位在山中尤其如此,還不到可以脫下薄外套的時節。
我下頷輕壓著她鑽到袖子裡的手說:「台灣的燕子都不用南遷呢!」
「誰知道呢,說不定每個寒假牠們都趁我們不在的時候往南飛,我們回來之前就又北上了。」她隨口接話,順便把我的頭從她手上移開,另一隻手也伸了進來。
「燕子幹嘛每年都南遷呢?為什麼不乾脆在南方定居就好呢?」我再把頭壓回她的兩隻手上。
「說不定是捨不得你呢!你不是牠們的親戚嗎?」嫌暖手不夠,她把頭也靠到我肩窩,舒舒服服地棲在那裏了。
「你又知道他們都姓晏了」被她這樣予取予求的我也不甘示弱,頭遂靠到她頭上去了。
「就算不姓晏,小彤彤躺起來這麼舒服一定捨不得的啦!」一派理所當然的口氣。「所以其實我是一張床?是給燕子躺的?」
「對啊!你不知道嗎?」
「有沒有給魚躺的床呢?」我輕描淡寫地問
「你不知道魚都不睡覺的嗎?」她不輕不重地答
上課鐘聲還是響了,無情驚起多少春夢中人。
第二課
那時已是暮春,大學分發皆已塵埃落定,妳選擇回台南家鄉,終結異地學子生涯,我則到北部求學,從山中浪跡到都市,繼續在外飄盪。大家都為了畢業典禮群情沸騰,沒有人在乎學校還沒著落的指考班心情。教室裡夜夜笙歌,解放從高一鬱結至今的壓力。愛熱鬧的妳當然加入畢典籌備小組,很快就成為核心幹部,超級忙碌。我本是個討厭熱鬧而自甘寂寞的人,以練習書法為由,從集體燃燒著的青春火焰中淡出,在校園的靜僻角落與墨香共處。班級共同話題我沒法加入也沒什麼可惜,我總是樂得用課外讀物築起自己的小天地。
然而只有妳,一開口便停不下來似的,向我單方面聊著在典禮上將執行的偉大計畫:「小彤彤我跟妳說,這次的畢業影片要用我們自己寫的歌欸!詞跟導演都是歐文忠喔,一整個超級催淚的,我覺得所有老師看了一定噴淚到不行。柳詠老師就不用說了,到時候一定哭死。那群數學怪物負責的部份,聽說搞得很......數學。哈哈哈!不知道能有幾個人看懂,到時候台下一定尷尬到死…」
雖然白天因為還是要上課總是見得到面,但用心良苦的老師為使學校不要太像遊樂園,還是安排了大學入學前的先修課程。我被分到理組作實驗,妳則是在文組讀世界文學,見面的時間倒比學測前少了。
一日晚上我如常在小小的書法教室獨自臨摹趙孟頫的般若心經,為他俊秀而雅致的代筆深深著迷,陶醉得如入無人之境,外頭腳步響起:
「嗨!」
我在夢遊般的狀態下被驚醒,筆倒是一下沒撇錯,鎮定自若地問:「怎麼來了?」「來看妳不行嗎?」
我微笑,心裡瞬間綻出向日葵一樣的燦笑「不敢恭迎余小姐大駕。」
我滿意地寫完一張毛邊紙準備換張,妳卻坐到我旁邊,自顧自地哭起來了。
我默默放下筆桿,從口袋拿出衛生紙幫妳擦淚,不會說什麼安慰的話,就默默等妳緩過氣來,由妳來說:
有個姓王的同學總是和妳作對,表面上很配合,實際上都在檯面下挑撥離間。都幾年的同學了,一直以來都好好的,妳不懂到底哪裡得罪她,為什麼要這樣放冷箭。妳哭得梨花帶淚,嘴上卻是咬牙切齒,怎麼說怎麼委屈。我跟著妳罵那個姓王的,罵三句勸一句。到最後妳罵累了,說著不幹了、不幹了,以後跟我一起來寫書法,不要再跟那群死沒良心的畢典幹部混了。說到後來乏了,畢竟為了兩周後的典禮最近幾乎不眠不休的。不知不覺,竟趴在旁邊的字帖堆上睡著了。
我關了盞燈讓妳好睡。月光盈盈穿入窗櫺覆著妳,雪白的臂膀上了層霜。哭紅的眼眶還泛著水氣,長長的睫毛顯得好晶瑩。細細柳眉似蹙非蹙,飄著一縷極為單純的愁思。雙脣因為剛剛的情緒鮮紅了,沒有意識地吻著帖上的字。
我根本無心書寫了,就這樣肆無忌憚、近乎貪婪地望著你。
春雨過後,大地生機盎然,連夜,都這樣美。
第三課
畢業倒數一個月,每日白晝都像冬眠,學生有一搭沒一搭地上著課。終究已是強弩之末,能堅持本分的同學並不多。每日黃昏,地球轉入陰影的那面,世界像穿過了交界線,瞬間甦醒了。排演話劇的、拍攝影片的、練習合唱的、混吃等死的……高三的教室有種鳶飛魚躍的氣象,彷彿本就是為了夜晚而活,畢業生們用流光溢彩點亮濃濃籠罩在黑夜中的校舍。
而我的顏色是什麼呢?
校園很大,縮在書法教室的角落,其他人熱情的青春灼傷不到我,他們無疑都帶著光彩照人的顏色,而我呢?難道是墨黑色的嗎?
我正在寫侍而拜託我的舞台背景,在大大的畫布上書寫李叔同的《送別》,我一邊勾勒筆畫一邊出神地想,身為墨黑色的我到底都怎麼活過來的呢?
我不會打屁聊天,每個輕鬆談天的場合只要我一開口,總是很快被句點。
我不懂如何八卦,影視版上每張面孔、每個名字我沒有一個認識。
我無法了解和我同齡的學生們,每天都在聊的韓劇、日劇、陸劇到底有什麼有趣。
和其他顏色沒辦法交流,一接觸到就會把氣氛染黑,這麼無能的黑色為什麼得以存在到今天呢?何德何能和光與火一同站在舞台上,貢獻一個用濃墨搭建的小小角落呢?
都是因為妳吧 !
從不嫌棄總是接不上話題的我,總是自顧自地講著想講的話。把我那只有黑色跟灰色的世界,點染上一抹一抹斑斕的七彩雲霞。上大學後的世界又是怎麼樣呢?妳要回到台南,像洄游的魚總是要回到出生的水灣。我呢?即將北上,到那個人稱天龍國的地方。那裡的人又是什麼顏色呢?會在意一個總是黑黑灰灰、聽不懂人話的人嗎?
我覺得自己好蒼老,比石頭、比海水都老,人說「留命以待滄桑」,我的人生已經水墨般只有濃黑跟淺灰的區別,還有滄桑的餘地嗎?離開這裡、妳不在我身邊之後,世界終究再也沒有一絲光與火的可能,妳能想像嗎?妳沒想過吧?
最近大家都在交換畢業紀念冊,在每個裝飾精美的頁面上寫下想對這個人說的話,妳當然把本子遞過來了,但我拖了三天遲遲沒下筆,索性先傳給其他人,等全班都寫過後才又回到我手上。
我每次都盯著紙的左下角那兩隻水墨風格的錦鯉,一黑一白,在紙面下多麼自在歡快。妳說這頁是特別為我選的,還要我寫完用書法題句詩。
要怎麼跟妳說,妳才會了解,光在水墨中是多麼重要,比墨暈跟留白都還要重要。多想跟妳說,妳就是水墨中的光,無處不在把整個畫面照亮。要怎麼寫,才能讓妳明白,沒有妳就沒有光、沒有溫度、沒有色彩、沒有世界。
我想寫得很多很多,一張紙根本不夠。
百轉千迴想了很久很久,最後拿起毛筆,我寫:
「鴻雁在雲魚在水,錦繡前途無際」
第四課
倒數一天,全班在做完最後的大掃除後,四散坐落於空曠乾淨的教室各處。老師說好了要給我們看電影,放下投影布幕,同學們拉起窗簾,惡狠狠地杜絕窗外豔陽,鑽入偷取我們最後一點點相處時光。不知道從哪裡生出爆米花、洋芋片、杏仁巧克力脆片,電影還沒開始就到處傳遞著,話夾子跟餅乾包裝都興奮地開啟了。
同班數年寒暑,最後一部一起看的影片,經過極其慎重的挑選,決定看卓別林的《城市之光》。電影從躺在雕像上的卓別林揭開序幕,眾人不時爆笑出聲,一面大笑一面嚼著零嘴。老師坐在貴賓席,桌上有我們進貢的各式點心。和同學一起笑得東倒西歪,威嚴的教師形象早已不復存在。
然而,每個搞笑的場景無一不讓我哽咽,卓別林滑稽的樣子重重掩蓋了悲哀的現實。好笨拙、好天真的愛,一心一意沒有心機。女主角當初看不見,長相連同真相都只存於想像。一事無成的男主角蒙著自己的雙眼跟著活在夢裡面,恣意扮演著愛人的白馬王子,為了圓這個用謊織的夢,他甚至站上擂台與人搏鬥。
我何嘗不是活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夢裡面,是有溫度而不熱、有光彩而不刺人的美夢。
然而我何嘗不知,這一切都是有時限的,驪歌一奏夢就要斷了。
如同他給她一筆錢去國外治眼睛,她重回光明之時,便是他返入黑暗之際,往事如煙如夢般終究雲散。明明愛得那樣真切,而身敗名裂的他還是有沒有一絲後悔。最後刑期結束的他與手術過後的她在街上相認了,沒有夢碎與被欺騙的絕決,女主角反而充滿柔情地笑了。
看到這裏我止不住了,淚水還是滾出我的眼眶。
如果我告訴她心裏真正的想法,她也會這麼充滿柔情地對我笑嗎?
影片結束在這裡,我悄無聲息地用手敷眼睛,不動聲色把眼淚抹去。哪有人看喜劇看到哭的呢?我為自己的荒唐破涕為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