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篇:慈悲的諦聽
這份文件並非一份客觀的分析報告,而是一場虛構的對話集。我們將匯集日本社會各個角落的聲音,共同圍坐在一盞象徵澄澈智慧的琉璃光下,謙卑地探問一個古老而深刻的字:「苦」。這場探問的起點,源於一句蘊含無盡慈悲的箴言——「未經他人苦,莫勸他人善」。
此言並非消極的禁令,而是積極的倫理指引。它呼喚我們從試圖評判與糾正的衝動,轉向一種僅僅是陪伴與理解的深刻臨在。因此,本文的目的並非草率地提出解答或勸誡,而是進行一場深刻的、慈悲的諦聽。我們相信,在真正理解苦難的樣貌之前,任何建言都可能成為另一種形式的暴力。
本次對話將依序展開三個篇章:「勞作者的磨礪」、「社會網絡的枷鎖」與「公僕與傳承者的心聲」。透過這三個層次的諦聽,我們期望能呈現苦難如何在不同的生命脈絡中顯影,又如何被宏大的社會結構所塑造與加深。現在,讓我們靜下心來,首先聽見那些用汗水與生命構築社會根基者的低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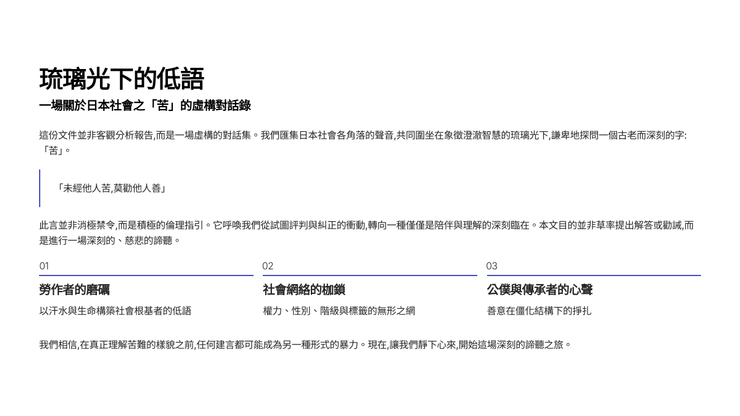
--------------------------------------------------------------------------------
第一部:勞作者的磨礪
在本章節,我們將聚焦於那些以自身勞動支撐社會運轉的人們。他們的「苦」,不僅僅源於個人的辛勞與汗水,更深刻地植根於宏觀的經濟變遷、制度壓力與文化期望之中。正因如此,任何脫離了對此結構性脈絡理解的輕率建議——諸如「再努力一點」、「要提升自己」——在此都顯得尤其蒼白與殘酷。以下是四位勞作者的分享。
--------------------------------------------------------------------------------
運送業者:
「人們說這是『失落的三十年』,對我來說,失落的不只是國家的GDP,而是我這一代人對未來的安全感。我年輕時,『終身雇用』就像空氣和水一樣理所當然,你只要進了一家好公司,忠誠地工作,公司就會照顧你一輩子。但泡沫破了,一切都變了。我們這些開貨車、開計程車的,很多都是『非正規雇用』。合約一年一簽,沒有獎金,福利也差得遠。年輕時還能靠體力硬撐,但現在年紀大了,身體到處是毛病,心裡卻一天比一天慌。我不是沒有努力,我每天握著方向盤超過十個小時,但薪水幾乎沒漲過。當你不知道下個月的合約還在不在,當你連生一場大病的本錢都沒有,那種深刻的不安全感,那種 precarious 的處境,就像沼澤一樣,讓你越掙扎陷得越深。這不是個人努力就能爬出來的坑。」
老農夫:
「我這雙手,跟這片土地打了一輩子交道,但現在,我卻看不到這片土地的未來。你看看周圍,還在田裡忙活的,哪個不是像我這樣頭髮白了、腰也彎了的老頭子?我們這一代,平均年齡快七十歲了。年輕人?他們不願意回來。這裡又辛苦,收入又不穩定,誰願意呢?後繼者不足,這不是一句口號,而是我們每天睜眼就要面對的現實。你看那邊,那片荒掉的田地,在日本全國,像這樣的『廢棄農地』已經有四十萬公頃了。我們自己的『食料自給率』只剩下百分之三十八左右,一個國家,連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飽,這不是很可怕嗎?有時候我看著夕陽下的田埂,心裡想的不是收成,而是等我們這一代人走了,還有誰來守護這片土地?」
護士:
「最近政府推行『働き方改革』,說要縮短我們醫護的工時,聽起來是好事,對吧?但現實是,醫院的人力根本沒有增加。工作量還是一樣多,時間卻被壓縮了。過去還能利用下班後的時間帶帶新人、做點研究,現在連喘口氣的時間都沒有。但身體的疲憊還不是最痛苦的。最深的痛苦,我後來才知道有個詞叫『道德損傷』(moral injury)。當我知道一個病人需要更多時間的陪伴與傾聽,但制度和績效指標卻逼著我必須在幾分鐘內完成所有流程;當我知道某種治療對病人最好,卻因為保險給付的規定而無法提供。那種感覺……就像是靈魂被撕裂一樣。我違背了自己的專業良知,不是因為我冷漠,而是因為系統不允許我慈悲。這種無力感,比任何加班都更讓人耗竭。」
新創企業家:
「大家看到的是我們光鮮亮麗的一面,是『自由』、『夢想』。但他們看不到的是,每一個決策背後的孤獨。公司的幾十個員工,他們的生計都在我肩上,我每天都在巨大的財務風險上走鋼索,但我能跟誰說?我必須是那個最堅定的人。很多像我一樣的自由業者也是如此,我們用『自由』交換來的,是整個社會安全網的缺席——沒有失業保險,健康保險要自己負擔高額費用,更不用提退休金了。這種不穩定,會讓你陷入一種『稀缺心態』(scarcity mindset),你的眼光只能盯著下一張訂單,根本無法做 long-term 的規劃。那種自由,有時候更像是一種漂泊。」
--------------------------------------------------------------------------------
從他們的聲音中,我們聽見,勞動者的苦難並非孤立的個人掙扎,而是與其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經濟的潮汐、制度的經緯緊密相連。更令人警醒的是,這些苦難並非終結於一代人,而是構成了一條相互傳遞的代際因果鏈。泡沫經濟崩潰後「失落的三十年」,不僅定義了上一代勞動者的不穩定生涯,更成為了下一代年輕人所繼承的、階層固化的現實。這些經濟上的困頓與制度上的壓力,如運送業者和護士所言,進而迴盪在整個社會結構之中,形成了我們接下來必須探究的、無形的枷鎖與隔閡。
--------------------------------------------------------------------------------
第二部:社會網絡的枷鎖
在本章節,我們將視角從具體的勞動現場,轉向更廣闊的社會關係網絡。權力、性別、階級與社會標籤,如同一張張無形的網,在無形中製造並固化了某些群體的苦難。這是一種更為隱蔽的、日常化的結構性暴力,它將人們囚禁在特定的角色與命運之中,難以掙脫。
--------------------------------------------------------------------------------
單親母親的獨白:
「日本的『性別差距』(ジェンダーギャップ)對我來說,不是新聞報導上的數字,而是我每一天的生活。我離婚後獨自帶著孩子,每天就像一場戰鬥。早上五點起床做便當,送孩子上學,然後衝去打兩份零工,傍晚接孩子,回家做飯、洗衣、檢查作業……一天結束時,我才發現自己連坐下來好好喘口氣的『時間』都沒有。這種『時間貧困』,是社會看不到的。
他們說,日本有百分之五十點八的單親媽媽都處於貧困狀態。我就是其中之一。因為要照顧孩子,我只能找那些時間彈性但薪水微薄的非正規工作。我拚命工作,卻依然貧困,這就是所謂的『働いても貧困』。最讓我難過的,不是物質的匱乏,而是社會的眼光。當別人勸我『再努力一點,給孩子更好的生活』時,他們不知道,我已經付出了全部。他們沒有看到,是這個社會不成比例地將家務和育兒的無償勞動壓在女性身上,是這個社會對單親家庭的支持如此薄弱。我的苦,不是我一個人的苦,而是這個結構加在無數像我一樣的女人身上的枷鎖。」
更生人的獨白:
「我在監獄裡服了很長的刑,我以為出獄那天就是重生的開始。但我錯了,真正的刑期,是從我走出監獄大門那一刻才開始的。社會在我額頭上烙下了一個看不見的刺青,叫做『刑務所帰り』(剛出獄的人)。這個烙印,讓我寸步難行。我去找工作,一看到我的履歷,對方就找藉口打發我走;我想租個房子,房東一聽說我的過去,立刻就說房子已經租出去了。
我真心想要改過,想要靠自己的雙手好好活下去,但整個社會都在對我關上大門。那種絕望,比在監獄裡還要磨人。更可怕的是那種無處不在的『自己責任論』——人們覺得,你會變成這樣,都是你自己的錯,你活該。這種排斥滲透在整個系統裡,就像那些去申請福利的人會遇到的『水際作戦』(窗口勸退)和『扶養照会』(強制聯絡親屬)一樣,整個社會都在用各種方式告訴你:『你不屬於這裡』。他們用一句輕飄飄的『你要為自己負責』,就撇清了整個社會的責任。這種排斥,比任何有形的牆壁都更令人窒息。」
高階主管的獨白:
「我必須承認,很長一段時間裡,我不理解真正的『苦』是什麼。我的生活,就像被一道『豐裕的帷幕』包裹著,出入有司機,住在安全的社區,孩子上最好的學校。我身邊的人,談論的都是投資、收購和海外度假。基層員工的掙扎、社會底層的絕望,對我來說,更像是報紙上的統計數字,缺乏真實的溫度。
我的成功,讓我不知不覺地相信了一種『公正世界信念』(just-world belief)——我相信這個世界是公平的,只要你足夠努力、足夠聰明,就一定能成功。所以,過去在制定公司政策或參與公共事務討論時,我很容易就把他人的失敗歸因於他們個人努力不夠,或是選擇錯誤。我現在才意識到,那是一種多麼傲慢的認知偏誤。我未曾真正走進過他們的處境,卻輕率地用我的世界觀去評判他們的人生。我那些自以為是的『善意』建議和政策,或許在無形中,加深了他們的痛苦。」
--------------------------------------------------------------------------------
這些獨白揭示了,社會結構的困境不僅體現在邊緣群體的掙扎,也體現在權力者的認知盲點之中。這些深層的結構性問題,最終必然會反映在負責維護社會運轉的公共服務體系之內,考驗著身處其中的公僕們的善意與良知。
--------------------------------------------------------------------------------
第三部:公僕與傳承者的心聲
在本章節,我們將深入那些身處公共服務體系與文化傳承核心的人們,傾聽他們獨特的困境。他們是政策的執行者,是文化的守護者,本應是善意的傳遞者。然而,當系統本身的僵化與文化內在的張力成為阻礙時,他們自身的善意也可能成為痛苦的來源。
--------------------------------------------------------------------------------
基層公務員(訪談片段):
「問:您在第一線工作,覺得執行政策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答:是無力感。巨大的無力感。日本的官僚體系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問題,叫做『縦割り行政』(條塊分割的行政體系)。每一個部門,就像一個個獨立的穀倉(silo),各管各的,資訊不互通,政策不協調。比如,一個貧困家庭來求助,他的問題可能同時涉及厚生勞動省(管福利)、文部科學省(管教育)和國土交通省(管住房)。但在我這裡,我只能處理我這個窗口權責範圍內的事。我看著眼前這個焦急的市民,我知道他的問題是環環相扣的,需要一個整體的解決方案,但我手上的法規和權限卻把我綁得死死的。我只能跟他說:『關於那個問題,請您去另一個部門的窗口問問。』那一刻,我覺得自己不是在幫助他,而是在把他推開。我們身在第一線,最清楚民眾的苦,卻被系統的僵化困住,有心無力。這種挫折感,每天都在消耗我們的熱情。」
中學教師(訪談片段):
「問:關於校園裡的人際關係,您認為日本文化有什麼樣的影響?」
「答:我們的文化非常重視『和』(Wa),也就是和諧。這本身是個很美好的價值,它讓社會有禮而有序。但在某些情境下,它會變成一種巨大的『同調壓力』,尤其是在學校。以校園霸凌(いじめ)為例,學者提出的『四層結構』——加害者、被害者、觀眾、旁觀者——就非常清晰。真正讓霸凌得以持續的,往往不是加害者有多可惡,而是後兩者,也就是『觀眾』和『旁觀者』的沉默。
為什麼他們會沉默?很多時候是為了維護班級那個微妙的『空氣』。為了不破壞表面的和諧,也就是『建前』(Tatemae),大家選擇壓抑自己內心的真實感受,也就是『本音』(Honne)。一旦有人站出來,就會被視為『不識相』的麻煩製造者。所以,大家選擇了沉默。而這種沉默,本身就是一種集體的、無聲的勸誡,它在告訴受害者:『為了大家,你就忍耐一下吧。』在這種情況下,神聖的『和』,就異化成了一種殘酷的壓迫工具。作為老師,這是我最心痛的地方。」
--------------------------------------------------------------------------------
從公僕的無力到師者的心痛,我們聽見了善意在僵化結構與文化壓力下的掙扎。當諦聽了所有這些來自社會不同角落的低語後,我們的心中不應只有沉重,更應有一份清明的覺醒,一份共同的願望。
--------------------------------------------------------------------------------
結論:從「莫勸」到「同願」
在諦聽了勞作者的磨礪、社會網絡的枷鎖、公僕與傳承者的心聲之後,一個核心的洞見,也是一個令人不安的模式清晰地浮現:箴言「未經他人苦,莫勸他人善」在現代制度中,正呈現出一種遞迴性的違背。這意味著,一個在頂層發生的、輕率的「勸善」,會層層傳導,最終迫使身處底層的個人,在違背自身良知的情況下,對他人做出同樣殘酷之事。
當政策制定者在未能體會第一線資源匱乏的痛苦下,便推行以效率為導向的改革,這就是對護士的「勸善」,其結果是護士因「道德損傷」而耗竭,難以再給予病患慈悲的臨在。當僵化的官僚體系要求基層公務員嚴格執行脫離現實的法規時,這就是對公僕的「勸善」,其結果是公僕被迫將求助的民眾推開。系統的無情,最終透過耗竭的個人,傳導至社會中最需要關懷的群體身上,形成了一個層層相扣的苦難循環。
因此,箴言的智慧引導我們完成一次生命中最深刻的轉向。第一步,是「莫勸」的神聖靜默。這不是冷漠或放棄,而是一種在承認自身認知局限、洞悉苦難背後龐大結構之後,所做出的積極的倫理克制,旨在避免因無知而造成二次傷害。
然而,靜默並非終點。它為一次更深刻的昇華鋪平了道路——從「莫勸」,走向「同願」。這意味著,我們應當放下扮演「拯救者」或「規訓者」的自我,謙卑地與受苦者站在同一陣線,不是去指導他們,而是去感受他們,與他們共同朝向一個更美好的願景,發出共同的祈願。
人間淨土的根基,並非建立在一個充滿相互規訓與評判的世界之上。恰恰相反,它必須建立在一個所有成員都願意先放下自己那把名為「善」的尺子,去謙卑地理解,並親身致力於改變那些造成他人苦難的、具體的、鑲嵌在生命脈絡與社會結構中的障礙。這是一個從諦聽開始,經由理解,最終付諸集體慈悲行動的旅程。
萬分感恩,南無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