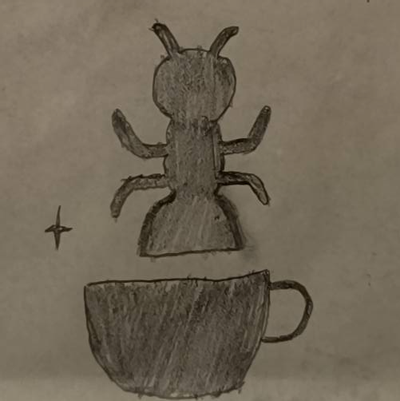夜伏之時,簫笛瑟瑟,靈,淒卑,簫笛迎風離目敘無遠。
---------------------------------------
吹落在海面上,尾端輕輕拂著海面的赤紅絲帶,是那燈籠的綴飾。海面上映著那赤紅的燈籠,風一樣地吹著,而那幾許絲帶,層層疊疊的染紅了深海。
霜雪落了,也成了那絲帶的花,霜霜白雪成了那紅棠,綻開在了長生殿旁的海中。
風之大,大舟也能抵,這是北嶽大帝的風。
塵宵,那約莫十七歲少年外貌的北嶽大帝,蹲低了身,輕輕地拾起了在海中開啟的紅棠花,拾起了那紅棠,放在那海面上,讓它飄浮著。
哭燈已經漸漸地遠去,離開了長生殿的邑門。
塵宵,望著眼前的深海,一個望不到底的海,輕輕說著:「這江水,淹得真快。」。
塵宵,立在了海面上,抬手摸了摸長生殿的大匾,那個玉竹製成的大匾。
陽世四十五年的人生呀,對塵宵而言,太過漫長。
塵宵陽世間的帝王袍與帽冠鞋履,被將壇放在了那福繪旁成了裝飾。
凡人帝王的塵宵,成了將壇筆中的簑笠客,那深暗黃色的帝袍,若隱若現的藏在黑簑笠裡,而祂,是這福繪裡引海的那尊佛。
許許多多的罪業,是凡人自己造下的,塵宵,是去理帳的。
好不容易回來的長生殿。
果然是在陽世間走了一回,那塵宵身後的鬼差爺們,個個神色更加的寒冷。
仔細地瞧著,每個鬼差爺的身上臉上也都不乏傷疤,可沒有凡人知道,正神佛,身上都是有那證的傷疤的。
誠如那東嶽大帝,臉上的傷疤可都還在,祂都已經是最大尊的佛了。
死去了一個帝王,回來了北嶽大帝,塵宵,也不過剛證成那北嶽大帝而已。
太過寒冷的風,在長生殿內吹起。
所有的物品都結上了一層薄薄的冰霜,連長生殿內都下起了雪呢。
很快的,許許多多的銀舟從深深的長生殿內飄了出來,是的,可又有誰知道呢?這長生殿,是那水之殿。
淡淡的寒江水,是那透明剔藍的冰川,慢慢的淹起了整座殿。
可得踏上那銀舟,讓那川水送舟入殿,否則,可沒有哪位官亓可以越過五嶽大帝行走入殿,這可是塵宵親自訂的規矩,這寒江水,塵宵輕輕擺擺手而漫淹起的。
這霜凍的寒江水,可以淨了所有神亓,所有神亓好似上了無形的枷鎖,一舉一動都被束縛著的,這是北嶽大帝的法門。
無事不得登殿,是塵宵親自訂的規矩,免得那充滿好奇心的將壇,在休歇之時,鬧騰著跑來觀望動靜,但凡是那中壇元帥,武將的本性,藏不住的好玩心與調皮。
長生殿內的海江,自然名為那:長生川。
曾有那好奇的官員想掬起那寒江水,卻是手連碰都碰觸不到的。
誠如那西亭大帝手碰了那水,水也只是消失在手上,不留痕跡。
陰寒的氣息,是北嶽大帝獨門的氣息,一股冷冷的香很淡很淡的散在了寒江水裡。
今夜的長生殿,速速要起審的,畢竟北嶽大帝是出名的沒耐心。
塵宵走在了那江水裡,疾步向殿內。
而那銀舟上的官吏,個個直挺挺地站在了舟上,不敢輕舉妄動,可沒有誰敢坐下。
江水湍湍,掀起了那冰藍色的水滴,夢幻如此,卻是波濤之顛,駛的那舟有夠顛簸。
塵宵很急。
光看那畫生動的程度,祂便知曉,小小的中壇元帥已經在殿內等候了。
光看祂那帝王袍上的螭龍鮮活的張著爪,吐著赤舌,周身火焰紅紅的燒灼著,祂便知曉,小小的中壇元帥已經坐在那主審的龍椅上,調皮地搗蛋著,又等待的不耐煩著。
祂好不容易娶到的妻子,在等祂。
誰說那舟上的官吏不是呢?誰說那舟上的鬼兵卒不是呢?大家在陽世間歷劫之時,陰曹地府的家眷,可都是焦急的在等候著。
長生殿內的迴廊可是如此曲蜒,再精熟方位地列的武將軍,可都是會在裡面迷路的,思索著這些的塵宵,輕輕吐舌笑道:「我就是在說你,旭謙遲。」。
這旭謙遲生前也是遠近馳名的大將軍,可當初祂死後回到這長生殿,可是大鬧一場,因為祂迷路了,迷失在北嶽大帝親自佈的陣裡,堂堂西亭大帝,出名的鬼帝迷路,可是笑話。
越接近那長生殿,那中壇元帥笑鬧的聲音,可是響進了整座迴廊。
暖暖的木香,是妻子的法門,送著那暖呼呼的風吹出了長生殿的大門。
看看那持著黃令與黑令立在兩旁的兵衛,方可知,嶽佛都到齊了。
這長生殿的牆上,除了那幅繪,在那水光的映盪下,牆面出現許許多多的影像,有地嶽惡鬼圖,有那陽世的惡浮圖,有那血腥沙場圖,有那貧乞圖,有那血屍圖,太多太多今日要斬要審的鬼的生前影像,累生累世的為那水光映在了長生殿的各處牆上。
所有的判官、兵鬼卒,無一例外,都在觀著帳。
還有那在殿外,尚在草舟上飄盪的鬼們,也在看著自己生前的累生累世,還有那仇家的累生累世,那帳阿,就在它們的眼裡,凡人總是痴昧的妄想成那有通之人,塵宵在他們死後,便是如此將那它們生前妄求的觀落陰,原原本本的成了它們初死後,尚在候審時,眼裡唯一的風景。
漫漫長生川,是塵宵在開帳本的水川,藉那水川之光,映出所有帳。
有好小好小透明散著夕陽光的小金魚,游出了大殿門口,喔,塵宵是從不讓小小的妻子走入那長生殿的迴廊的,小小的妻子總是坐在龍椅上,被好好地守護著的。
那夕陽色的光暈小金魚,是妻子的法門,呆呆的黏在塵囂的面龐上,成了那紋青,為北嶽大帝這太過陰冷的臉龐,增添許多妝容,祂本就銳利卻斯文的臉龐,美艷了許多。
旭謙遲總是笑著塵宵,分明是武將,卻長了一副斯文面,當真是那表裡不一之人。
那光暈小金魚,染醉了塵宵的酒窩,恰到好處的,貼在了祂的唇旁,也繡在了祂那受傷的眼尾旁,那道紅痕,反而成了金魚嘴裡啣叼的棠花。
小金魚淡淡的夕陽光暈,暖了塵宵冰冷的臉龐,那是妻子的小手,在輕輕地觸碰著祂。
但凡有誰敢讓小妻子踏入這迴廊,都得被塵宵殺了。
每生每世,好小的妻子,都是在東嶽佛的守候下,在殿內的龍椅上好好的吃食著,被擁抱著等著祂歸來的。
「我回來了。」,塵宵輕輕地勾起臉頰兩側的酒窩,臉頰淡淡的紅暈,訴說著祂的喜悅。
殿內最深處,在那夕陽光暈醉光明處斜榻在戍嶽膝上的小妻子,是那少女的模樣,穿著那白霜織成的裙綢,那光暈染在她身上,好柔美。
看那地上摔碎的玉瓷碗,是小妻子在等待時玩玩的遊戲。
看,那龍椅桌案前的地板,有一層薄薄的冰霜水,游出許多小金魚,小小的妻子,剛剛摔碎了玉瓷碗在跟塵宵玩耍著。
一隻瓷碗裡藏了一隻小金魚,塵宵猜對了金魚的顏色,便會游到塵宵身上成了那紋青。
塵宵在這趕路的圖中,一直遙遙地與妻子玩耍著,報平安。
那薄薄兵霜水的水之中,游走許多小金魚和小鯨魚,漫漫的,俏皮的游到塵宵身前,游到塵宵身上,游到了風裡面。
那在陽世間的塵宵,身上一直有著金魚的紋青,更有那無形通的小金魚游在他四周,皆是中壇元帥庇佑的法門。
塵宵自戍嶽膝上抱起小小的少女,那身著華服的少女,眼裡有掉不完的珠寶,滾滾顆顆灼傷了塵宵的眸,四十多年的帝王,只不過在等著死後回來見她。
小小的少女臉上也有金魚的紋青,是她跟塵宵約定好的,在塵宵回來這天,要穿著白金魚繡滿的服裙,戴著那雕了許多白金魚的冠,等著他歸來,可都沒有人知道喔,這冷酷的北嶽大帝,喜歡的動物居然是那嬌小可愛的胖胖小金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