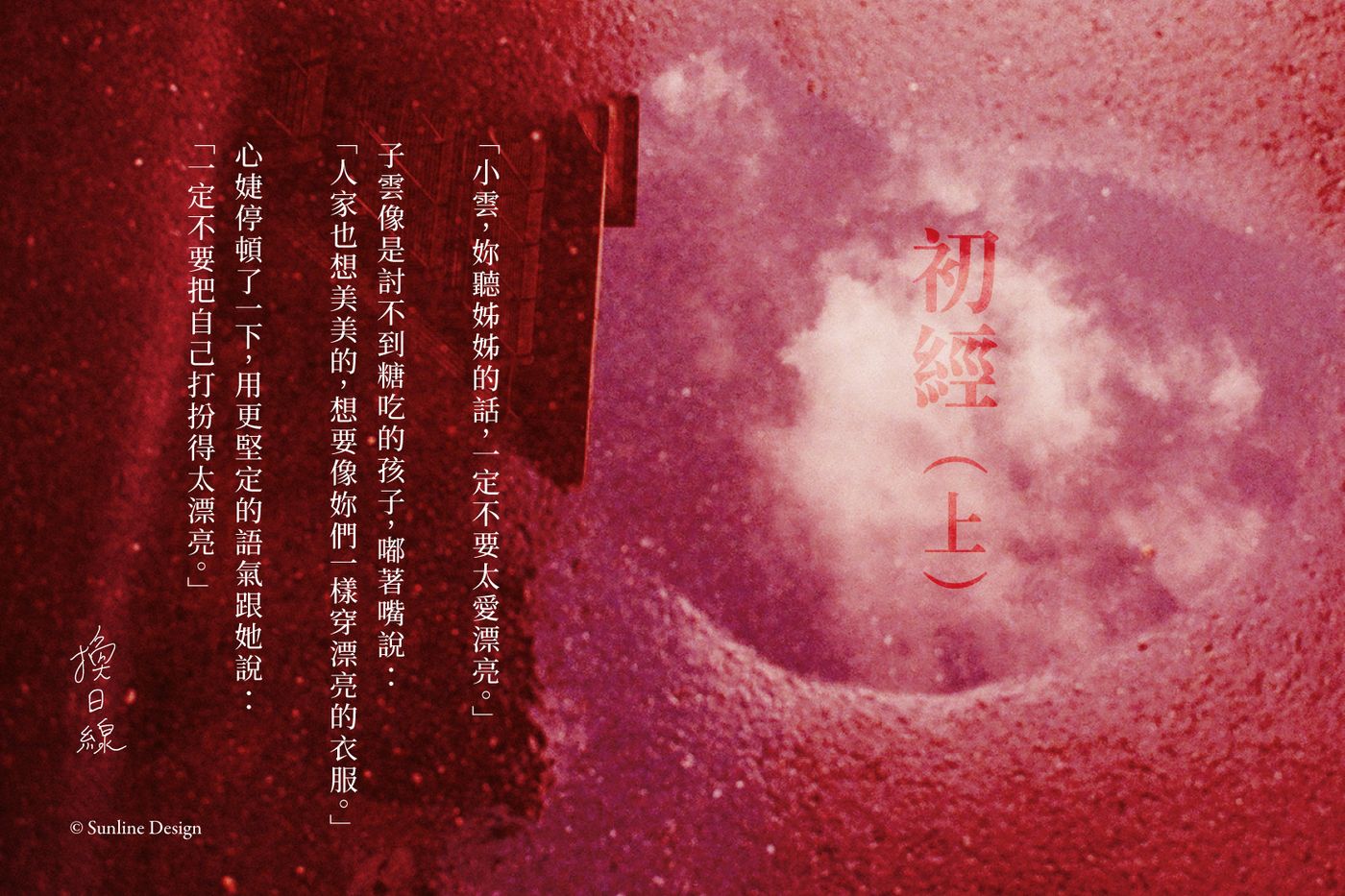她跳上床勒住老王的脖子的時候,老王的陰莖還留在趴跪在床上的子雲體內,子雲全身赤裸、雙手被綑綁在床頭,對老王進出自己的身體沒有做出太多的回應。
老王被她這麼一勒,從子雲的身體退了出來,他一手將她從自己的背上甩向床邊的地板,再起身抓住她的頭髮朝地板猛力地撞擊,直到她放棄反抗後,老王一邊揉捏她的胸部,一邊搓著自己的陰莖,在它硬挺後,從裙底拉下她的內褲,直挺挺地進入她的身體。
子雲在一旁發出微弱的聲音想要制止老王對她的暴力:「王大哥,你不要打大姊,你要我做什麼都可以,你不要打大姊!」
她聽見子雲微弱的聲音,想起自己第一天進到麗霞也像子雲一樣貓式般的被綁在同一張床上。她的制服被老王從身上撕出棉布的纖維,學號和姓名在撕裂出兩端的不規則,老王沒有再粗暴地扯開她剛發育穿上的少女內衣,他從她內衣下緣的鬆緊帶下伸進手,變換了不同的角度揉捏,丈量著胸部的大小,「再買一些補品給妳吃,妳這樣太小,沒有人要買妳的檯。」
她沒有掙扎,沒有力氣掙扎。在那之前,老王遞來幾顆藥丸和一瓶水要她吞下,沒多久她就只能任憑老王將她綁上床,無法做出任何反抗,但老王在耳邊說的每一句話都字字清晰地進入她的耳裡:「妳們那對父母,生妳們就是為了要送進來賺的。妳如果要怨,就去怨妳爸媽,不要怨我。」
她聽見老王解開西裝褲上的皮帶,金屬碰撞的聲音銳利穿進她的耳中,連同老王拉下拉鍊的聲音都清楚地像深夜裡誰突然翻身劃破原來的安靜。
老王脫下她的內褲,摸著她剛長出的陰毛,一根手指進入了她的陰道。她不感覺痛,只聽見老王呼吸的聲音越來越急促。
「等到小雯月經也來了,妳就會有伴了。」
聽到「小雯」兩個字,她用盡全力想要開口說點什麼,卻依然沒有辦法做出任何反應。老王放進她陰道裡的手指從一指、兩指、三指,最後他換上陰莖,沒有進入她的陰道,而是深深地插進了她的肛門裡。
等到她清醒的時候,老王已經不在這個房裡,她殘破的制服旁,除了全新的衣褲外,床上還有幾張鈔票。她感到疼痛,從雙手到胸口延伸到背、腰都像是猛力撞擊的車禍後隔天醒來時的痠痛,但更讓她痛哭失聲的是陰道和肛門的撕裂,像被誰拿著子不深不淺地劃在她的身上,每挪動一吋都讓她痛到想再回到沒有知覺的時刻。
她第一次從麗霞逃跑是一個熱鬧的跨年夜,麗霞門口擺了幾桌的流水席,是老王和其他幾個大哥出資宴請經常到店裡捧場的常客,還有其他也是被送到這裡賺錢養家的女孩和小弟們;她和其他跟她同齡的女孩們被要求穿上露出屁股的短裙,即使天冷得想套上羽絨衣,老王還是下令只能穿著閃著光亮的小背心,擠出她們或深或淺的乳溝。
其他女孩冷得發抖一一拿起一杯杯的烈酒往嘴裡倒去,只有她悄悄把杯裡的酒全都到在舖著大紅桌巾的桌下。但她還是被那些平日進出她身體的男人們灌了幾杯酒。
酒席的菜上到最後一道時,女人們坐在男人們的腿上,男人大聲划拳拼酒也不忘將手伸進去女人們的胸前、褲裡。她找了理由推拖了半天,才從人群中脫身,搖晃著帶著酒精的身體走進她接客、睡覺的小房間,拿出她預先準備好的剪刀沒有猶豫地剪去自己被老王交代麗霞燙捲的頭髮,再拿出她被老王打到送醫後,那些包紮她的傷口沾著各式液體的繃帶在胸前緊緊地纏繞著自己的胸口。
她從老王替她準備的衣服裡,挑出顏色最深的、沒有亮片,也沒有腰身的T-Shirt,再穿上那些衣物裡最不起眼的一條褲子,套上客人留在小房間那件不合身的厚外套後,她逃離了麗霞,在大多數人都沈浸在酒精的跨年夜裡。
她手握著幾次小孟離開她的身體後,在她陰道塞進幾張綑進塑膠袋的鈔票,走在山腳旁的小巷裡不斷地變換路線,她不知道自己能走去哪裡?直到回過神的時候,大馬路上跨年倒數的聲音在耳邊響起,升上天空的煙火點亮了黑夜,她才從路邊的車窗上看見自己的倉皇。
*
我離開老王將我綑綁的那間純白的房間,已經是初經沾上內褲的十年後。那十年中,我像心婕一樣不斷地從麗霞逃跑,也像詩雯一樣企圖想用一次又一次的性愛中得到老王的信任,希望可以換到離開麗霞的自由;我更像子雲一樣,以為只要能夠賺錢,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卻從這個火坑跳進另一個火坑。
我偶然得到老王的允許能夠跟著麗霞在店裡學一些不靠男人進入身體賺錢的功夫,從洗頭開始跟麗霞學起,接著是剪髮、刮鬍、修剪指甲、燙髮、染髮⋯⋯店裡那些在我身體裡進出的男人,有不少都被我刮過鬍子。我從他們的閒談裡慢慢得知老王挑選女人的規則,其中一項是初經來後規律的經期滿一年,像是生啤有一定的期限,過了那個階段就會走了味。
最後一次逃離理容院是老王開始往另一個山腳下頻繁走動,不常出現在店裡的冬天。我帶走麗霞給我一組刀具,以及幾件客人留下來的衣物,還有在理容院工作的分紅,趁著整理理容院毛巾的午後,從透天厝後方的防火巷奮力的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直到我搭上客運抵達另一個城市落腳幾個月以後,才真正相信我終於離開老王、逃離那個用身體賺錢的惡夢。
那幾個月裡,我不斷在太陽底下奔跑、鍛練自己的體態,讓自己越來越沒有女人的樣貌,不再讓任何人認出我是麗霞的得意助手小孟;我在鄉下小鎮開了一間美髮店,專門收留那些無家可歸被送去出賣自己身體的女孩。
我本來以為我不會再回到老王那間有無數個女孩被他用著相同的方式在初經之後下藥、綑綁,再儀式般從手指到陰莖進入陰道至肛門的步驟開啟她們出賣自己身體初體驗的房裡。直到我從網路上一再看到心婕暱名的求助貼文。
我再度走進麗霞理容院時,麗霞已經不在,換上了幾個年輕的女孩在幫忙打理店內的生意,她們完全不認識我,甚至沒有任何人發現我是女人。
救出子雲以後,心婕和詩雯的聯絡方式全都沒有回應,慢慢的變成了空號,連同網路上所有聯絡的方式全都無法與她們兩個接上線。
我剪去子雲原來過肩的長髮,替她換去所有有女性特徵的服飾,帶著她在鄉間小路跑步,像是我剛離開麗霞那幾個月對自己的改造。
推刀從子雲耳旁剔出可見頭皮的平坦時,她對著鏡子裡的我問:「我以後是不是都要打扮得像男人一樣?」
「這只是暫時的,在妳有其他賺錢的能力養活自己以前,妳都不能被找到。讓自己像個男人比較好保護自己。」那是我離開麗霞以後,不斷告訴自己的話。
後記
這是七月底前寫好的故事,前半段寫得很快,一直到文學獎截稿前我始終想不好故事該怎麼收,就這樣交上去了。沒被選到是正常,也沒什麼得失心。倒是我還是一直覺得這個故事全文的對話理當要用全台語,國語我覺得怎麼寫都沒那個氣味。
這不算「只是聽來」的故事。應該還是離我很近的人發生的故事。記得馬世芳有集節目提起〈大武山美麗的媽媽〉這首歌是胡德夫加進了對原住民雛妓的關懷,原先我本來是要把這首歌加進這個故事裡,但礙於時間緊迫,加上我寫故事都超隨性的沒在寫大綱和結構,也就可惜了沒能把它們串起來。
我忘記,是誰告訴我這個故事?是當事人本來,還是從身邊熟識的人聽來的。後來我知道小雲也像我一樣與同性在一起,爾後又聽說她有交往的男友,但再見的時候,我們都是無法從外表辨識性別的樣貌。一樣是見了面不多說話,就是很輕淡的微笑著(啊!我們都還活著!)
未曾想過要去向她問這些往事,或問她的姊姊們這個故事的真實性(或細節)但始終都知道,我身邊有那麼一些人,很多都不是帶著被期待的方式降生在這個世界上,甚至很多人都是這樣過著擺脫不了的宿命的生活,即使你將他們丟往安逸的人生,他們都還會質疑那些不屬於他們,然後再逃回那些宿命裡!
生活是充滿苦難的。
我們僅能在這些苦難裡,多一點對世界的寬容和慈悲!
P.S
這幾日忙,也真沒空重新讀過和修改。也許下次我再打開這個檔案,就是想到怎麼把它更完整的呈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