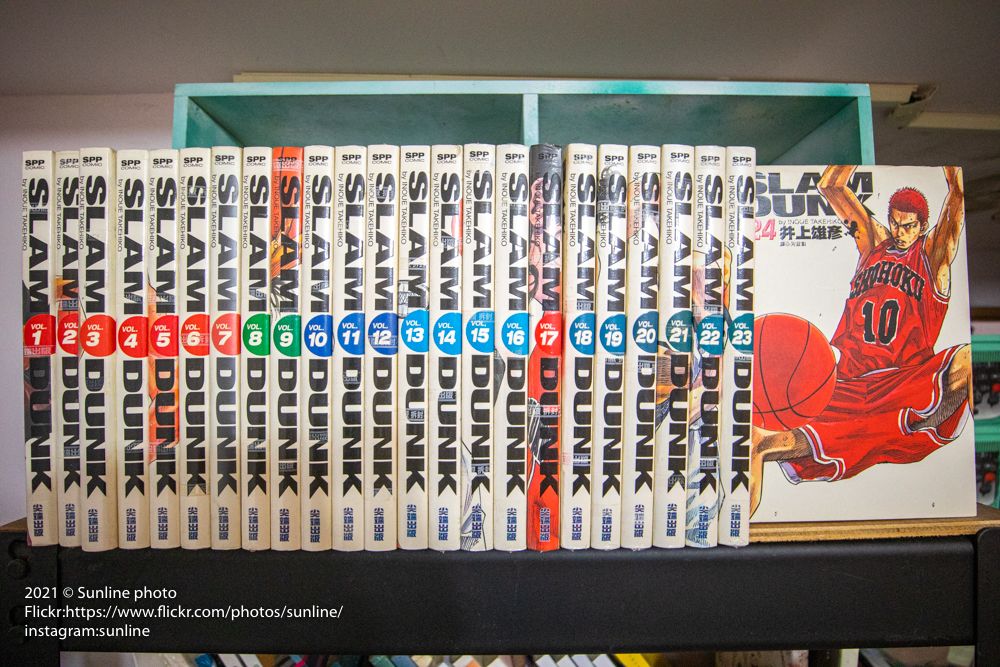從小並不是一開始就會閱讀的,但我現在還記得,在我小學中年級的時候,姑姑送了我兩本音樂家的傳記:蕭邦跟布拉姆斯。所以這兩位可以說是我最早認識的音樂家。那個時候印象最深客的,應該是蕭邦跟布拉姆斯的感情世界。因為故事的關係,我也一起認識了克拉拉。
現在回想起來,人物傳記之所以會吸引我、讓我至今還記得書裡面的一些片段,並不是因為歷史文獻或者是資料的關係——而是這一些人物的「故事」。這也許解釋了為什麼後來我非常的喜歡讀文學作品——因為裡面有著數不清的故事。
我自己並不是一個聽故事長大的人。或許是戒嚴時期留下來的那一種不安跟驚恐,所以在我的家庭裡,並沒有故事的存在,更不會有想像力這件事情。生命的維繫,比較多是關乎有沒有辦法可以維生。那並不是一個會留意「精神糧食」的時代。可能覺得自己的生命是非常慘淡而貧乏的,所以後來有機會浸泡在課外讀物的時候——再加上那並不是一個3C產品盛行的時代——書裡的故事世界,就變成了我賴以維生的支柱之一。所以,閱讀對我來說,有很大的部分,是因為我可以在那些文學作品裡面,找到很多很多的故事。
因為對於故事的喜愛,各種因緣際會,這幾年也開始涉獵一些歷史的東西、開始有「歷史感」。因為,許多的故事,都是從創作者所生長的時代跟環境裡面,成長出來的。(但我不是讀歷史文獻的閱讀者,這個科學的工作,就交給歷史學者們做研究)
所以,我覺得引領我的,似乎是對故事的濃厚興趣,而歷史則是提供了這一些故事的物質基礎。我常常在讀這一些「史」的資料或是文獻時,總會不自覺地去想像:在那一些史料空白的地方、那一些沒有被講出來的、沒有被書寫下來、沒有被任何形式記載下來的,裡頭可能會有什麼轉折或者是不為人知的內心世界。
小說家張貴興說:歷史鬼影幢幢之處,就是小說想像力介入之處。
這一種「個人特質」,或者要說是長期對「故事」培養出來的某種能力,現在時不時會把我帶到,讓我起雞皮疙瘩的時刻。比如說,當我在讀某一個人物的回憶錄時,其中的一段場景、某個物件,我竟然可以在另外一個人物故事裡面發現兩者可能的關聯。而這兩個人物的生命,在一般以特定人物為主的歷史記錄中,不大會出現。變成是只有我在閱讀時「偵測」到的、有如蜘蛛絲般的牽連。這幾次講道,也讓自己練習從不同視角出發去講故事,像是從民俗音樂、杜鵑樹、苧麻、一張登新高山的照片。
又或是,在歷史人物的傳記裡面,在那一些史實呈現之處,總免不了動用到長期在人文學門培養出的想像力,讀出誰的某一些選擇,放在歷史的脈絡下,是種「不得不」,或是有限之下的選擇。 也許就是因為這種觀察,讓我可以不會輕易的就掉到很平面的歌功頌德(之前在上基督教史課程的時候,老師曾提到,現在history這個字,有時會改用story了)。
而這種對故事的好奇,也讓我開始在走到每一個地方的時候,都會留意環境裡的東西、紀念碑、遺址等等——也就是說,每一個我行走的地方,都是一個文本。比如說,在一年多前,我們搬來到現在的位置,家裡附近有一個「生態公園」,而沒有想到這一個生態公園,其實是造船廠遺址。當時剛好在讀王聰威的《複島》,其中有一處關於「拆船」的段落(地點是旗津),讓我印象太深刻。 也因為閱讀地貌的拓展,當我行走在地景上,就會看到過去不曾留意的。
而且我記得,去河樂廣場的時候,那裡曾經展出過有關河樂廣場的前身的歷史記憶。這個又跟五條港的地貌牽連在一起。我現在每日生活的區域,有一大部份,在很久以前,是「海/水」路,不是「路」路。
甚至我在猜,明朝鄭成功抵達時,在現址為司法博物館之處設軍營,應是離港口不遠。
這裡曾經傍海而生,因而發展出密度相當高的廟宇(其實,現在新樓幼稚園那一帶,清領年間也應該有溪流穿過,不知是否為竹溪)。
對「水」開始敏感,應該是閱讀吳明益的《家離水邊那麼近》開始被「提醒」(請別誤以為我只爬山)。 也許是這一些不經意的、對歷史片段的知識累積,以至於今年在工作上有了一個新的任務——改編台灣文學家許丙丁很有名的作品《小封神》為繪本故事。除了《小封神》的宮廟都在現住家附近,讀起來很有熟悉感之外。在閱讀到最後,赫然被一句話「水路可利用堀頭港」(來迎神接官)擊中,把住所附近關於水/海/港的記憶,全數喚醒(但一位基督徒來改寫宮廟神仙道士的故事⋯⋯今年實在太神展開了哈哈)。
(順帶一題,玄天上帝也是「海神」,因其管理水上水下之事與生物)。
那一瞬間確實有一種雞皮疙瘩的感覺。因為各種走讀、閱讀的累積,最後總會引領我到未曾意料的地方,卻又如此契合。 又因為這一些知識/能力的累積,可以讓我較容易當起偵探,給予不同的想像跟說故事的角度。
我相信上主是終極的編織者(關於編織的概念,請見〈生命的編織者〉),聖靈的運行,則是讓人能夠編織、創作、成為故事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