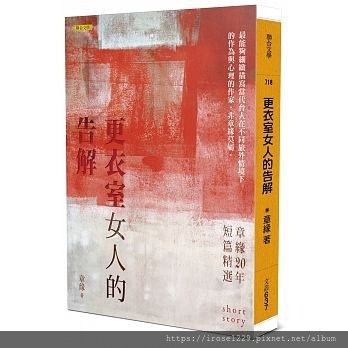老樟新桃交叉,木輪紅爐依傍,綠荑長路漫漫,乳香泡餅一碗。
「鳴,你再不吃就要涼了。」聽得叫喚,夏時鳴方轉正身子,囫圇嚥了一口牛奶泡餅,目光仍是不離身後的大道。
過了一會兒,安奉良問:「老闆,都督真是走這條路嗎?」
推車後,攤子老闆滿頭大汗,添新柴、搧爐火,攪一攪鐵鑊中的牛奶,記下新來的客人要吃甚麼,仍可忙裡答話:「三府都督從潤州南下,視察民情,揀陸路肯定走這邊!客官您瞧,今天生意這麼好,也是托都督們的福,大夥兒都想瞅瞅他們出巡的威風。」
附近聚集許多民眾,幾個聰明的小販遂跑到這裡擺攤,安夏二人來得早,猶能坐到位子,晚來的人想品嚐甜品小食,只能站著吃了。
大約又過一個時辰,才聽聞有人高喊:「來了、來了!」
循聲望去,先見兩支繡旗委蛇,近三十人列隊於後,中間三人騎馬並行,身邊的侍衛左手按刀,右手擺臂,行進的步伐穩健,數十人的足聲整齊如一,無人搶前,無人落後,足見紀律嚴明。
隊伍中最搶眼的,是那三隻體格肥碩,昂首踏步的座騎,即便是不懂馬匹之人,亦嘆服三駿健壯如龍。馬上的人亦非泛泛之輩,兩眼炯炯有神,髯鬚濃密烏黑,錦衣光鮮亮麗,小刀砥礪契苾真,噦厥竹筒打火石,再一把大金刀繫於玉帶,七事環腰,英姿勃勃。
圍觀的民眾很是興奮,熱烈討論,言中皆是讚嘆三府都督的氣派。惟夏時鳴與安奉良見了,思及要堆出這一身行頭,得粉碎多少家庭,搶奪多少民脂民膏,均憤慨於心。
安奉良側身低語:「要暗殺這三個人,不如突襲這個陣仗。」夏時鳴左眉一軒:「是啊,然後包袱綄綄,就可亡命天涯了!」他凝神觀看,續言:「這三人不是省油的燈,一對一正面交鋒,也未必有十足的把握摘下他們的腦袋。」都督畢竟是地方最高軍官,不是尋常武夫可比擬。
夏時鳴轉頭問:「老闆,你可知都督今次會在嘉興待到何時?」「這您就問對人啦!」老闆的消息相當靈通,流利對答:「我聽我大姐夫的表妹的小叔的姨媽說,這次榮都督帶領兩位遠道而來的都督四處參訪,觀摩江南的治理之道,這五日會住在嘉興西郊的明秀行館,之後便前往宣城。」
「感謝!」夏時鳴多壓數枚銅錢在桌,與安奉良相偕離座,隨後展開輕功,趕在護衛隊之前,來到官員下榻的明秀行館。
明秀行館是提供出門在外,刺史等級以上高官的臨時居所。其座落在一片平疇沃野,遠遠即見黛瓦白樓聳立,曲牆三面圍之,行館西面是一座蓮花小塘,無牆無垣,直接與外邊灌溉用的渠道相連。這邊亦有不少平民欲觀賞達官顯貴的排場,衛兵也更多了,守在道路、大門、花園、高樓、廊廡,個個勇猛強壯,站立不動時,彷彿一根根松柏扎根在地;行走四巡時,猶如一隻隻虎豹投足於周。
安奉良算了算,連同佇立大道兩側,這兒的衛兵將近八十之數。夏時鳴的下頷抬了抬:「那個迎接的縣官,合該是李勳。」此時李勳已審完顧高德一案,褪下染血的官袍,換上另一套衣衫匆匆趕來,恭候上官大駕。
待得隊伍浩浩蕩蕩地走來,暖陽西照,已近申時。
李勳打躬作揖,道:「下官拜見三位大人。」
榮世禮、武伯信及盛玉行齊齊甩鐙下馬,榮世禮說:「有勞李大人為咱們設宴洗塵,請。」「請。」李勳始終微彎著腰,將三位都督迎進行館。
趁著群眾尚未散去,安奉良及夏時鳴踱至西邊,遠眺行館內的樓舍。一幢位處東北,可將周邊概況盡收眼底的高樓外,另有兩間屋舍橫於樓閣東、北兩側,三棟建築形成直角,面對中庭的花叢草木。
意識到高樓上的守衛正往此方望來,安奉良趕忙扯著旁人的臂膀背過身,「行館很小,想來裡邊不會複雜到哪兒去,狗官們的房間不會太難找。」
夏時鳴道:「問題就在這兒的環境太過單一,曠野千里,光是接近就得費上一番工夫,而此後如何神不知,鬼不覺地殺掉三人,更是困難。」
這時恰有一頭繫著鈴鐺的黑騾拉車行來,車斗上的竹簍載著時蔬鮮果。
見安奉良對著數簍蔬果若有所思,夏時鳴說:「想藏身竹簍,你得把身軀剁成八塊才行。」「我看刺殺一計是行不通了。」他嘆:「行館裡三重、外三重全是人,蒼蠅都飛不進。」夏時鳴亦不抱希望,僅道:「先回去再說。」
二人依照許震海的指示,前去韋陀寺,抵達時人都齊了,開始講述適才所見所得。
安奉良看楊芳的臉色蒼白,當問:「王淦呢?」
許震海頭枕雙手,右腳搭著屈起的左膝,懶懶地答:「火猿寨確實是狗官養出來的,那小子把勒索來的黃金藏在那些狗官的祖墳裡,然後就滾去見他祖宗了……嘿嘿,是小女娃殺的。」
藍渝樺和洪珺萱一驚,雙雙朝楊芳看去,盧筠甄握著她冰涼的素手,反覆來回搓熱,「王淦出言污辱大小姐,小芳衝動之下,便用髮簪刺了他……」
不相信她一人能夠殺死王淦,夏時鳴眉峰一挑。寧澈瞧出他的狐疑,加以說明:「簪子刺到他前,老先生先用石子擊中他的頸動脈,使其暈眩,楊姑娘這才安然無事。我將插在心口簪子捅得更深了些,後再拔出,他便失血過多而亡。」
夏時鳴點點頭:「狗官住在西郊的明秀行館,我們在那邊有見到李勳。顧仲堯呢?在牢裡還是在家裡?」
「在家裡。」這一答,楊芳眼神一黯,然藍渝樺旋又道:「被擔架抬回家的。」
眾人瞠目,盧筠甄問:「他受傷了?」
洪珺萱更正:「不是受傷,是死了。」聞言,大家更為驚詫,於是她娓娓道出公堂上所有經過。
聽罷,許震海嗓聲微揚:「喔……出乎意料啊!」
桓古尋道:「他不怕那些世家大族,是否能邀他加入咱們?」然則寧澈不甚贊同:「難說,顧仲堯在大庭廣眾下襲擊李勳,李勳有充分的理由格殺他,但那三個都督不同,尤其咱們走的還不是正當、合法的路子。」大手捏了捏後頸,刀客另問:「行館那兒的地形長怎樣?」
「行館周圍十丈內甚為平坦,無林木樹叢,亦無農舍民房,僅一條溝渠連到行館西側的水塘。」安奉良扁扁嘴:「此外尚有八十名衛兵重重把守,想刺殺,那兒不是一個好所在。」
夏時鳴提議:「要不派人打聽打聽,獲知他們的行程,再選個好下手的地點,預先布置。」「都督身份顯赫,死於非命勢必驚動朝野,傾力調查。」寧澈道:「吾等不宜同太多人接觸,像是探聽情報,能不做就別做,不留一絲線索破綻,方得置身事外。」
「你仍想在行館刺殺?」許震海重新綁好鬆掉的頭巾,「這種暗搓搓的事情我不擅長,小娃兒別想使喚我,我去杭州等你們。」彈腰一挺,拍拍臀上的茅草,就要往外走。
洪珺萱本想挽留,卻聽桓古尋說:「藍姑娘,你們四個也先去杭州。」
「你確定?」藍渝樺黛眉微蹙,覺得不妥:「都督可是武官,再不濟也不是說殺便能殺的,多點人手總是穩妥些。」「但也容易被追查到。」寧澈指指樓上,「王淦的屍首就麻煩你們了,剩下的我們來就成。」
「我和安奉良也要參與刺殺囉?」夏時鳴道:「若要回行館查探,最好喬裝一下,左近的民戶應留有不少衣物。」然後直身欲行,安奉良、桓古尋、寧澈亦朝門口移動。
瞧他們不顯憂色,楊芳信心稍增,感激涕零:「四位的恩情,小女子今生莫敢忘卻,該怎生回報才好?」
跨過門檻前,嗜吃美食的青年回首噙笑:「素聞嘉興的南湖碧香醇甘美,勞楊姑娘捎幾罈來,給安某一嚐為快。」
*****
是夜,離行館最近,約莫十二丈之距的茅舍,窗戶開啟一道細縫,僅容單目遠觀目標。
時值三更半夜,除了天上的眉月靨星,行館稀微的燈火外,眼目所及,是石硯濃墨般的黑。
「高樓,子時四刻交班……」鳳眸緊盯行館內部的一舉一動,夏時鳴聽著寧澈口述,一字不漏地提筆記下。
安奉良豪飲一口南湖碧,咂嘴讚道:「這酒不錯喝。」然後從懷裡取出飯盒打開,是一隻炸得金黃酥脆的乳鴿。
饕客津津有味地吃著,香味還惹來嘴饞的黑貓,喵喵叫地討食,他亦不吝嗇,撕下可口的腿肉,與之分享。
「咱們一路爬來,你還能隨身攜帶酒食,真服了你。」桓古尋的臉髒兮兮的,倒出水壺裡的清水沾濕袖口,胡亂擦拭。
一如他所言,四人披上草葉偽裝,摸黑匍匐,爬至這間農民擺放工具的茅屋。為求謹慎,他們欲連續監視三晚,弄清行館的布防,此夜是第二晚。
夏時鳴邊寫邊問:「總共幾個衛兵?」
寧澈折下一根樹枝,在地上畫出館內建築大致的分布,說:「和昨晚一樣,高樓兩人,北面的走廊同是兩個,東面則是四個,西面的池塘一個,中庭花園兩個,大門口亦為兩個,深夜清醒巡守的有十三個。嗯……從入夜算起,他們約二更半換一次崗,一夜五更,會有兩班衛兵,共計二十六人輪番站崗,考量日夜作息,起碼有七十甚至八十名衛兵駐守明秀行館。」語畢,一樓兩房,花園水塘,粗略展現於沙土,他繼而道:「各處換崗的時分不一,四刻鐘為高樓,五刻鐘為東房,六刻鐘輪到花園,七刻鐘是池塘,八刻鐘……亦即下一個時辰,為北面房舍。」
安奉良道:「該選換崗的時候潛入,這樣較安全。」「不。」桓古尋搖首:「他們刻意錯開來換崗,就是要避免有人踩點潛入,某處在換崗時,其餘崗位必會特意看來。」
「阿尋說得沒錯。」寧澈道:「剛才高樓換崗時,守池塘的那個明顯側頭仰望,直至他們交接完畢,方正首平視。」
「然則咱們哪時行動,取決於要從哪裡潛進行館。」夏時鳴思忖:「狗官皆住在東側的房舍,照理說除開守走廊的,三個都督應再各有一名門房服侍,是以東側布兵最是嚴密,北邊是衛兵睡覺的通鋪,人最多,南側僅正門一個出入口,幾無遮掩,如是一來,最佳的突破口便是……」
「西面池塘。」另三人異口同聲。
桓古尋伸出食指,畫出彎彎曲曲的線條,連至代表水塘的圓圈,「順著灌溉的水渠,即可游入池塘,上岸前,得先解決池塘邊的衛兵。」「高樓的那兩人怎麼辦?」安奉良道:「他們地處高位,可即時看到底下有變。」
「放倒池塘的守衛後,再假扮成他。」寧澈說:「夜晚光線昏暗,只要不是近距離照面,或體型差距太大,難從遠處發覺異狀。」
「好。就這麼辦。」夏時鳴道:「順利上來後便是中庭,接下來要怎麼走?」
安奉良伸指比畫地圖,「從南面繞過去。雖然此處的遮蔽物少,但正門的守衛該是看外不看內,僅需瞞過中庭那兩個的耳目,就能直達東側的廂房。」
「到了東廂房,至少有七個人看門。」紅舌舔舐犬齒,桓古尋苦思:「最理想的是繞開守衛,祕密擊殺三個都督,但……怎生繞開呢?」
安奉良又道:「憑藉花叢隱蔽,或能繞至東廂的後邊……」「你想從後窗偷襲?」夏時鳴皺起眉頭:「那必須一擊即中,而且得同時斃掉三人,否則會陷入最壞的情況──正面衝突。」
桓古尋忖說:「試試將人引到窗邊,一刀抹脖子。」
「不行。」寧澈反對:「現場不能看起來像凶殺案,三個都督死在這邊,不僅地方官,連帶行館內的士兵皆會遭到處置,輕則降職,重則殺頭,這不是咱們的本意。」
斜飛的眉角一揚,夏時鳴問:「你要偽造成意外死亡?怎麼弄?其他人會信嗎?」
「不信也得信。」他狡黠一笑:「怯邪帖可深入人體,不傷經絡,僅束緊心脈,造成心肌缺血,進而使心臟無法跳動而亡,狀若暴斃,無人可驗出真正的死因。」
桓古尋道:「那得碰觸心口,緩慢渡氣,才能騙過驗屍的仵作。誰會讓你乖乖按著自個兒的心臟渡氣?除非……」
「除非被迷昏了!」提議者胸有成竹:「這樣就有足夠的時間,殺人於無形。」
夏時鳴只覺異想天開:「怎生迷昏?徑直讓他們聞迷魂香嗎?」沒想到寧澈真的說:「正是。」見人欲要搖頭,遂再續:「我知悉一種無色無味的迷魂香,惟醫術高明的大夫透過驗血,方知昏迷者被下了藥。我打算等他們都睏去時,放香迷暈,再徒手戮之。」
安奉良抱著雙臂,僅問:「用這個方法停止心跳,你預計多久殺死一人?」
長目一閃,有點心虛:「一盞茶到兩盞茶……吧。」
「光殺一人就如斯費時,何況要殺三個!期間還要避開守衛,接連進出三名高級軍官的房間,過程中哪怕一人在睡夢中翻個身,即有失敗之虞……」夏時鳴滿臉不同意:「你是去殺狗官,不是去送人頭。」
「我沒有要送人頭。」寧澈反駁:「阿尋,你也講點話,狗官只待在這兒五天四夜,僅剩第四晚能動手,沒有考慮謀畫的餘裕。李勳斷案公正,雖然三個上司死在轄境內,但沒有他殺之嫌,他不會隨便抓人頂罪,無後顧之憂,況且……澤山錄可不是吹噓的。」
「澤山錄僅能降低常人發現咱們的機會,不能隱形。」他肅容沉聲:「太危險了,想另一個辦法。」
而後一室寂然。
半晌後,寧澈舉手故問:「有人有說話嗎?」
「唉……」桓古尋扶額長吁,終是妥協:「答應我,一有狀況,你要立即撤退,我們也是。」
「那是自然。」寧澈拍胸保證。
*****
饑貓擭田鼠,泥鰍入稻田。
水聲潺潺中,寧澈、夏時鳴、安奉良穿上深色水靠,咬著蘆管,跟隨水渠的流向,魚貫游至行館的池塘。
蓮葉作蓋,蓮莖為幕,三人悄無聲息地探頭出水,收好蘆管,戴上面罩。
一兵獨立池畔棧道,臉朝外面,隨意巡視左右,渾然不覺腳邊動靜。
此方沒有圍牆,可謂門戶大開,仍只派單兵站崗,不是疏失,是因這裡視野開闊,一望無遺,加上緊鄰北側兵房,縱然外敵潛游靠近,亦只能止步於此,一旦離水登岸,絕對逃不過衛兵的兩耳雙目。
衛兵就在寧澈三人的頂上,夏時鳴和安奉良屏氣凝神,空舉雙手,似要接住某物,寧澈則緩緩擎起右臂,視線鎖定高樓上,面朝此側的衛兵。
三人維持動作不變,耐心等候,直到高樓的衛兵打了個大哈欠,想坐下打個盹兒,上半身方矮下牆垣,寧澈即刻屈臂下拉!
「啵。」一顆石子打在池畔衛兵的右太陽穴,力量不大不小,剛好令人暈眩左倒,就要落水濺聲!
「嘿。」失衡的軀體倒在高舉的四手中,寧澈掏出細針,迅速朝人後頸一扎,麻藥入體,衛兵便雙眼翻白,昏睡不醒。
三人趕緊將之抬回棧道,快快登陸,由寧澈把風,安夏二人負責剝下衛兵的外衣,而桓古尋從北邊跑來,把彈弓收入懷中後,跟著扒下兵服。
兵服一脫,桓古尋隨即穿上身,再解下衛兵的頭巾,纏在髮頂,「我留在這裡。」
將昏死的衛兵拖入草叢後,安奉良言:「有任何異變就吹哨通知,我們會立刻撤走。」
寧澈遞來一管針盒,「這是麻藥,一針能使人昏迷一個時辰,雖然這回暗殺預估僅耗半個時辰,但以防萬一,一盒放在你這兒。」
夏時鳴蹲身面往中庭,覷守衛越走越遠,遂招手催促:「該走了。」安奉良亦弓腰伺機。
把針盒塞向好友後,寧澈方要遠開,手背驀地一熱,被溫暖的大掌包覆,他奇怪回頭,但瞧一雙晶瞳澄淨:「萬事慎重,你的傷才方好。」光潔的下頷輕點,頎長的身形偕夏時鳴、安奉良跬步而遠。
「呵啊──喔!幹嘛打我?」被打的衛兵摸著熱辣的雙頰,半是莫名半是氣惱。
另一個衛兵年歲稍輕,然表情嚴肅:「丑時才過一半,阿彥哥便呵欠連連,請您打起十二分精神,以防宵小入侵。」
老兵沒好氣地道:「瞎操心,你知這裡有多少將兵嗎?三位大人的本領有多高嗎?誰有那麼大的膽子,夜闖明秀……」「甚麼人?」年輕的士兵猛地一喝,奔往花園南側!
老兵後知後覺地跟上,只見牆角一盆玫瑰花倒地,先到的新兵提著燈籠,四下搜索。
「喵。」一聲貓叫,抬頭瞅去,毛色烏亮的小貓端坐牆頭,悠閒地舔著左前腳,應為鄰近的農家所飼。
「你看看你,不過一隻小貓,就嚇得你豎毛。」老兵忍俊不住,噓聲趕走黑貓後,續:「放輕鬆,今晚守完夜,明天再護送都督至吳縣,就沒咱們的事啦!」而後長臂攬過同袍的肩背走開。
僅一屏花草之隔,三名不速之客摀鼻憋氣。
有驚無險地通過中庭後,來至兵防最重的東廂。
和早前監看推測的一般,兩個衛兵分佇房屋兩側,一左一右,還有兩個因視角阻隔,從這裡看不著人。都督們所住的三間廂房外,各自盤坐一卒,閉目養神,隨時聽候房內大人差遣。
潛匿而進的一行人躲在草叢後,屋前是平坦的石子路,可不能大喇喇地走去。
正自思考對策,倏爾一陣涼風,吹得廊上的火炬明暗不定,守衛的注意力甫被引開,寧澈下意識騰身一撲,滾過石子路,閃進對面的杜鵑花叢。
安奉良和夏時鳴來不及趁隙穿越,和他面面相覷。
環目四周,寧澈的左邊有棵高大的樹木,樹幹粗壯,枝葉繁茂,直壓屋瓦房檐。他遂心生一計,使眼色要對邊的夥伴稍安勿躁,隨後輕身上樹,兩三下爬到樹枝和屋頂的相疊處,瞥了瞥腳下的火炬後,深邃的鳳目闔上,呼進一大口氣,再沉沉長吐,天地萬物,俱納己有。
今夜的風甚是不安分,再度吹得炬火忽大忽小,衛兵們忙張掌阻擋風勢,免得火焰熄滅,未察前路左處,又有兩道黑影相繼掠過。
杜鵑花叢一直延伸至屋後,終至最末一道關卡,果見另兩個衛兵把守後防,一者離己方較近,一者偏向高樓。
寧澈復摸出一管針盒,食指拇指捻出一枚銀針後,瞄準擲出!
投擲的力道太輕,方觸及褲腳便給彈開。
安奉良亦捻針投擲,勁道是夠了,卻射在衛兵後面的牆上,準心得再練練。
「你在幹嘛?別浪費我的針。」耳聽質疑,安奉良反問:「那你又在幹嘛?」「我來。」夏時鳴隔開兩人,也捻起小針,閉起左眼,單以右眼測距對正,右手前後搖擺數下後,脫手扔出!
依然沒中。
不是三人臨場失常,而是他們均非使用暗器的好手,銀針既細且小,沒下過苦功,自是不悉如何拿捏準頭力氣。
瞧盒子裡僅餘兩針,不由得結舌呆愣,心想該不會要栽在這兒?
兀自煩惱,安奉良不經意掃過牆頭,那隻差點害他們暴露形跡的黑貓又來了!他眼睛一亮,道:「我有辦法。」先讓夏時鳴及寧澈退至一旁,自己則窩在衛兵正前方的花叢,儘量伏低身體到縱使有人行近,亦不會被即刻看見,然後面向牆上那隻饞貓,吸吮手指,故作嚼食。
綠色的貓瞳咕溜一轉,旋即縱身入懷,安奉良一手抱貓,一手抓住杜鵑花枝,輕輕搖晃。
衛兵見狀,好奇走向這叢杜鵑花,安奉良拍擊貓臀,受驚的貓咪嗖地竄出花叢,衛兵目視貓兒跑離的方向,剛欲旋身返回,即墜入夢鄉。
安奉良單手拎著衛兵的前襟,控制其軀,狀似自行蹲下,再拉入花葉茂密的深處。
二度扒下兵服,這次由夏時鳴穿戴,著裝完,他邁出花叢,直朝遠側的衛兵。
屋後緊鄰圍牆,通常不會有人通行,故無特別設置燈炬,僅靠月光和高樓散出的些微火光照明,可說是伸手不見五指。
站在高樓和東廂之間的守衛依稀瞧著紅衣紅巾,不疑有他,問:「怎麼了?」
夏時鳴不答,隨手亂指,那守衛中計扭頭,他瞬時欺近,捏針扎人。
再一人倒下後,安奉良套上他的衣服,對寧澈說:「快進去。」
寧澈運功感知,確認屋內的人已然入睡,遂開窗翻進。
甫入內,但瞧矮几蒲團,躡至轉角,才見床榻中央隆起一團白色的被褥,鼾聲若有似無。那人背對刺客而臥,睡得很熟,吐納間鬚毛顫顫。
寧澈揣著竹管,拔去頂端封條,湊至那人的鼻間,數息後,掐了掐他的頰肉,沒反應,遂伸手進被子裡,貼住左胸。
鼾息止了,心跳也停了,寧澈仍沒離手,持續運氣鎖住心脈,過了約半炷香,人面呈現死白,刺客方收手,沿原路而出。
關好窗門後,寧澈和同伴示意沒問題,又啟開第二扇窗,再次躍入房內。
第二間廂房,同樣走過待客用的几案,悄然步至床邊……
「咳、咳咳咳……」忽然一連串的嗆咳,驚得人縮在矮櫃後。
床上躺的是潤州都督榮世禮,他迷迷糊糊地起身下床,拖著腳步踱到窗邊的木案,拎起案上的銀壺咕嚕嚕地灌,再抹抹嘴角水漬,後踅回床榻,鑽入暖和的被窩。
若非室內近乎全黑,暗處的寧澈極盡所能地鎮住心神,與牆壁矮櫃融為一體,鐵定事敗逃跑!
待榮世禮二次睡著後,刺客略鬆一口氣,再以相同的手法暗殺,重返屋外。
涼風拂來,寧澈打了一個哆嗦。
夏時鳴道:「穩住,無須心急。」語罷,目送他三度入房。
這間房睡的是武伯信,其睡相豪邁,大字平躺於床,坦腹酣眠。
迷香奏效後,寧澈正欲動手,卻突地迴身!
左臂一揚,抄住暗空中的飛鏢。
房外的安奉良與夏時鳴大為錯愕,萬萬沒料到有人霍地翻牆而入,再快速越過窗臺進房。
夏時鳴右手一撐,也縱進房裡,安奉良則在外頭望風。
為防暗殺敗露,四人遮住面貌外,亦無攜帶平時慣用的兵刃,以免遭人指認。寧澈鏢夾指間,直擊不知名的黑衣人,但黑衣人偏頭閃避後,順勢搶進身前,挽住他的後頸,發力下壓之時,右膝猛然抬起!
寧澈交掌擋住迎面撞來的膝頭,並後勾左腿,形如蠍子擺尾,欲蹬人臉面!
然黑衣人腰微仰,又一次躲開攻擊,再出招前,右邊先一腿橫來,正為夏時鳴!該者及時彎臂格擋,旋即退開,寧澈緊追其後,逼人至牆角,正要發招,他卻倏地踩牆一蹬,借力反踢!
一腳踹中胸膛,寧澈應力後飛,撞翻家具前,夏時鳴趕忙騰身抱住。
拳腳數度往來,激烈非常,卻安靜無比,門外的衛兵絲毫不察。
寧澈及夏時鳴不欲糾纏,正想出去,那名黑衣人瞅了眼失去知覺的武伯信,竟細聲問說:「你們也是來刺殺他們的?」由於戴著面罩,其聲模糊不清。
夏時鳴訝然:「也是?」黑衣人下頦一頷,而後左臂一敞,「要殺他的話,請便。」
雖然疑點重重,但當前不是辨認話真話假的時機,寧澈繼續方纔未完成的事,夏時鳴則提防著好壞未明的蒙面客。
黑衣人沒有乾杵原地,他走到書案前,一一拆閱木案上的書信。夏時鳴旁觀許久,才問:「你在找甚麼?」
「一封私人信件,講的或是無關緊要的小事,抑或貨物進出之類的賬目……也有可能提及黃金……找到了!」語焉不詳的人抓起一封信塞進兜裡,夏時鳴瞭然直問:「你也曉得武伯信他們和火猿寨是一夥的?」
他愕然抬首,未及應話,寧澈走來便道:「好了。」
黑衣人反向步回武伯信身側,併指探向頸部,又撥開他的眼瞼,果然已經死亡,後撩開死者的衣裳檢查,毫髮無傷,尚自驚訝,夏時鳴已道:「餘下兩個也死了,你慢慢看,我們走啦!」
「嚓。」鞋履重踏草地後,安奉良語氣警戒:「你誰啊?」
「待會兒再問也不遲。」夏時鳴對黑衣人說:「幫個忙好嗎?」
於是四人合力,拖出仍在呼呼大睡的衛兵,還給他們衣服,並擺坐至原本的崗位。這個事先準備的麻藥當真好用,兩個衛兵被翻來覆去的,眼皮動都沒動,就算藥效退去醒來,也僅會以為昨夜是不支睡倒,而非中針暈死。
爾後他們翻出東牆,貼壁而行,經由北牆回到西面的池塘。
桓古尋苦苦等待多時,終見他們平安返來,本欲大步迎上,卻突然頓住,揉揉右眼,歪著頭:「你是……」
寧澈亦道:「等會兒再說。」
同將原來的衛兵整裝復位,四加一人終於大功告成,潛水遠走。
「嘩啦、嘩啦、嘩啦、嘩啦、嘩啦──」五聲水花淅瀝,行刺者先後坐上渠岸。
遮臉的面罩皆已拿下,寧澈見著半途加入的人,道:「居然是你,你不要你的烏紗帽啦?」
「你是第二個跟我說這話的人。」此人正為李勳。
夏時鳴斜睨著他,「我瞧他不只不要他的烏紗帽,頭顱也不在乎了。」
安奉良則問:「看你的舉動,是想直闖行館,與三個都督、六七十個守衛對攻?」
「是八十二個守衛。」李勳答:「連日來我左思右想,僅剩此法可行,本抱著捨身取義的決心,幸得上蒼眷顧,遇到爾等,事半功倍。」
「現在我是第三個人了。」桓古尋問:「你不要你的烏紗帽啦?」
李勳撫著膝頭,神情悠然:「有人目無法紀,李某既為人民父母官,豈能坐視不管?」
寧澈不敢苟同:「若照你的原意行事,即使真能刺殺都督,突圍亂軍,事後亦難逃處分,三個長官在你的地盤遇害身亡,上面若欲怪罪,丟失官位都算輕了。」
「天涯海角,總有容身一己之處;冠蓋布衣,各具造福百姓之道。」短短兩句話,盡顯為人處世。
桓古尋咧著犬齒:「小澈,這人比你還瘋。」寧澈白他一眼:「別亂講話。」而後頗感慚愧地別開臉:「先前是我誤會你,一聽到你是嘉興縣令,就認定你和三個狗官是同路人,才沒和你碰頭。」
李勳道:「起初我也怕你們不信任我,是故隱瞞縣令的身分,後來久等不到人,料想你們自有計較,王淦應已伏誅。惟首惡不除,憂患猶在,幾經思量方出此下策,殊料四位智勇雙全,能將謀殺變成意外,把損失減至最小,妙哉妙哉……美中不足的是,那些搜刮來的黃金至今下落不明,但願方才找到的那封信,會對此有幫助。」
安奉良遂言:「黃金在他們的祖墳裡。」「你怎知曉?是王淦說的?」李勳問。
「算是吧。」寧澈答:「黃金的事就勞煩李大人多費點心思了。」
「然而你這封信……該和黃金沒關係。」李勳的布兜不防水,下水前將信交給夏時鳴保管,現下他讀著那封信,並朗聲誦出: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
自三月拜別以來,孩兒無日不念母親音容,夜深人靜時,尤是難忍思情,常面天踞床,徹夜無眠。此行將走訪常州,其紫筍茶色翠味香,待孩兒捎帶回鄉,母親即得聞香品茗。
天候猶寒,孩兒公務繁忙,時常遠行,望母親體諒,肅此。
金安
兒 伯信 謹叩」
信一念完,安奉良嗤之以鼻:「三月還沒初十呢,他就想念母親想得要寫信傾訴,但見他所作所為,未免可笑。」
「這信有甚麼不對嗎?」桓古尋不解:「撇除他……很黏他的娘親以外。」
「李某這幾日接待觀察,武伯信簡直嗜酒如命,莫說是茶,水都我沒見他喝過幾次。若說是貼心,帶點土產孝敬老人家,然怪就怪在他的母親早已去世多年。」李勳道。
「這下有趣了。」夏時鳴道:「這封信是要寄給誰呢?」
寧澈拿過信紙折好,放回信封內,遞還李勳,「趁他人猶未知道都督已死,李大人何不在黎明到來前,替武大人辦最後一件小事,寄出家書。」
「當然,本官也想看看他究竟弄何玄虛,後續的事就交由李某處理,我會告知最新情形。」李勳接過信後,直腰立身,「今日一行,不但親見三惡伏誅,更結識四位英俠,有你們在,實為萬民之幸。李某一介散人,僅能以禮聊表敬意。」隨即躬身而拜,久久不起。
瞧他這般隆重,四個青年亦紛紛站起回禮。
長揖過後,李勳說:「有緣再會。」話罷,揚長而去。
桓古尋搔搔頭,「這人每次都這樣,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安奉良面有得色:「我倒挺喜歡他的,直來直往,不說暗話。」
「你是喜歡被稱讚的感覺吧!」夏時鳴出言戳破,後評:「不過這人的確謙遜有度,完全看不出他是當官的。」
「他也不該當官。」寧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