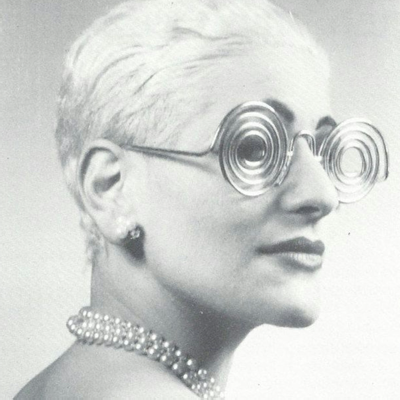技術物與藝術的關係:總體藝術與行動者理論的探討
檢視技術物和藝術的關係,以及討論總體藝術之中的巨大的權力不對等如何限制觀眾對於藝術的詮釋權。
在當代藝術與設計的領域中,技術物和藝術之間的界限愈發模糊。技術物通常被視為具有功能性的工具或裝置,而藝術則承載著情感和文化的意涵。然而,許多藝術創作的實踐表明,技術物不僅是藝術創作的輔助工具,更可能直接參與到藝術的生成過程中。技術物如何從純粹的工具性物件轉化為藝術創作的有機部分,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本報告試圖從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以及總體藝術(Gesamtkunstwerk)的角度,分析技術物如何參與藝術創作並成為其中的重要行動者。
2. 定義
2.1 技術物的定義
技術物(technological objects)指的是那些具備特定功能、用來解決問題的物件或裝置。技術物本身並不具備主動創造意義或傳達情感的能力,而是以其功能性和可操作性為主。然而,當技術物進入藝術創作過程中,它們可能獲得新的詮釋和角色,成為藝術品的重要組成部分。
2.2 藝術的定義
藝術則是一種能夠脫離創作者控制、產生自我影響力的創作過程。藝術作品不僅反映創作者的情感與意念,還能在觀者的詮釋中生成新的意義。藝術超越了單純的物質層面,承載著文化、歷史和個體情感,提出問題並促使人們思考。
3. 理論基礎
3.1 行動者理論與藝術創作過程
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每一個技術物都具有其能動性,並與其他行動者(包括人類和非人類)互動,共同參與到藝術的生成之中。行動者理論強調,藝術作品並非藝術家單方面的創造,而是眾多行動者相互協調、溝通和轉譯的結果。這個過程類似於總體藝術的實踐,即藝術家透過與各種媒介、透過這種協作過程達成共識,並由所有行動者共同確認藝術家的詮釋權威。
3.2 行動者理論與技術物的能動性
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提出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NT)認為,技術物在社會和文化的構成中具備能動性(agency)。儘管技術物並非人類行動者,但它們在與人類互動的過程中對社會現象產生影響。技術物不僅是被動的工具,而是能夠影響藝術創作方向和結果的活躍參與者。
3.3 總體藝術的概念
理查·華格納(Richard Wagner)提出的總體藝術(Gesamtkunstwerk)概念,強調藝術是多種媒介和形式的綜合體。華格納認為,音樂、視覺藝術、戲劇等不同形式的藝術應該互相協作,共同創造出完整的藝術體驗。在總體藝術中,技術物不僅作為媒介存在,更是參與藝術生成的重要元素。
然而,透過總體藝術的方式將技術物納入,也可能帶來詮釋權集中於藝術家之手的問題。在這樣的藝術場域中,觀眾往往處於無法對抗的弱勢地位,因為藝術家通過技術物創造出壓倒性的藝術體驗,使觀眾難以擁有自主詮釋的空間。特別是在沉浸式表演或裝置藝術中,觀眾無法逃離作品所設下的情境,這進一步加劇了藝術家與觀眾之間的權力不對等。這種單一權威的詮釋方式,雖然強化了藝術家的創作意圖,卻也可能限制了觀眾在藝術體驗中的多樣詮釋可能。
3.4 正當性與詮釋權威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提出,正當性來自於社會對某一權威或制度的認可。藝術家的詮釋權威即是建立在觀者、評論家和技術物之間的協調和共識之上。正當性是基於對某一政治體制或社會秩序權威的信任,這種信任進一步創造出內在的道德義務,使人們遵循這一權威。藝術家透過技術物的參與,鞏固並強化了藝術品的詮釋權威,形成一種內在的道德義務,使觀眾服膺於藝術家的詮釋框架。
"Legitimacy is the result of a belief in the authority of a poliFcal regime or socialorder, which creates an internal sense of moral obligaFon to obey authority."
4. 實際運用
4.1 諾蘭的《星際效應》作為總體藝術的實踐
克里斯多福·諾蘭(Christopher Nolan)的電影《星際效應》(Interstellar )是總體藝術概念的現代表現。這部作品將視覺特效、音樂、劇本、物理學理論以及演員表演緊密融合,創造出一個完整且沈浸式的觀影體驗。電影中大量運用科學技術物,如實拍模型、精密計算的黑洞影像模擬,以及漢斯·季默(Hans Zimmer)創作的原創音樂,共同構築出震撼的藝術效果。
這些技術物不僅是工具,更是推動敘事和情感共鳴的重要行動者。例如,黑洞「Gargantua」的呈現是基於物理學家基普·索恩(Kip Thorne)的計算模型,技術團隊通過數月的模擬和渲染,最終創造出科學與藝術交融的視覺奇觀。此外,電影配樂多次使用「崔斯坦和弦」(Tristan chord),這是一種和聲張力極強的音樂語法,首次出現在華格納的歌劇《崔斯坦與伊索爾德》中。崔斯坦和弦營造出一種持續未解的懸念感,使人感受到無盡的孤寂和未知,正好契合電影對於宇宙和時間的描繪,強化了觀眾的沉浸感和情感投入。然而這些技術性元素的組合在某些層面上形成了觀眾詮釋的權力不對等,進而限制了觀眾對電影的自由解讀。
首先,《星際效應》運用了高度精緻的視覺效果來呈現太空、黑洞、時間旅行等概念,這些視覺效果往往需要觀眾對科學和數學有一定的理解才能完全領會其背後的深意。例如,黑洞的呈現並不僅是視覺上的驚艷,更是依據科學家基普·索恩的理論設計的。然而,這樣的設計使得某些觀眾(尤其是對科學不太熟悉的普通觀眾)可能會感到困惑,無法完全理解電影的深層意圖。在這樣的情境下,電影的創作者(如導演、視覺效果團隊等)對電影的視覺呈現和科學背景有全權控制,而觀眾則在接收過程中可能缺乏解釋的自由。這種視覺主導的結構限制了觀眾的詮釋,特別是對於不懂科學原理的觀眾來說,他們的理解空間受到限制,可能無法完全自主地詮釋電影中的科學元素。
其次,電影的音樂是由漢斯·季默(Hans Zimmer)創作的,這些音樂在情感氛圍的營造中起到了強大的作用。例如,電影中大部分的情感高潮都依賴於音樂的加持,特別是在父女之間的情感牽絆和時間的流逝這些核心情感主題上。季默的音樂運用了大量的低音和宏大、緩慢的旋律來引發觀眾的情感共鳴。音樂在電影中的作用是讓觀眾的情感反應變得更加一致,幫助導演「引導」觀眾的情感經歷。然而這種情感操控性強的音樂創作模式可能會讓觀眾無法完全自由地詮釋某些情節或角色的情感。例如,在父親與女兒的告別場景中,音樂的強烈情感氛圍可能會使觀眾過度依賴音樂引發的情感,從而對角色的動機和情感層面產生單一的解釋,減少了他們自行詮釋的空間。
再來,電影的時間線是非線性的,特別是在關於時間相對性、愛與時間的關聯等哲學問題的探討上,這樣的結構設計使得觀眾對於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角色的行為動機等難以做到完全自發的詮釋。諾蘭巧妙地通過多重敘事線和時間膺懲的結構來探索人類情感與科學理論的交織。這種非線性的敘事方式將觀眾置於一個被動的解釋角色,因為觀眾需要接受電影所設計的時間結構,而不是自發地理解時間流動和事件因果的方式。觀眾的理解必須依賴電影的結構設計,無法完全自由地按照自己的節奏或偏好來解讀故事。
最後,《星際效應》探討了許多深奧的哲學和科學問題,如人類存續的意義、愛的普遍性、時間旅行的物理學等。這些問題涉及到極為抽象的科學理論,並且電影中的某些元素(例如第五維度的表現)需要觀眾對物理學有相當程度的理解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其背後的象徵意義。由於電影中的科學背景和抽象的哲學問題較為專業,觀眾在解讀這些元素時受到的限制很大。電影的創作者決定了這些問題如何被呈現,觀眾只能接受這些既定的呈現方式,這對於缺乏相關知識的觀眾而言,會造成一種權力不對等的情況,因為他們無法完全自由地詮釋電影中的哲學和科學內容。
5. 結論
技術物在藝術創作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透過行動者理論和總體藝術的視角,我們可以看到技術物不僅是被動的輔助工具,而是在藝術生成過程中具有能動性的參與者。然而,總體藝術的運作方式也暴露出藝術家與觀眾之間的權力不對等問題。藝術家掌控著詮釋權,觀眾被動接受作品所傳達的意義,缺乏參與詮釋的空間。這種權力結構限制了觀眾的詮釋自由,值得在未來的藝術實踐中進一步反思和探索。
參考資料
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Fon to actor-network-the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gner, R. (1910). The art-work of the futur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Weber, M.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Fve socio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olan, C. (2014). Interstellar. Warner Bros. Pict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