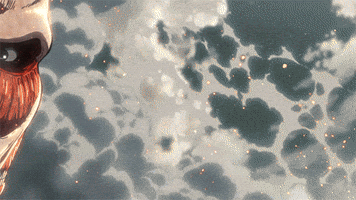【懷特獨白】蘭花賊:回到故事的發生地,將生活構築在幻夢與理想之外的現實中
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私心自作計畫|後青春焦慮的自我
情感電影是充滿詩意表現的象徵,經由作者揣摩事物直觀經驗的轉譯,向觀者吐露在這充滿赤裸昭示的過分感受。藉此,我們就能經過印象描繪情感意象的輪廓,穿梭在作者靈感湧現時,和文字筆下發生的美妙場景。從故事情節轉向揭露在編劇私密的創作過程中:總是想要寫出完美劇本的查理,卻也因此陷在自我僵局的困頓,同時,生厭使然的性格,也同樣讓查理保持在高尚理想的藝術思想裡,甚至逼近窮途末路的執著,將他沈淪在晦澀無明的死局。然而,與之不同的是類似基因的雙胞胎弟弟,既使處在塵世混濁的世界,又同時交出個人滿意的成績,使得在兩兄弟的對比中,也很明顯的交代他們性情與看待事物的不同,而此,沒有高大尚與假情操的處世哲學,這是帶入電影敘事的第一層。
敘事之二,探向事件延伸的情節片段:否去改作劇本明定的劇情走向,查理顯然有意表示超越原著的平庸,將其圍繞在人物與蘭花的故事,編撰在令人滿意的收尾,如是從淺俗的內容中脫穎而出、推崇蘭花的繆思或安排晦澀的電影寓意,相比兄弟之間抱持的創作信念,查理小心翼翼、總是以學理專業為意圖的實務方法,都使他處處設限。反之,映襯在查理所預期的結果,好的敘事並非是難以理解的劇作,能夠吐露真性、回歸質樸,在庸俗的劇本中抓住寫實與幻境的超越體驗,與之從生活情境中的微妙連結裡,獲得最直接的視覺回饋。便是尚好的創作難題。
查理急切賦予蘭花賊全新意義的不切實際,卻更貼近於自己原先的意圖,其無論是從記者之間的對話、兩兄弟的交談、片場中的互動關係,卻都讓查理的生活隨著故事一同轉向了陳腔濫調的內容裡。諷刺的是,查理保守的個性,對比兄弟查理的奔放情感,那不具有深度背景故事架構的劇本,對飢渴難耐的影視產業而言,卻是非常恰當嘗試,畢竟誰不喜歡編劇兄弟黨,於是,當約翰與劇組團隊一拍即合時,查理內心卻也不免興起一陣唏噓。回到劇本創作的突破上,這乏味可陳的劇本概念,既使查理力求突破,創作心境的限制框架,也不盡能夠讓他找到平衡點,使之,即如他預期的發展方向,這大膽的嘗試,卻狠狠的賞了自己一個耳光,如同作品的陳腔濫調,既沒有創新,就連這故事的邏輯都顯德無稽而乏味。
因為如此,作者與故事之間的關係也隨之惡化,產生出一種莫大的漏洞:由於不信任而使兩者沒有辦法獲得實際連結的破裂關係,又不經意的在手上的劇本中產生微妙的現象。顯然又回到了肥皂劇的庸俗籌碼了,正當查理想著蘭花賊故事最平凡的部分,只是一部以蘭花為題材發想的文學創作,並不令他感到任何獨見之處;但是,蘭花賊最具有繆思的部分,正是那平庸卻有可塑性的創作空間,於是,查理那難以抗拒的念頭,自然而然的將懸疑、弔詭的故事情節,飛車追逐、槍械元素的添入在故事的範疇,甚至,還有各種可能引發的意外,又一再變成他創作過程的一部分,以至於在這奇思妙想的突發事件,空洞、華麗卻平庸的故事,回應查理原先抱持的創作態度,毫無邏輯、不假思索地改寫,都使她陷入了自己的沈思中。
延續著創作的平庸性,故事映射的概念正如同作者個人的情緒反應,無論是從精神層次的解放或超越,現實的自我或保守的模樣,查理對於中年生活的頓悟,直到這交錯的人生歷程,終於也使他獲得截然不同的寫作方法:以至於查理駑鈍的社交關係、情感,和忠於自我的創作,無論是最荒誕的敘事概念,卻都將自己的生活經驗一同被包裹在其中,且同時由於情感真性的推動,更昇華成了這虛無世界下,一個具有豐滿創造力的生命歷險,並持續在生活與超現實情境的寫作世界中,不斷地擴散下去。
隨處可見的戲謔,讓人很難不察覺的安排,即是從查理發想概念、投入創作,以至夢中纏綿無數的夜,反芻在書中情節的投射,卻始終沒有產生一絲的火花,這在原作字句間充滿的意境,到頭來卻成了假象,於是,正當查理創作遭遇瓶頸,焦頭爛額的他不得不尋找突破,他卻有了大膽的想法:有如戲劇方法論的重塑,便悄悄地潛入作者的生活裡。然而,正當查理碰上如此窘迫時,那對於書中之外的真實世界,故事與他所見識的畫面,卻變得衝突而顛倒。至此,查理原先抱持的信念都變得不切實際,也使得他終於能夠將這牽制一生創作的束縛遠遠的拋開,直到最後,無論是看破世俗的虛假,或是電影故事的荒誕,比起生活遭遇的現實慘劇,對比這場人生再平凡不過的荒謬,歪斜的寫作經驗都變得不再令人感到耗弱,也在此時之間,查理終於完成了他筆下的蘭花賊故事,正當他見識社會的虛假時,那富有智性的內涵都隨著故事一同昇華,成為作品之外更具有靈魂的實力作家。
回到故事所要表達的內容:意圖與反意圖論述的支持者,電影前半段發生在查理創作產生的過程,看似是反意圖行為的展現,實據卻是將劇情導向唐突的謬誤之中,而此,正是他們的邂逅,將其抱持在作品與應證自身價值的認知上,將屬於在蘇珊身上的內容,從查理的創作概念中脫離開來;至此,對於查理奇妙的創作歷險過程,儘管查理有些遲疑,但也因為有了唐納的堅持,才有了那次和蘇珊進行的創作訪談,如此一來,查理心中質疑的念想皆全然地釋放了。而另一種動機即是抱持意圖主義的考證,所在對於作者的創作物,提出較為主觀意識的見解,所幸在電影之後經歷一場驚奇的歷險,查理始終沒有將這一段故事寫在劇本之中,甚者是說,我們僅能從他和交往對象的告白,獲得一次對話的安排。不得不說讓筆者感到錯愕的是,這對雙胞胎之間的差異,由唐納所發表的劇本:一再讓查理感到反斥、噁心的粗乏濫造,卻受市場普遍喜歡的模樣,既諷刺又悲催的,同情查理這樣才華獨到的編劇;而還有唐納建議他去參加編劇佈道的課程,何嘗是一位抱有報復憧憬的作者能夠接受的結果,就算在編劇大師傳授給他的想法之間,也很難去接受這段故事與電影結尾所安排的情節呼應,而查理選擇遞交的故事結局,當所有圍繞在編劇改寫工作時發生的誤會,即使感到有些突兀,也免不了讓查理耗費苦心帶來了作品的突破。
要瞭解《蘭花賊》闡述的故事,過於拘謹的態度,顯然是不夠的。其故事採用非單一的線性架構,呈現的不再只是蘭花賊的主體,透過觀賞的角度,隨著鏡頭描繪的輪廓,同時也將兄弟關係的交流過程都完整的表現了出來,除了頹老編劇的框架外,受到啟發的兄弟唐納,在事件主人翁的對象物間,也成了故事之中最為強烈、衝突的人物存在。而為了如實呈現原著中的特殊情境,正當查理試著回溯、重返書中的世界時,這穿插在書中的過往、查理創作的當下,還有發生在人物接觸之後,所產生一系列戲劇化的故事變動,卻都將他帶到了自己的重生路:也就是身為中年作者的他,在逐漸沒有創作動能的狀態裡,找到全新的出口、不再頹靡。以至於作品的前半段:看似在敘述查理改編蘭花賊故事的編撰工作,而其由蘇珊的創造物:代表作品本身去給予讀者閱讀經驗的認知,也因而讓查理深陷其中的窘境;但是,蘭花賊電影實際闡述的概念,卻出奇的從「作家改編」的故事核心,一路轉為「作家工作沈思時的心理活動」。而蘭花賊之於Adaptation的片名詮釋,相較電影原意的「改編」,中文片名的轉譯卻多了幾分曖昧的意象,如是蘭花賊中的角色,因為他們的優雅、內斂,還有奔放的性情,都將電影知性的內涵捕捉到了。
乃至於作品意志的感官層面,查理自劇本轉譯工作之前所設限的自我,涵蓋在查理個人的厭惡情節、主流文界的糜爛,力圖創新的意圖都從查理保守的態度,被自己限縮了。不過對於大眾而言,一個完整、獨具主觀意識,又不讓人感到生澀的代表作品中,無論文學或電影,都已成了人們憧憬與想像的實現物,儘管故事有太多無法超越自身層面的門檻,使得他在追尋個人層面的完美架構之下,不斷給定內心的束縛,甚至是選擇放棄、只得讓作品以失敗告終;但是在蘇珊與唐納的接觸之後,這樣創作過程的獨立運作機制,直到最後,終於都被擱置在一旁。
蘭花賊看似講述著電影編撰的故事,實則卻是對作家本人的工作側寫,無論是在獨自沈思、呢喃或內心獨白,生活中的精神狀態都會持續影響起創作的思考活動,猶如查理難以抗拒唐納對他的影響,這種與身俱來、不斷連結的比較心態,也將他內心深處渴望反抗的力量都被激發出來。所以當查理受困在自身的駑鈍時,唐納那有著滔滔不絕的靈感,卻令他感到憤慨不已;就算是唐納完成了生涯第一部作品,對比他在事業中的成功,這僅有成名代表作的成就也不遠比他工作時力還要具有意義,於是,在思緒迴路的催化下,呈現在兄弟兩人截然不同的創作過程,恰巧因為查理碰上創度難關,卻又不得向唐納尋求可能的見解,也使他在後續的橋段中,唐突且諷刺的成為了唐納的假冒者,甚至也不過只是為了接觸作者蘇珊的對談。
可以說電影對於蘭花賊最有玩味的部分,正是故事反覆穿插著兄弟的互動情節,無論是劇情猶如《敵對》中的角色性格對比,抑或是兄弟互相調換身份進行冒充的橋段,都為這劇中劇的平庸起了點綴的妙用,而此,蘭花賊獨見之處還得回到劇情的穿插設計,將原先改寫故事的工作階段,不斷地和兩兄弟的相互關係牽連運作著。同時,當查理灌注一生信念的創作信念,都被強行鞭撻時,查理看清作者的真實面目,也成為了他創作的全新突破。直到最後,作品以然不只是蘭花賊為主的故事構成,因為唐納、查理的添入,更重新定調了整個劇情的發展概念,於是,當人們都參與了這場劇本編寫工作時,以蘭花賊為題的改編作品,卻也變成了查理個人的半自傳體敘事電影,在故事之間不斷的發散著。
為什麼會看到廣告
40會員
92內容數
生活的哭悲與無常,就用一杯酒水惜別你的的放蕩時光,今天的你還好嗎?本專題是由所製作的【哭悲無常】專題,以廣播及短文集形式,重新詮釋電影中的文化符碼;包括文化與公共的討論範疇,藉由影像語言的解構,提出我們對當代文化的觀點。
留言0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