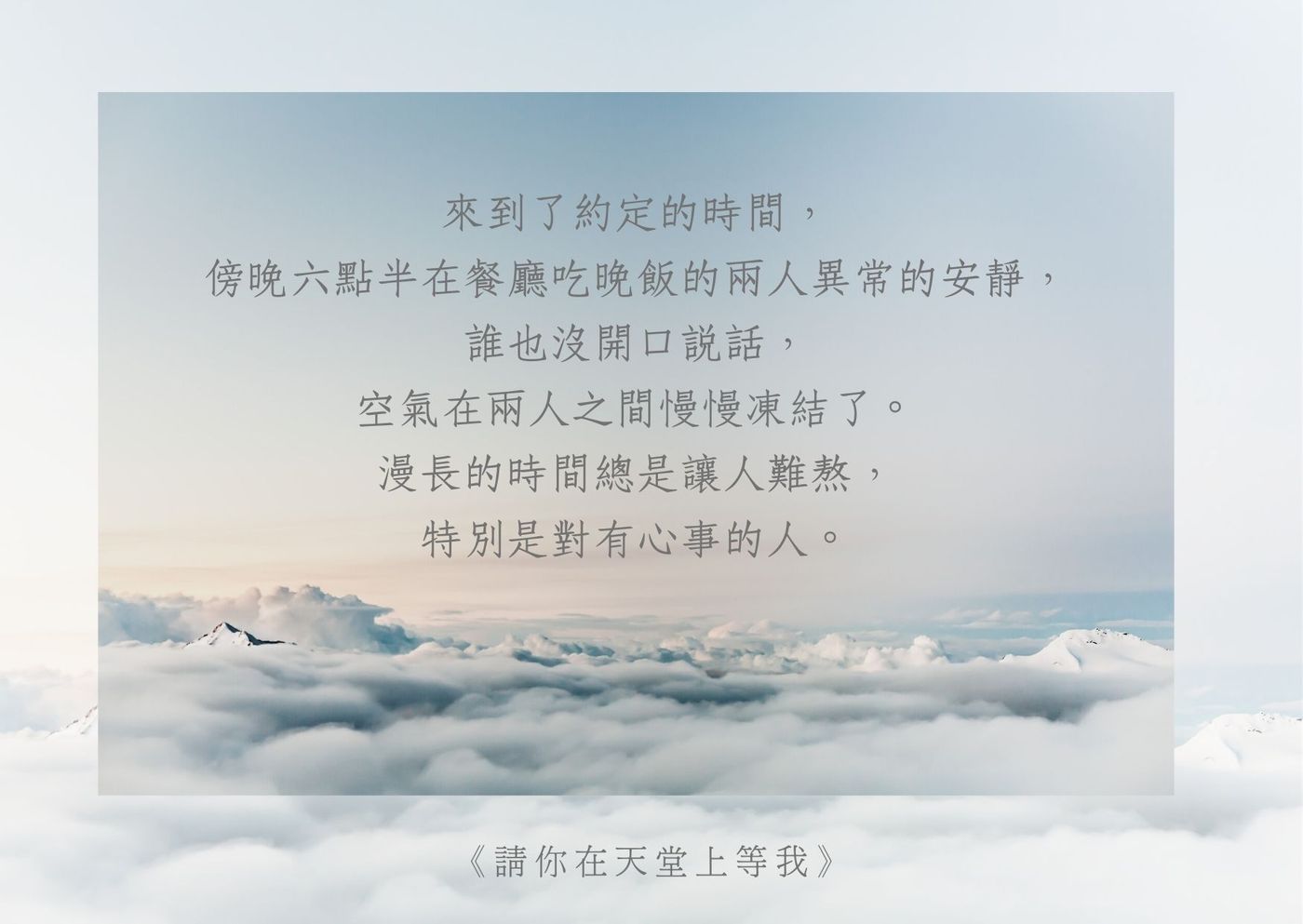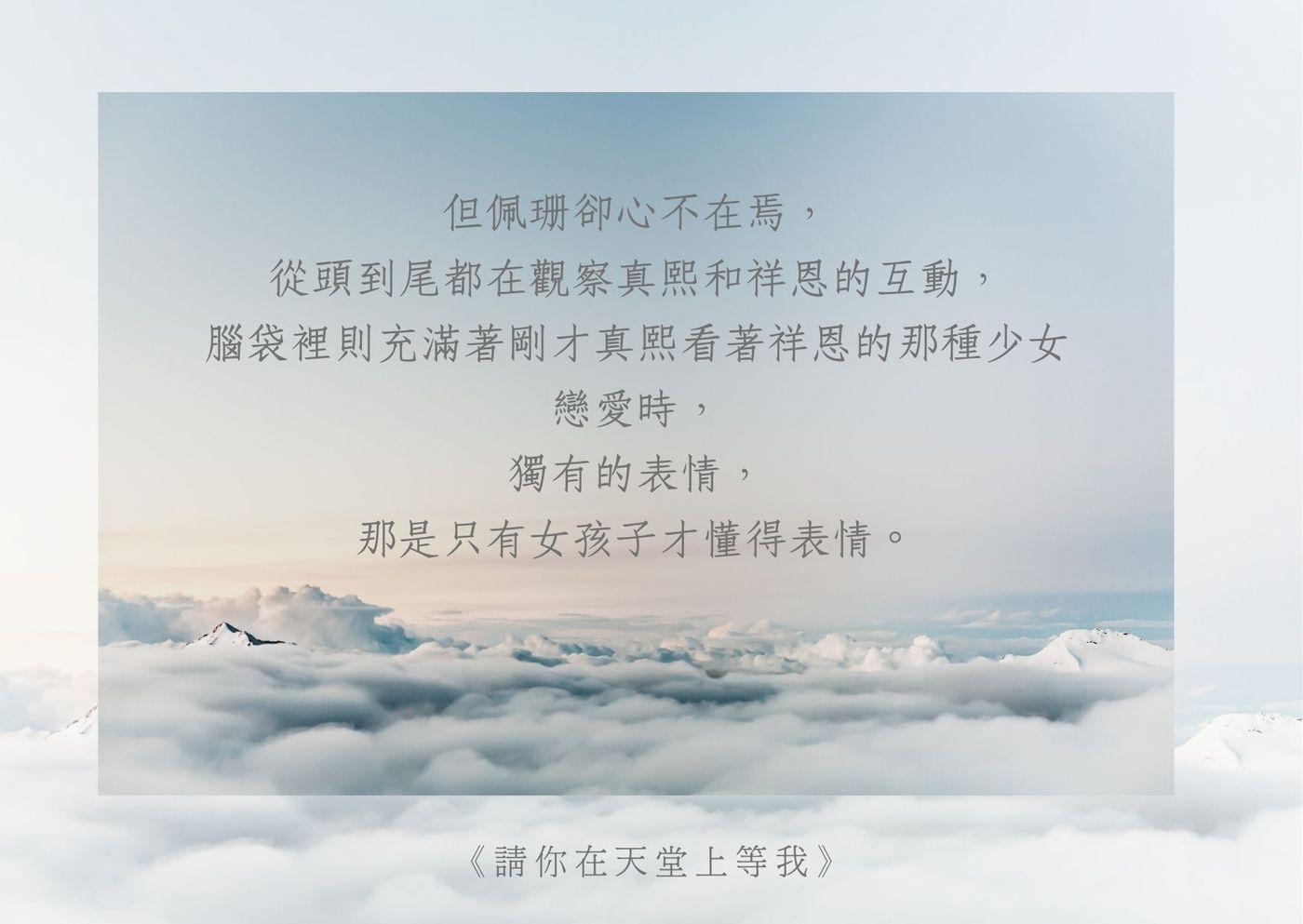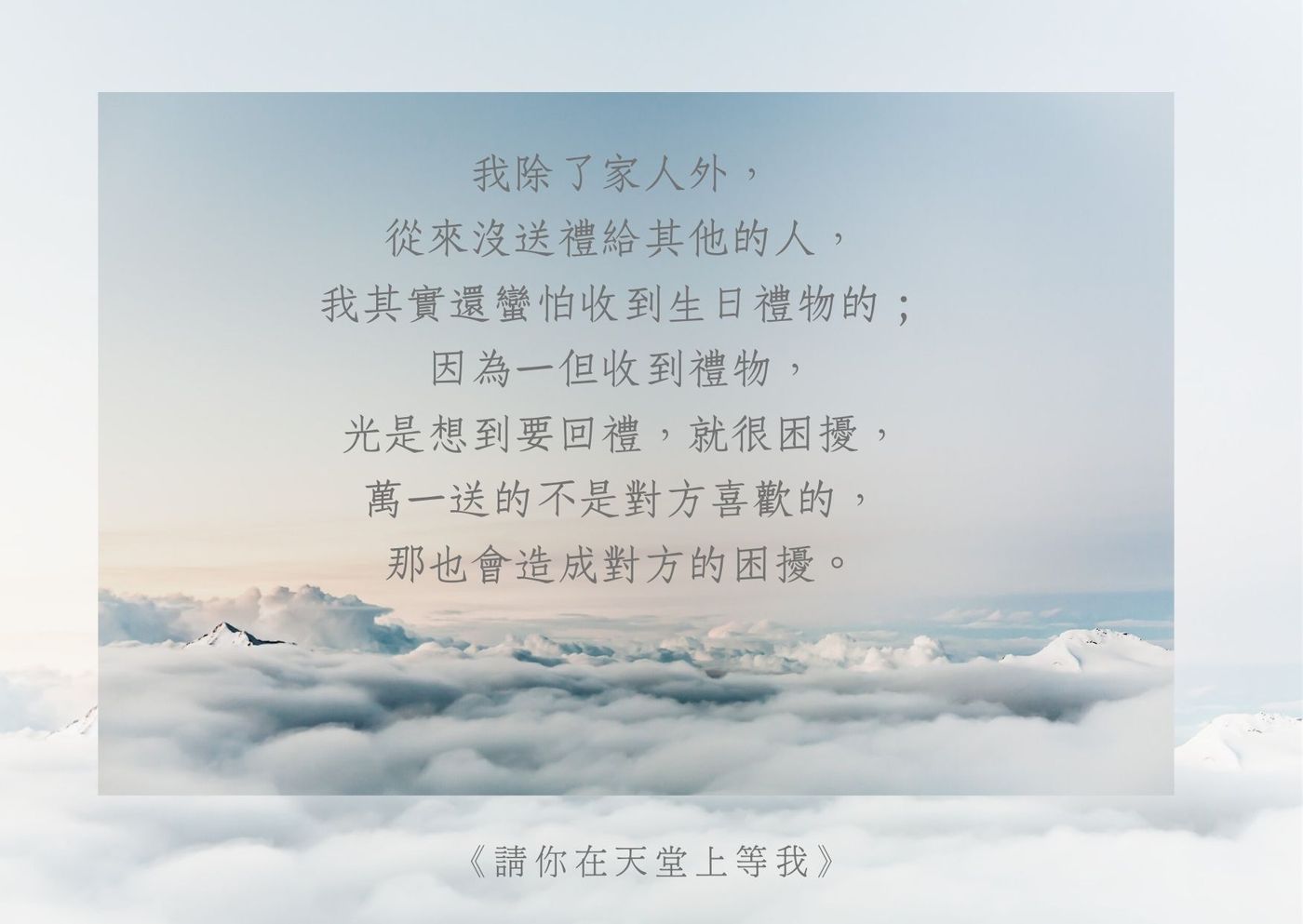【短篇】Candy篇:在鷹一般的沙丘上(上)
黃昏時分,半月形的沙丘刮起詭譎的風沙——那時,Candy拉住男人寬鬆純麻製米色罩衫的一角,心底暗自企盼他不要對她博愛。念頭剛起,那混進沙洲的小麥於飛揚的沙粒後匯聚成人:充滿生氣的墨綠色被本該無情的風兒梳順,顯眼的麥色鷹勾鼻,在彷彿藍星Aton神的照拂下,泛出似弦月將逝時那線狀珍稀的、時而銳利時而婉約的強光——光的細線正放肆觸摸男人的喉結,那是一條精緻蜿蜒又發出光芒的曲線,而後,這條線活了起來——
「妳看起來快哭了。Katie,別對我客氣。有所求才能『存在』。不覺得很美好嗎?妳的存在,在這一刻,被我、被妳自己,牢牢抓住了。看,就在妳的手中,妳抓住我了。」
怔怔地見男人朝自己揪著的衣袖處頷首,一股羞窘的熱氣竄上心尖,螫破女人已然脆弱的心,心臟裡的膿血被生生擠出,她不堪面對、朝他大吼——「你知道我不想存在的!知道我無法去求去奪!我明明那麼安靜!安靜地受傷再安靜地痊癒……為什麼還要質問我、劃傷我?」痛哭失聲。
男人靜靜地聽,眼睛悄悄瞇起來,微微蹙起的眉頭說明他的心情很差,甚至是惱火。
「我真的不懂他在想什麼。」敏銳察覺到她身上可能發生過什麼事,這讓他心底像被火烤過——打心底恨著這素未謀面卻將女人催長染著的生命!
霎時,一陣沁涼的風路過他的頭、男人像被風兒拍撫的小動物;頭上的觸感提醒他該冷靜下來,該在旁人未察覺時盡力消散自己的慍怒;在這取回自己力量的世界裡,男性神、男人,他可從來不用紆尊降貴於誰,著實使他忘記該控制情緒,避免陰鷙之氣流竄天地、生靈塗炭。
「言山,你的表情好可怕……」女人這才注意到自己一股腦兒說個不停,怯怯地瞧他,只見他露出一貫的笑:「說罷,Katie,我想知道妳的事。雖然我現在這具身體不能動怒,但要知道這世間還有人幫妳生妳該生的氣。」真名Katie的女人腹誹:『安撫我也不忘傳道,真是個瘋子!』真心的笑卻藏不住對眼前人的欣賞。
但她不知道的是,言山也在腹誹——『我可不想再進聖地的地洞裡囚身,那裡的無聊會逼瘋我!』基於神靈身分的限制,男人沒能將異世界的知識帶給藍星的人。
「好、好喔?那時我在想,可能我曾經懂過他,但在知道他是如何裝作無害地靠近,只為了無聊的虛名時;在知道他從沒懂過,我已如實交代的本我時。情意已然虛擲,我很想嘲笑自己、竟把真情獻給了海妖而不是一個真正的良善者。最可憎的是對方還以為自己是信教的聖人,你他媽這種淫亂的Bitch才是真正的大聖人,他是個什麼東西,也配稱自己神聖?連我這種蚍蜉所見世間之真理都未曾得見者,還敢妄圖稱聖。可笑荒謬到耶穌都能再死一次。」
男人瞠目結舌、「你他媽這種淫亂的Bitch是在說我嗎?這算是稱讚?」荒謬到他笑出聲來。Candy不悅:「你認真聽啦!」、「好嘛。不打斷妳。」他逕自伸手玩起飛揚的沙,沙粒正有意識地圍繞指間移動……「言山。我真的很自責,明明有那麼多思想純正的人在人生路上等我,我卻辜負他們,雖然本來也不用應允他們。可我很難過,時間不對,正確的人也會變得不正確。結果來說,他們都成為不正確的人,只因為這個人的存在染著了我、抹去了我的良善與隨興,我怕你也這樣,失去心靈的自由。我知道不該做回憶的奴僕,可夢魘如影隨形,深怕下一個遇到的人,如何眼神雪亮璀璨、認可我的價值觀,卻又是個不誠實的人。」
「唉。確實。」『聽這種事就想來杯咖啡。』男人沒膽說。以前還是人類時被她打怕了,就怕到了異世界這女人還拿他試身手。
「你的表情太明顯了。你的咖啡癮還沒好嗎?『這世界』沒有咖啡嗎?哈哈。」
「沒有,這世界味道像咖啡的植物果汁喝了會醉……」、「你真的不是偷喝了死藤水……」、「噓。不要告訴言山。」他刻意靠著女人耳畔用性感的低沉嗓音低語,女人卻笑道岔氣:「你幹嘛啦、哈哈哈!醉到精分喔?欠打——」彼此追打、笑成一團,像好久沒這麼開心了;玩累的兩人不約而同彎腰拄著自己的膝蓋,許久方能緩氣。
待兩人站直後,言山讓女人安然地倚靠自己——僅僅是男人的左肩與女人的右肩相觸,高於己的體溫還是延燒——Candy想求更多又怕著貪愛,剎那消逝的癡迷之色令他大笑——「Katie,妳變了。是這種蟲都不如的狡猾騙徒將妳變得膽小嗎?妳們是信眾,我是施用奇蹟的耶穌,看著我,剛剛說過了,不用對我客氣。」
被超脫俗世的神靈允許許願的女人愣住,不可置信地看他,看進他黑曜石般深邃的眼中、自己清晰的倒影上:慟哭失魂落魄的女人、被狂風吹亂狼狽且不流於華人社會推崇的形貌,以及沾上沙粒、經那烈日烘烤得來眼下的黃金瀑布——理智被拉到不久前的某個事件、來到曾經久居的世界、真正的藍星上,一個畫面隱約浮現……
「那時早就決定好了,要像黑貓少年那時一樣,好好收拾自己已給出的,一個瞬間就不再鍾情於他。」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