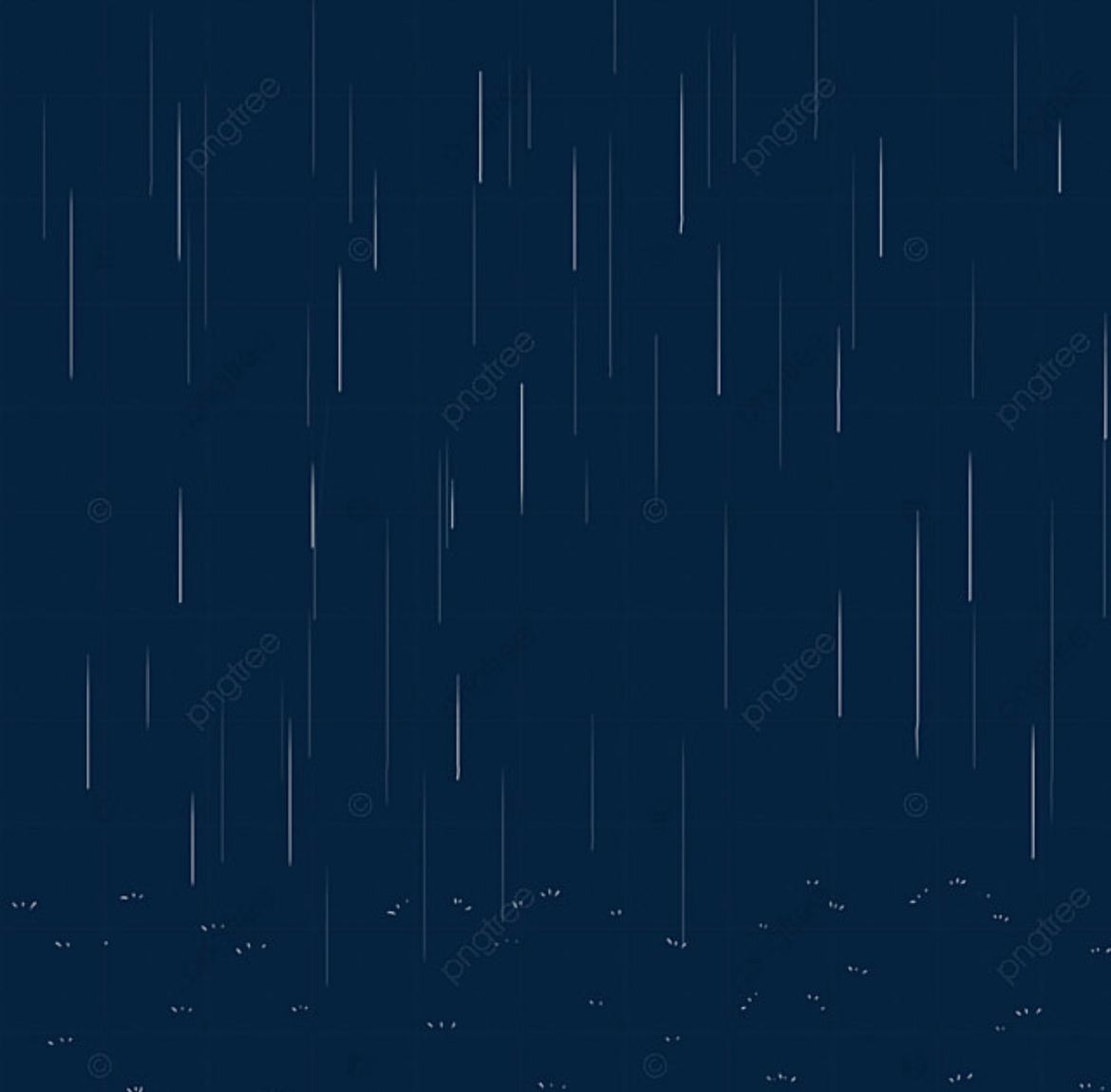如果先見到未亮的燈泡,再看見聖誕節的裝飾燈亮起;如果先見到燃燒完的木柴,再從記憶裡找尋熊熊烈火--那麼光亮就成為讓人疑惑的存在,帶有希望的抽象性與寓意被抹除了,一排LED燈不亮時是沒有意義的,路旁的孩子經過說了一句:「怎麼不會亮呢?」;燃燒完的灰燼是發光的犧牲品
誰在發光,誰在暗處才被看見?
S將捏扁的鋁罐握在手中,他朋友笑他走路像個古人,總把手背在後頭。他的嘴巴充滿酒與香菸的氣味,他的身體很慢很慢,正適合這個姿態。他經過公園,看見一個個大袋子和椅子上不知是否熟睡的人;他經過郵局,看見紙板上也躺著一個人,臉被打開來的雨傘遮住了;他走下地下道,也有一個人蜷在棉被裡,同樣看不見臉;他從地下道走上來,十層樓高的大樓前還有一個,像睡在巨人的腳下,拖鞋整齊的放在紙板邊,看上去像個女人;而銀行台階上那一個,他倒是注意好幾次,這個人是固定班底,他在旁邊的ATM領了錢,同時打量那人的居所,比一張S自己的床還小。白天一到,他們就消失了,地下道、車站、公園、郵局、銀行、大樓前的他們,不知去了哪片叢林狩獵,晚上才回到河谷邊休息。
公車站旁邊的垃圾桶爆滿,八個披薩盒疊在旁邊,上面還放了一雙爛布鞋,一張建案廣告單從被塑膠袋塞滿的垃圾桶裡透出來:「要住就住最好的」。全家亮著燈,有人捧著關東煮出來,好幾台計程車排隊等綠燈。在這個城市裡很少看到流浪狗,不知怎地,S卻在公園發現了,有個人在夜晚叫囂,狗不知從哪刁來裝著便當盒的塑膠袋,舌頭激動地往橡皮筋綁著的紙盒裡舔,旁邊散落一些衛生紙團和油紙袋。公園對面是一棟鋼筋外露、正在興建的新大樓,(S心想:這是「最好的」嗎?),大樓前的鐵皮牆空間夠大,正好被某一政黨的宣傳布條貼滿貼好」,他坐著,正好面對這斗大的「2020政黨票投OOOOO」。心情已經不怎麼好了,看到這個,心情更差,不知道是候選人還是黨主席的半身被印在上頭,起碼也來個美女吧,他心想。他想轉身問另一張椅子上熟睡的男子,「你幾天後會不會回家投票(他的籍貫、他的家在哪裡?)」,另一名叫囂的男子走了,除了幾台車過去,公園的夜晚基本上是安安靜靜的。
「我們創造了一個社會但裡面的人都不快樂。」S想起幾天前聽到的這句話,來自少數的先驅。
「主流生活崇尚秩序、標準、節奏。」為了生活的進步與水準,總要有人收拾殘局、收拾垃圾、收拾寶特瓶、收拾骯髒、收拾白天的物欲和夜晚的狂歡。那些跟不上節奏的就被甩出去了,甩出去到社會的邊緣,被剔除在九大行星以外,孤獨、沒有名字,在宇宙裡自轉,等待自爆、衰竭的那一天。
他,S他,真的,再也不想聽到「社會就是一個機器,人類就是螺絲釘」的比喻了。沒有機器,沒有螺絲釘,幹他媽,人類就只是「人類」,為什麼要當螺絲釘?好端端的人,每個好端端的人,到底哪裡像螺絲釘?這是什麼愚蠢的比喻,為了說明每個人都是平等、微小嗎?那在還沒有機器以前,社會是什麼是?螺絲釘的目的是為了讓機器能正常發揮,而這就是「我」的目的嗎?憑什麼呀?要為著一個名為「進步」、「安穩」還是「經濟」什麼的共同目標奮鬥,沒有功能,沒有目的,什麼都沒有,「什麼都不要。」他拒絕張開手,於是那些東西都落在地上,像是無臉男要給小千金子,但她不要。
到底再想什麼呀。「我到底在想什麼呀?」他抱著頭,閉上眼,試圖將注意力轉移至嘴裡殘留的酸澀裡,可是他腦裡都是這個城市的畫面,像是千百支監視器,深入到城市的每個孔洞裡,每個垃圾桶、每個水溝蓋、每個閃黃燈的路口、每個牆上不明的塗鴉、每個菸蒂、每個玻璃碎片、每個裝滿回收物的推車、每個紙板上蜷曲的身體、每個在自己房間裡熟睡的人、每個在路邊流著淚講手機的、每個便利商店的店員、每個哼著歌騎著ubike過去的、每個拿鑰匙開門的,鎖打開的瞬間,「喀擦」一聲。
他將媽媽的手掌心貼在臉上,那麼近的去以嗅覺記憶一個人,那是他的兒時,他想起他那辛苦一生的爸爸媽媽。有些聲音靠近,一個穿著短褲的男子,拉著他的拉車經過,看了S一眼,像在找什麼,他的腳步沒有停,就這麼跟著他的拉車走了。
凌晨三點零六分,開始出現水滴打在窗台上的聲音,S盯著公園的監視器,很久很久,幾乎是凝視,他的手還握著鋁罐,後頭傳來打呼聲;狗不見了,便當盒打開來,空空的在那裏。他想起明天下午還有個人要見,他知道明天下午還有個人要見,他告訴自己明天下午還有個人要見,他的腦裡現在只剩下一個聲音︰「明天下午還有個人要見」——無論這個人重不重要。於是他結束凝視,意識到鋁罐始終都在手中,起身,走遠遠的路回台北的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