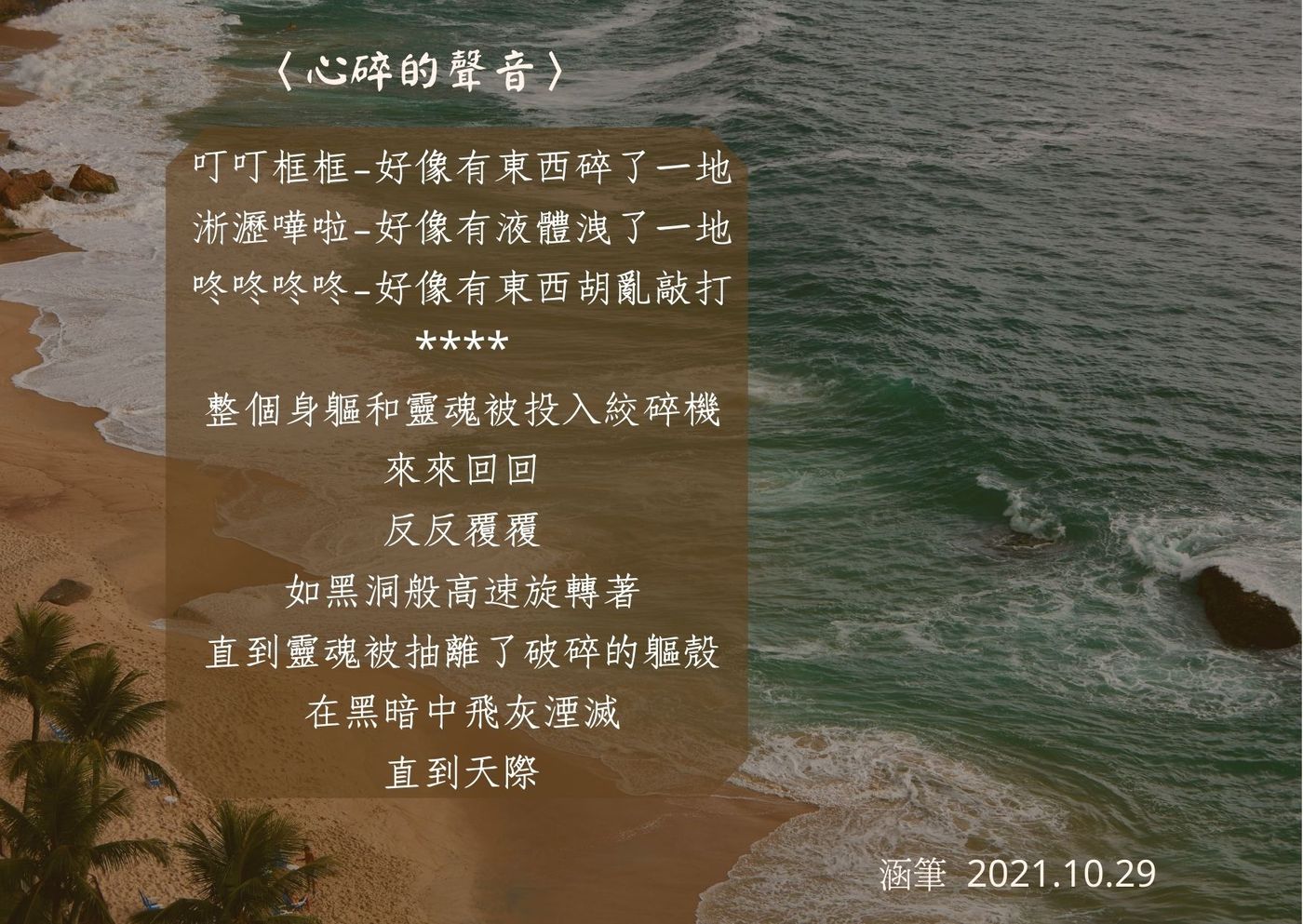01
有時候戀愛是荒唐的。我們怎麼能夠放心地把全部的自己,交給一個也許根本對你一無所知的人?你總是對自己“小心輕放”,又怎麼有勇氣,輕易撕下曾經牢牢貼在身上的那張"易碎品"?有時候我覺得,荒唐的不是戀情本身,而是身陷於戀情之中,那荒唐的自己。
小時候曾經在補習班收過一次情書,他說我的眼睛像玻璃彈珠那般美麗。當時我戴著厚重的近視眼鏡,我就這樣相信他了。他約我一起去看管絃樂社團表演,為了讓自己當天有一頭自然的捲髮,前一晚睡覺前先綁了辮子,笨拙地挑選了我認為最漂亮的裙子,衝到正在玩電腦遊戲的哥哥面前問他好不好看。
「我穿這樣好看嗎?」
「不是都差不多。」
「我是說,會不會很奇怪。」
「妳有哪一天不奇怪嗎?」
「滾!」
「這是我房間。」
總之,我滿意地照照鏡子小碎步出門了。表演看到一半,我覺得好無聊,全天下的無聊都讓這場表演包辦了。顧不得台上的人和那個約我出去的男生,噢,我甚至記不得他的名字,我抓著包包說要去廁所,頭也不回的走了。我用我的GD88手機傳簡訊,告訴他家裡有事要先離開,後來再也沒跟他出去過。在那個手機剛開始普及的年代,這已經是比不告而別更好的選擇。我覺得我喜歡的是自己玻璃彈珠那般的眼睛,雖然我戴著厚重的近視眼鏡。
02
時光匆匆地過了幾年,我談了一場算不上是愛情的戀愛,對我來說,那是不像樣的,但我就這樣得過且過,走了一段時間。人生中總有一些時刻會覺得自己什麼都能做到,有一陣子我對自己充滿自信,即使我從來沒有完整彈完那本討人厭的徹爾尼,即使我在沒告知母親的情況下自行開除了我的鋼琴老師。我覺得自己能夠成為一名作曲家,我常常在洗澡的時候有很多靈感。後來才發現,原來那只是每個正在洗澡的人都會做的事。
身為擁有註冊日6000多天的資深宅女,我開始在PTT上搜尋一些資訊,加入了其中一個創作的FB社團。那裡的規則是先寫詞再譜曲,有一個負責分派工作的精神領袖,他會決定每個人的角色,寫詞、作曲、編曲、配唱,接著會在網路上發行數位專輯。那是一段不長不短的時光,曖昧的時間不夠短,戀愛的時間不夠長。我沉浸在這段不長不短的時光,寫了幾首歌,唱了幾段,談了一場不長不短的戀愛,分一段很長的手。
03
一開始我就被他吸引。他的FB頭像是《LINKIN PARK》主唱,正在聲嘶力竭。我覺得他也是那樣的人,和Chester一樣用力活著,我希望我也能用力活著。我們漸漸有了交流,我們不聊音樂,我不願讓他發現我只是個愛聽芭樂歌的無知女孩。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每天都會聊天,上班說早安,睡覺說晚安,沒有他的早安,一天好像不會開始。他告訴我他比較喜歡用GOOGLE+,那個曾經想要挑戰FB的社群軟體,大部分的人聽都沒聽過。他開始會發一些奇怪的動態,戀愛中的人通常都會變成詩人,尤其是開始與結束。很快的,我就知道他是屬於哪個階段。很好猜,不知道答案的時候,選以上皆是準沒錯。我想我大概知道他用GOOGLE+的原因,絕對不是因為它特別。我們小心翼翼地聊著,早安和晚安之間多了一點不自在的禮貌,深怕超過了那條看不見的線。
有一天他告訴我,他要到我的城市出差,我們見面了。他不像Chester那樣,但有他著低沉的嗓音。你知道的,好聽的聲音總是讓人難以抗拒。我踩在線上,不知如何是好。我們一起看了場不知道內容的電影,快結尾時,我們就像老派電影裡戀愛的人一樣,牽手。這次我們一起踩在線上了,我好奇我們會不會就這樣觸電身亡。人生總是不會給你時間充分思考,該牽手的時候就是要牽。我在車站與他告別。我哼起《THE DOORS》的〈LIGHT MY FIRE〉,Come on baby light my fire. Try to set the night on fire…。
04
我告訴自己,大家都是成年人了,牽個手而已,又不代表他要牽起你這輩子,而且一輩子也太超過了。我持續著每天說早安的日子,那是除了咖啡外,最撫慰人心的日常。有一天,他跟我說他搬離了他們的租屋處,自己租了一間房。我知道那是對我的邀請。
在那之後我們一起走了半年,每個週末我們在車站見面,在車站告別。離開時我偶爾會在心裡唱著《張秀卿》的〈車站〉。漸漸地,我發現他對告別不再感傷,漸漸地,我開始寫不出社團精神領袖指派的曲,我像是搭了火車後找不到應該在包包裡的那張車票,卻遇上列車長來驗票的人,又慌張又無奈。我一邊搭火車,一邊準備不知何時會來的,真正的告別。
「我想回去那間房子。」他送我到火車站時告訴我。
從那時候開始,我知道真正的離別是沒有聲音的,就算我以為我已經做好準備。

05
我終究離開了那個不屬於我的城市,回到了我應該待的地方。戀愛中的人通常都會變成詩人,尤其是開始與結束,於是我也成了詩人,寫著沒人有興趣的詩。我完整的經歷了悲傷的五個階段,並且橫跨了四個季節。有好幾次,我忍不住到了他的城市,只想求他再愛我一次。再後來,我以為我是全世界最悲情的女主角,每隔兩週就寄信給他。周圍的人開始看不下去。
「你應該要勇敢一點。」
「你先做點勇敢的事再來跟我說勇敢。」
「你就放下吧,都快一年了。你也不過就談了半年的戀愛。」
「閉嘴。」
後來我哭倒在哥哥的懷裡,勇敢刪除他的電話和FB,過時的人才用FB。我在房間裡唱了一次又一次《A-LIN》的〈荒唐〉,結束這場“曖昧的時間不夠短,戀愛的時間不夠長,分手卻用了一輩子”的短命戀情。那不過就是一場破戀愛和一個不負責任的破男人。 他害我差點連Chester都要一起恨。
「收拾你的荒唐,然後離去。」我唱著。
我總是對自己“小心輕放”,在我鼓起勇氣撕下那張貼在身上,邊角若即若離的“易碎品”時,我發現我仍然是那個,愛著自己玻璃彈珠那般的眼睛的女孩。原來,有時候荒唐的並不是戀情本身,而是那個愛上悲傷不願起身的,荒唐的自己。
唱完荒唐,手機裡傳出《五月天》的〈生命有一種絕對〉。我還是那個想要用力活著的人,什麼都沒有改變,但是好像有什麼已經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