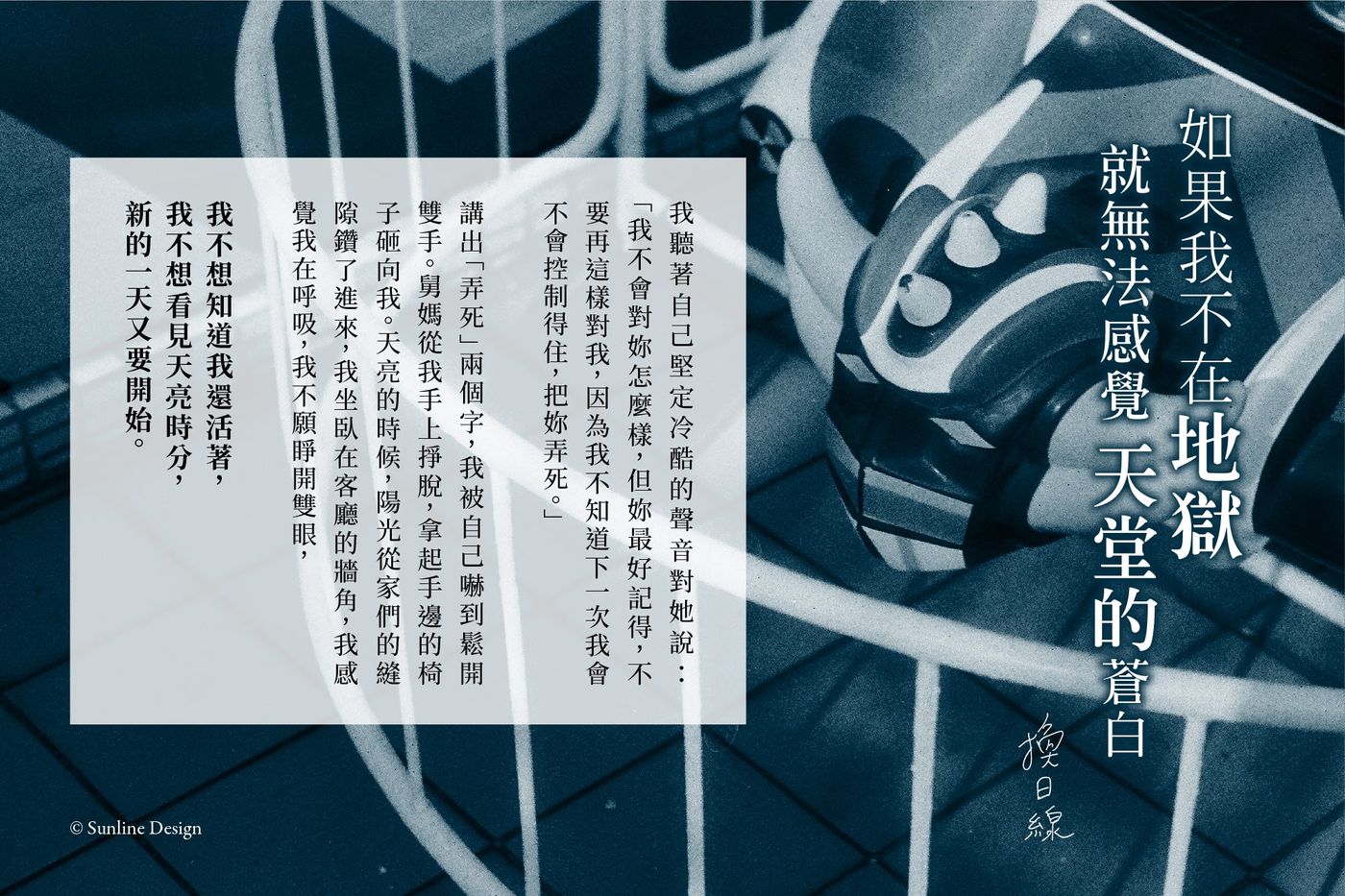J與K的婚禮舉行的那一天,我在現場。在那個平原草地搭配著東海岸的海景、陽光,將婚宴會場布置得像是電影場景一般。我不認識J與K,只是恰好透過嚴海的介紹,接了一筆婚禮小物的生意。是K委託我的手製胸章,從設計胸章圖樣到親手一個一個壓製而成的,K說要送給所有到場的人,希望每一個人如同胸章的字樣「一起幸福!」
那是同婚法剛通過的幾個月後接到的手工案子。我邊製作胸章,邊想著「這一天真的到來了」,而且真的有像J與K這樣的伴侶二話不說的就辦起了同志婚禮,張揚著自己的戀情,等著其他人的祝福,也像是替那些還躲在櫃裡終日不見陽光的戀人們打開了櫃上的那扇門,宣示且鼓舞著:來吧!一起幸福吧!我們結婚了。
跟樂樂分手已經四、五年。還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從來沒有想過「結婚」這個詞,像是約定好似的,兩個人從來沒有提起過這件事,甚至沒有想過如果有那麼一天同志婚姻合法化,我們是不是會選擇在各自的配偶欄裡填上對方的名字,只是非常認命地過著跟「好朋友」的同居生活。我特地向另一個剛結婚的客人要來一只她訂下高級喜餅的木盒,裝進一兩百個「一起幸福」的胸章,是我對J與K的小禮物做的精心包裝,想把另一對新人的喜悅也傳遞給她們。交貨的隔天,我特地去K的Facebook頁面看看她有沒有對這些胸章寫下什麼評價,映入眼中的全都是她與J準備婚宴的細節,包括那個東海岸的美景,以及每一則貼文都tag了J。
我突然很想要知道像這樣的同志婚禮,會是什麼樣子?會不會比起一般異性戀的婚禮有趣?去的都是什麼樣的人?她們各自的親人、父母會以什麼樣的姿態到場?會不會有什麼出忽意料或過於戲劇化的演進?我萬分想知道,如果有那麼一天我也要跟我的伴侶結婚,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我在K的Facebook傳了一則訊息:「K,不好意思,想提出一個有點唐突的請求。我想去參加妳們的婚禮,不知道方不方便?」K已讀後立刻回覆:「好啊!歡迎歡迎。」戶外的婚禮沒有人數的限制,我便在那個冬日陽光普照的平地草原上參與了人生中第一場同志婚禮。
*
跟樂樂分手那天,我們坐在拉麵店吃著不怎麼熱的拉麵。
那幾天襲來一波寒流,台北的冷總是從外衣一層一層的透著濕氣冷到骨子裡,夜裡若是不開暖氣,就算與樂樂相擁都還是很容易感覺著自己四肢還微微的冰冷著,若是再配著那綿密的細雨出門,很難知道溫暖是什麼,即使剛端上桌的拉麵都會在短時間中從冒著白煙變成不燙口的溫熱,再沒幾分鐘就會冷去!
我想戀愛也像冬日裡的拉麵一樣,若是店裡沒有一定的溫暖,別說要讓人在室內吃一碗暖身的拉麵,就連麵本身都會因為沒有適當的室溫而容易降溫,最後變成失了溫度再也沒有人要品嚐的食物。
我和樂樂怎麼走到分手的?我想可能我們當時都想不出任何原因,大概就是那幾句:「沒有感覺了。」「不愛了。」「沒有辦法跟妳一起過日子了。」然後什麼也沒多說就各自從對方的生命裡慢慢退場。
我和樂樂在一個手作坊相識,我應邀去當手作坊的講師,樂樂是與我接洽的工作人員,負責幫我準備手作課中需要的所有用品,以及主持課程進行的流程。手作坊的課程進行了一兩個月,每一次兩個小時,第一次上課之後,樂樂都會在上課前一天傳訊息告訴我:「老師,明天有準備妳的便當,妳要提前來吃飯喔!」我沒多想,課程有準備便當是常有的事,只是好不好吃跟能不能入口而已。
樂樂準備的便當,都是裝在保溫盒剛做好的飯菜,每一次我都誇讚她:「妳好環保喔,都知道要拿盒子去買飯。」樂樂總是微笑且溫柔的說:「這有保溫的功能才不會冷掉啊!」然後她會邊看我埋首吃著便當盒的飯,邊跟我確認當天的流程,再在教室裡進進出出的,等到我開始上課,她會將我剛才吃飯的桌子再整齊的清理過一次,將那個保溫盒清洗乾淨,隔週上課之前,再用它裝來我的便當。
「快吃吧!再不吃冷了。」我等著樂樂的麵端上桌後,遞了筷子對樂樂說。
我們沒有像平日裡互相交換彼此的拉麵和對方的口水,也沒有再多交談,慢慢吃著自己碗中的麵。就在我端起碗想把湯一口喝盡時,樂樂開口了:「妳知道妳上課時的那些便當是我親手做的嗎?」
我的動作在端起碗的同時停下了,「知道啊!」我說。我沒有看樂樂的表情,繼續把碗裡最後殘留的幾條拉麵再夾入嘴中。
我的確是在後來跟樂樂一起住了好一陣子之後,才發現那時課堂前的便當是樂樂親手做的。但我們從來沒有提起,她以為我不知道,我以為她不想那麼直接的說出口。
聽到我的回答後,樂樂像被按下了靜止的鈕,停頓了幾秒才抬起頭看著我問:「妳有愛過我嗎?」
我沒看樂樂,將頭轉向拉麵店門口,看著剛走進店裡的一對男女。男孩拉開自己原來擋在女孩頭上的外套,正要脫下時,女孩輕輕地在男孩身上拍了又拍,想要拍下男孩身上的水滴。以前我也像那個男孩一樣用著外套擋住樂樂頭上的細雨,而樂樂也像那個女孩一樣,她會拿出她放在包包裡的小方巾,擦去我身上的雨水。
我將頭轉回看了樂樂一眼說:「有吧!」
我彎下腰拿起放在腳邊置物籃的背包和羽絨衣,起身前我對樂樂說:「我去外面抽個菸,妳慢慢吃,吃完我載妳回家。」
我在拉麵店外可以遮雨的地方從包裡掏出了我的菸盒和打火機,想著她問的那句:「妳有愛過我嗎?」應該也是我想問她的句子。戀愛也像抽菸一樣,得先從燃起的菸吸進會讓人感到愉悅、有些嗆鼻和刺激的氣體,再從鼻口吐出那些汙穢,好像談戀愛只為了最後那句:「有沒有愛過?」不論答案是不是自己想聽的,最後都髒了眼前的空氣。
*
J與K的婚禮來了上百個人。在有著海風的草地上,有些人帶著野餐墊席地而坐,有些人坐在被排列整齊的長桌旁,孩子們圍繞著冰淇淋餐車和棉花糖機器等著大人們替自己挖一球冰、製作一枝棉花糖,他們的家長便在一旁看著孩子閒聊了起來,不論認識或不認識,都在這個如夢似幻的草地上,進行著一場從來沒有想過的儀式,關於同志結婚的儀式。
草地的另一端用花草、樹枝繞出了一個拱門在舞台前方,舞台的兩旁有著一組鼓和幾把吉他,以及數支立著的麥克風和音響及音控台,有幾位穿著西裝和套裝的男女在來來回回的準備著。K在一旁沒有著西裝,只穿著白襯衫和一條深色牛仔褲連領帶都沒打,她在舞台一旁拿著一張紙不斷地時不時看著那張白紙又望向天空,應該是在背頌即將開始的婚禮誓詞。
幫我牽線談妥這筆手作交易的嚴海不知何時從我身後冒了出來,輕拍了我的肩膀,「小虎,妳也來了?妳本來就認識她們?」
我側身看了嚴海一眼說:「本來不認識啊!只是想來看看同志婚禮怎麼辦的?就問了K能不能來。」
「妳怎麼不問我就好,我帶妳來啊!」
「小杜呢?怎麼沒有跟你一起來?你們什麼時候要辦?」
嚴海朝舞台的方向指去,那個穿著藏青色西裝的男人正慢慢走近舞台,拿起其中一把吉他。正「他今天要當伴奏,K說什麼要在台上唱一首歌給J聽,杜就自告奮勇的說要幫她伴奏。」
杜像是心電感應似的從舞台那頭轉身,嚴海邊對他揮了揮手,邊跟我說:「我們應該不會辦吧!可能偷偷去登記就好。你能想像我們兩家父母參加兩個不孝子的婚禮嗎?」
嚴海放下手示意我看向樹下,「妳看那裡,一個是K的媽媽,另兩個是J的父母。」他停頓了幾秒又說:「我沒辦法想像我爸怎麼可能出席這種場合?兒子的新娘是另一個人的兒子。」
「是啊!這真的是很難想像。這種海岸婚禮就算不是在國外,對一般人來說都是夢了,就別說是同志婚禮了。可能在夢裡才會出現吧!」
「如果妳和樂樂還沒分手,應該也到了要結婚的階段了吧!」
我轉頭看著嚴海問:「說真的,你和杜在一起二十多年了,你們有想過這一天真的會實現嗎?」
嚴海搖頭:「沒想過。」
「我和樂樂也沒想過,我甚至不知道她愛不愛我或我愛不愛她。但我確信的是,我每談一段戀愛都想要跟對方在一起一輩子。」
「不知道愛不愛還要在一起一輩子?」
*
我確確實實跟樂樂說過不下百次的「我愛妳」,口頭上、文字裡,床上做愛的呻吟聲中、熱烈又痛苦的高潮裡,爭執時求饒的拉低姿態,或者偶爾牽牽小手親吻時,我都會跟樂樂說:「樂樂,我愛妳。」就連樂樂曾有過跟其他男人或女人過分親近、親密,我都會毫不遲疑的跟樂樂說:「樂樂,我愛妳,我不想失去妳。」
樂樂有時輕聲的在我耳邊說著:「小虎,我也愛妳。但是妳能不能不要這麼焦慮?」然後用她的吻堵住了我的唇,再恣意地進出我的身體,不論我要或者不要。有時樂樂也會在某些需要我安撫的狀態裡要求我說:「小虎,說妳愛我,我想要妳很愛很愛我。」但最常的是,樂樂常常已讀不回我的愛意,在我經常性的焦慮和暴躁對她無盡的宣洩情緒後,再對她說愛或求愛的舉動裡。
我們經常性地以「沒有未來」為前提的爭吵,在同性戀情裡用彼此對未來的絕望切出另一塊幸福與愛的世界,而我們從來不會躺在那個以愛或幸福堆砌出來的城堡裡,任憑彼此看不見未來的絕望拉著對方往更深的黑暗裡落下。
我們時常在愛慾中重新燃起對彼此的渴望,認為只有在性愛裡透過高潮,才可以承接住對方交託在自己手上的愛情,好像只能透過那樣的交合,得以證明一點點我們有過戀愛的軌跡;只有在那樣繃緊全身細胞的行為動作中,那所謂的「愛」才能從口中、從身體、從心裡爆發在高潮的瞬間,再用那一刻的情緒度過每一次墜落時等待著地看見光明前的黑暗!
我們似乎從來沒有好好談論過「什麼是愛」「什麼是對方需要的愛」「什麼是自己渴求的愛」,只憑著自己「對愛的想像」要求對方照單全收,以回應自己心裡所需的渴望;我們甚至經常地責怪對方在哪些生活細節對自己的遺忘,像是兩個只是突然寂寞的靈魂剛好在某個瞬間在錯身的時候吸附了對方,然後再用力地攀爬那個名為「愛」的城牆,卻常常不知道以什麼為支點而踩空了腳,只剩下雙手牢牢纏住對方。
「樂樂,讓我離開妳吧!」
提分手的那天,樂樂剛從日本出差回來,我去機場接她的時候,在回程的車上這麼對她說。樂樂沒有回應地像是睡著般坐在副駕的位置上,我不以為意地繼續說:「如果妳的人生未來沒有把我算在內的話,我們就分手吧!妳應該有妳更好的人生,如果妳選擇的不是我的話!」
樂樂沒有回應我。我伸手想握住樂樂的手,才剛碰上她便瞬間從我的手中縮回她的手。高速公路上的車子一輛一輛從我後側超車往更遠的前方駛去,我沒再多說,加緊地踩向油門,卻不知道我和樂樂的戀情會駛向哪個遠方。
在那之前,我們已經無數次為了樂樂認為我的世界裡總是忽略她,或是她的決定裡甚少有我的存在或是找我商榷未來「一起」的事宜而爭執。每一次吵得不可開交的痛苦痛哭或是無言以對的冷戰,都在一次又一次的性愛裡像是被撫平,即使我們都知道那只是那場爭執暫時的停頓,卻都沒有誰真正開口想面對「未來」這個沒有未來的主題。
樂樂不斷地逃開我問她:「我們這樣繼續下去有什麼意義?」這個問題,而我則繼續窩在自己小角落裡用任何一件可以隔開樂樂的事情,將她阻隔在我的忙碌之外。除了做愛以外,我們幾乎再沒有什麼生活上的交集,就連見面的次數都在我們避開彼此生活步調越來越少。
到家時樂樂沒等我幫她拿行李進家門,自己打開後車廂拿下了行李往家的方向走去。等我停好車走到樂樂身邊時,她對我說:「妳如果想分手就分手吧!等我找好地方就會搬走。」我想上前擁抱她,想企圖再讓自己或她開口說出一句:「我們再試試吧!」她的行李卻橫在我們中間,她沒有往前,而我停在行李前面,誰都沒有再多說什麼。
*
同志婚禮其實跟一般婚禮沒有什麼差別(事實上本來就不應該有什麼差別。)讓人最難想像的那一刻,是雙方父母出現的橋段。我、嚴海和杜都拿著相機想要拍下這場婚禮當作見證,但都在K的父親出場的那一刻激動地哭了起來而糊了雙眼。
據說,K的父親本來不願意出現在這場婚禮。舞台的螢幕從K小時候的照片播放起,K的照片中幾乎都有她的父親,從抱在手中的到長大與父親併肩的,直到家族照片中出現J之後,K的照片慢慢看不見她的父親,她的樣貌也從童年時期穿著小洋裝到慢慢只有牛仔褲、polo衫⋯⋯
當K的父親出現時,全場都安靜了下來,所有的目光都投向本來靜靜出場的K的父親。主持人要K的父親上台說些什麼,他只是輕輕地對主持人搖搖手。K的母親起身拉著父親的手臂要他坐在自己與K身旁的那個空位。舞台旁投影現場畫面的螢幕上,K掩面哭泣的身體在父親身旁抖動著,K的父親輕輕地拍了拍K的背,連主持人都在那瞬間停住本來高昂的語調,而J不知何時從她的位置起身,接過了主持人的麥克風,說起她想跟K結婚的衝動。
「我跟K是在游泳課程認識的。那時候我剛失戀也剛失業,剛好看到K的游泳課程在招生,想著反正也沒事就報了她的游泳課。
「我一直學不會游泳,怕水。K很有耐心的一次又一次陪我潛入水裡、起身,再潛入水裡、起身,好幾次我都覺得我快淹死了,一直拉用力地握住她的手,她都會在水裡拉著我著手,一起站直身體,我才發現我只要站起來就可以了。
「慢慢的,K就放手讓我自己練習在水裡和水面呼吸,直到我學會換氣,能夠一個人游完一趟一百公尺很久以後,她才沒有陪我一次又一次的游著那一百公尺。」
J說到這裡停頓了一會兒,螢幕上帶到K的畫面,她已經止住眼淚,等著J繼續說下去。
「陪學生游泳很正常對不對?但她竟然可以知道我什麼時候要出門游泳,每一次我到泳池都有看到她,我都懷疑她在我家裝了監視器。
「然後,中間的過程你們都知道了。去年我背著她報名了一個開放水域的游泳活動,我心裡想著我要一個人去挑戰看看,回來再跟她說我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
「只是那次活動很不順利,我一下水踩不到地就整個人緊張了起來,連換氣都忘記怎麼換,而且越是掙扎,就越沒有辦法浮出水面,直到我腦海中浮出了K的臉。
「我慢慢在水裡、水面調整自己呼吸的節奏。我不知道為什麼在那一瞬間,K在我腦海中的影像安定了我的情緒,我跟自己說我要平安的回到岸上,我要跟K說:『我想跟妳結婚,請妳娶我。』」
聽到J講到這裡的時候,我已經哭得不能控制,我想不起來我跟樂樂有沒有過那樣的情感?一種瞬間想起對方就會感覺到心安能夠安定往前走的感情?不論是她對我或我對她,我想不起來有沒有某一個瞬間,我們曾經有過這麼輕柔但堅定的陪伴,想走到未來的那端。
我走到離舞台有一段距離的地方想要打通電話給樂樂,卻又無法好好的呼吸繼續流著淚。
舞台那端繼續傳來J的聲音,她說:「我還是懷疑她在我家或我的手機上裝了什麼監視裝置,怎麼會我去哪裡她都知道。」全場傳來哄然的笑聲。
等我調整好呼吸不再流淚時,舞台上已經換上K在說話,她說:「我是游泳教練要知道J去哪裡很簡單嘛,沒有裝監視器這件事。而且明明開放水域有穿救身衣啊,不要這麼緊張啊!」舞台旁又是一陣笑聲。
嚴海在舞台旁專注地看著杜刷著吉他,K拿起麥克風唱著莫文蔚的〈慢慢喜歡你〉:
書裡總愛寫到喜出望外的傍晚
騎的單車還有他和她的對談
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愛看她穿
好多橋段
好多都浪漫
好多人心酸
好聚好散
好多天都看不完
給樂樂的電話響了許久。四、五年沒聯絡,我想樂樂應該已經把我的電話從通訊錄刪去了,我也找了一下才從email裡的資料找到樂樂的電話,掛上電話後我又打了一通,場邊K還繼續唱著:
慢慢喜歡你
慢慢的親密
慢慢聊自己
慢慢和你走在一起
慢慢我想配合你
慢慢把我給你
慢慢喜歡你
慢慢的回憶
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
因為慢慢是個最好的原因
樂樂還是沒有接電話,我坐在那個平原草地的樹下,吹著東海岸的風,打開手機的Gmail,用手機打了一封信給樂樂:
主旨:對不起,我想我沒有愛過妳
內文:
樂樂,好久不見,最近好嗎?沒什麼事,現在在台東的海岸邊參加一場婚禮,同志婚禮。在我們曾經一起住過的那間民宿,妳還記得嗎?
突然想起妳了。當時如果我們能預見未來的台灣有這樣一條法律能讓像我們這樣的人結婚,我們會不會就會為這個未來多努力一點?聽著婚禮上的新人說著決定開口求婚的事,想要打電話給妳,回答妳那天問我的:「妳有愛過我嗎?」雖然我知道現在說這些很多餘,但請原諒我此時此刻寫這封信給妳。
我想,我是個不懂愛的人吧!每一次說「我愛妳」的時候,都像在說謊一樣,好像說久了,就會明白「什麼是愛了!」
實際上我是一個不知道「什麼是愛」的人,我以為我給出去的一切都叫愛,卻從來沒有好好想過妳需要的是什麼?我以為待在妳身邊,讓妳替我做任何我可能不需要的事就是愛了。我甚至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讓我開口不斷地說著「我愛妳」的謊言。
對不起,那些年讓妳感受不到「被愛」的感覺;對不起,在四、五年後寫這封信打擾妳,謝謝妳曾經那樣陪我過了一段人生。如果有那麼一刻妳曾經感受不到我愛妳的痕跡,那絕對不是妳的問題,一定是我的,因為我是一個沒有辦法感受或表達愛的人。
但我確信的是,跟妳在一起的日子,曾經是那麼開心愉快,而且想要跟妳走一生的心情。謝謝妳曾經來過我的人生。
祝好
小虎。台東,曾經有妳的海岸邊。
*

J與K的婚禮結束沒多久,我清理起家裡一些該要丟棄的雜物時,找出了多年前跟樂樂一起生活時拍的照片。照片裡的我們都是開心的,但不知道為什麼我記著的很多都是那些爭執的、不愉快的細節,我感到照片裡的我和樂樂都如此陌生,好像當時的我是另一個我扮演著「愛著樂樂」的那個人。
在那場婚禮的樹下,打完那封信後,我將它存進我email的草稿匣裡。後來聽說樂樂去了日本和後來認識的男人在日本結婚了。嚴海和杜也去參日本參加了這場婚禮,再沒多久嚴海和杜的喜帖設計案躺在我的email收件匣裡。
嚴海寄出email的時候,也同時傳了一條訊息來說:「虎,我爸在醫院昏迷了。我媽要我跟杜辦婚禮沖沖喜,喜帖麻煩妳了。」
「你還好嗎?」我問嚴海。
「無所謂好不好囉!能跟杜辦手續,就算好事一件。如果能讓老頭醒過來,也算好吧!」
「杜他爸媽沒有說什麼嗎?」
「沒有吧!杜沒說,我也沒問。應該就沒什麼問題了吧!頂多就是他們不出現而已。」
我已讀嚴海的消息停了幾分鐘。才又回覆:「做好通知你,不收錢。希望你爸能醒來參加你的婚禮。」
嚴海傳來一張他和杜在J與K那場婚裡拍下手比愛心的圖給我。
我始終沒有傳送那封給樂樂的信,讓它一直留在我的草稿匣裡。
關於「愛」這件事,我想那是我一輩子說過最多的謊言。在我搞不清楚「什麼是愛」之前,從我口中說出的「愛」都是謊言。唯有在失去那一刻的悲傷,真實地在心裡某一個地方劃出一道淌著血的傷口,但我卻不知道為什麼那麼痛!
後記:
這是第一次把matters的社區活動以小說形式寫出,有點長抱歉,但不想分兩篇,可以先收藏。故事純屬虛構。沒有嚴海與杜,也沒有小虎與樂樂。唯有的是關於「我愛你」的謊言。謝謝你看到這裡。這是今天花了一點時間不小心寫了好長的故事。拍個手或打個賞吧!謝謝。
圖:
20190106那場婚禮的小物
200709台東沙漠風情
最後附上莫文蔚的〈慢慢喜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