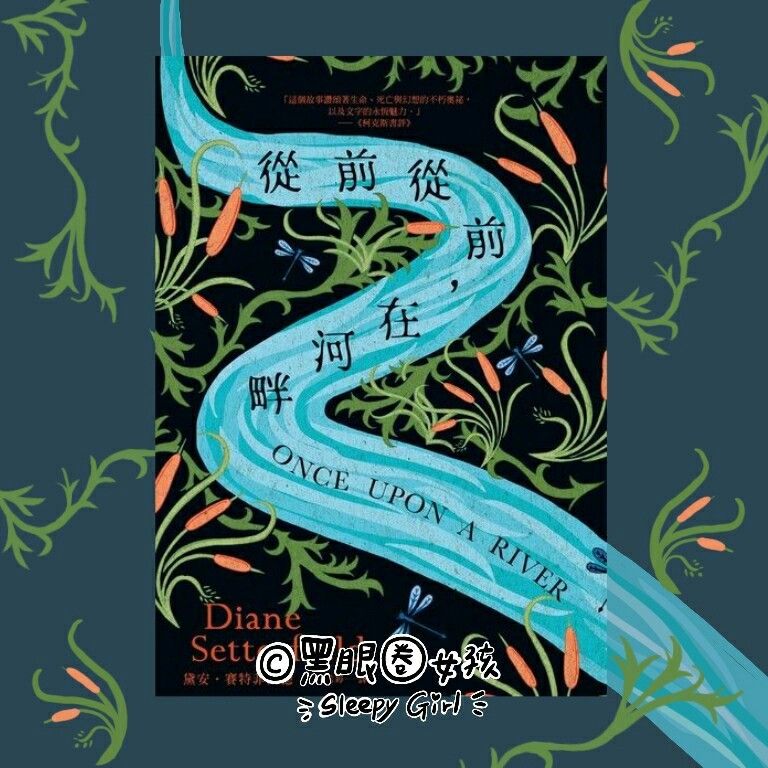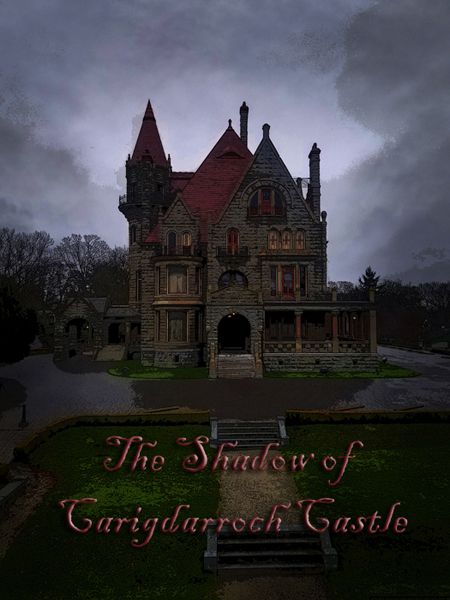撰寫: 顏鈺杰
歡迎按愛心、收藏、留言,留下閱讀的足跡🧡
正文:
警消破門而入,門外熙來攘往湊熱鬧的人群猶如池裡的錦鯉,看見岸上有絲毫風吹草動便蜂湧促前。門裡,只有一個穿著端莊肅穆的老嫗靜靜躺在撲滿碎花的床上,不開燈、不放電視、讓時間走過光陰的長河,留下一具裸裎的軀殼。死者是安妮,喬治一身的摯愛。
《愛‧慕》是2012年由麥可·漢內克編劇兼執導的法語電影,也為導演繼2009年《白色緞帶》之後斬獲了第二座金棕櫚獎,影片更名列當年《時代周刊》年度十佳電影第一名。《愛‧慕》紀錄了一對恩愛的退休鋼琴教師攜手對抗病魔的故事,漸漸地疾病壓垮了安妮的高雅從容,照顧的歷程也將喬治推向無涯的幽暗。這部電影有著法國電影的安靜、優雅,只是靜靜地訴說著疾病重重隱喻之下逐漸崩毀的中產階級夫婦,他們凝視死亡,感受生命落下前的最後一點重量。
凝視死亡的歷程
自從誕生我們就一路走向死亡,只是在疾病侵擾之前,我們不曾發現。
那一天前,安妮與喬治出席了學生的鋼琴演奏會,在公車上還意猶未盡地討論著,一如往常的幸福蔓延在空氣。翌日早晨,安妮上一秒還在與喬治談天說地,下一秒猶如木頭人似的,任何話題都激不起面容的變化。安妮病了,醫生診斷為頸動脈栓塞,從這天開始他們的生活徹底脫出了軌道。
跟疾病對抗的歷史,是一部壓抑史。
時間偶爾走過樹陰下篩下的片片稜光,安妮身體狀況好的時候,還能像個孩子般把玩著輪椅,在走廊前旋轉、溜搭。然而,當安妮第一次想要自己爬上輪椅卻重重摔落,發覺自己不再是身體的主人;第一次嘗試跳窗結束生命,才驚覺自己連餘生都無法掌握;又第一次尿失禁的愧疚,將平時高傲的自尊都無情的踐踏。
疾病的隱喻
安妮痛恨別人將她看作是病人,更準確來說,她憎恨疾病背後的隱喻,將她視為無用的、過度保護的,並且將所有正在發生的生活瑣事都從她身邊抽離,美其名曰要她好好養病。她不懂為何她無法參與朋友的喪禮、她更厭倦那些帶著憐憫的問候儀式。她頑強抵抗、她冷淡的面對那些殷切問候的臉龐、她拒絕任何積極性的治療,吃那些藥、做的那些診療,彷彿將她的靈魂抽乾後囚禁在玻璃藥罐內。
安寧與善終的想像過於美好而不真實,身體的苦痛磨平了她的稜角,從否認到憤怒,從討價還價到不得不接受。安妮如同孩子失神於霧氣氤氳的森林中,荊棘劃破腳底時帶血的痙攣,她的意念無法穿透冥遊如漆的黑夜。一路摸索,恐懼著何處傳來的水聲,踩上葉子的錯愕,她無法看清周遭景物、樹影、溪水、雲霧、山崖、魔神仔…。每一步都走得驚悸而惶亂,每一步都逼著她接受現況,催促著她手足無措的直面死亡。
直到疼痛再次將她喚醒,她甚至能聞到身上逐漸腐朽的霉味混雜著刺鼻的藥水味,她正在凝視死亡。
照顧者的囈語
喬治又何嘗不是一個悲傷的靈魂。他會為安妮做任何事情,協助她在輪椅與床褥之間來回切換,幫助她取睡前讀物,幫助她洗頭髮、如廁後穿褲子,為了寸步不離的看顧太太,喬治連出門採購的任務都交給了房門的妻子。
喬治了解安妮的各種習慣,他會用琴弦般的聲音親暱的徵求安妮同意後才搬動她的身軀,他會先以肉身體會過水的冷暖才讓水流淌過安妮斑駁的長髮。喬治盡量的為安妮卸下那層疾病的隱喻,不將她視為病人,所有照顧安排、照顧決策都盡可能依循安妮的意思。臨終前,安妮幾乎不在能表達自我了,喬治安頓所有需求後,仍不忘輕柔的詢問:「你覺得如何?」
然而,眼看病魔侵蝕著自己曾經的愛人,將她折磨成他不曾熟悉的模樣了。安妮偶而清醒的時光,彷彿偶爾從窗櫺流瀉的光點。如今,多半時候她只能發出零碎的囈語,偶爾她清醒的時候,會請求喬治讓她離開人世。
安妮不是第一次告訴喬治:「不想再繼續下去了」,一心求死的安寧讓喬治痛苦萬分,她拒絕食物、她嘗試跳窗…喬治即便同意安妮不使用醫療工具去延宕生命,但生者的依戀於無助又由誰來照顧?
時間猶如爬行的蝸牛,沉寂、遲緩,拖曳出透明的黏液。有一回喬治幾乎是被這種心態逼急了…
喬治: 「妳不喝水難道是想死嗎?」
安妮混沌的眼神裡混雜著怨恨與肯定,隨後把含在口中的水賭氣似的吐了出來。喬治賞了她一巴掌,隨後又自責地無地自容。
照顧者身後斥責的目光
女兒從外地趕回家想關心母親的病情,讓安靜的臨終生活多了些聲響。但是女兒的焦慮如豔陽一般跋扈,燒得青草枯黃、燒得喬治焦頭爛額,她一下指責為何沒有給母親積極的治療,又一下提議將她送到療養院以免拖垮父親的身體。這些旁人囁嚅的言語,不僅沒有讓情況改善,只是逼迫喬治拉開與她的距離,拒絕任何外援。
中產階級夫婦生活的瓦解
舉手投足都顯得高雅雍容的少奶奶,以及氣質端莊的老紳士,他們善於彈奏鋼琴道盡人生的悲鬱與歡快,在音弦之外,他們的肉體消融,在昏黃的燈暈下他們是人人稱羨的模範夫妻。然而,儘管再怎麼從容高雅,在經歷病魔折磨後,他們才意識到自己猶如自己過去生活一切循規蹈矩的理由,原來也只是官僚體系當中的一個零件。正如列夫.托爾斯泰的大作《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的主角,一切功名權位最後終將化歸為塵土,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不該外求。
生命很美好,只是太漫長了
夢境是現實經驗的蒙太奇。
午夜夢迴,喬治又夢見那深邃長廊,那雙佈滿青筋的手掐住喬治的咽喉。頻頻乍到的夢魘所潛藏的是照顧負荷,每一刻都無不讓他窒息。清醒的一刻仍餘悸猶存,此時,安妮的哭喊聲卻更加熟悉,「不全然是夢吧?」 喬治隨後往聲音方向走去。
這一天喬治不經意地說起童年的故事: 說到小時候去夏令營,因為不願吃完盤中的米布丁而被留在食堂好幾個小時,直到有一回發了高燒,被送往附近的醫院隔離。隔著玻璃窗,她終於見到了前來探望的母親,母親告訴小喬治每個星期都要寫信給她,如果想要留下就畫小花,如果不開心就畫星星。那明信片母親一直保存著,上面畫滿了星星。
說完喬治拿起枕頭摀住安妮口鼻。
琴聲嘎然而止,如同緊繃邊緣的橡皮筋應聲斷開。
歡迎按愛心、收藏、留言,留下閱讀的足跡🧡
FB南島電影迷
https://www.facebook.com/southisland.movie
IG南島電影迷
https://www.instagram.com/southisland.movie/
FB顏鈺杰
https://www.facebook.com/jacky.yen.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