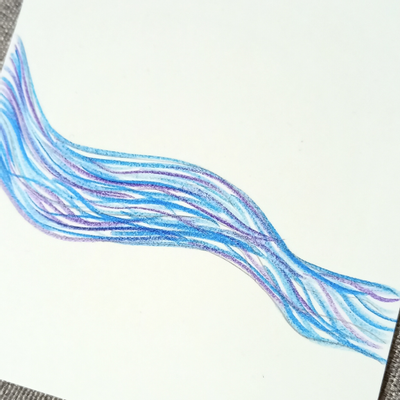我單槍匹馬,不必沙漠。
更新於 發佈於 閱讀時間約 1 分鐘
離開了家,是自己的眼淚溫暖手心,每一滴都瞬間冷卻,每一滴都瞬間蒸發,每一滴都瞬間告終。都是在對著自己宣告,沒什麼好留戀,沒什麼好留念,沒什麼好回頭,回憶,都像是擦上灰濛濛的天空。
那一片天空,用盡力氣寫在一張紙上,然後小心輕輕的揉成一團人們沒見過的團,最後輕率的放入瓶子滾去河裡,隨便它去哪都好。
我和我的馬,找最遠的夢。
誓言,早已經不必被火焰才能高漲,它自己一旦成了誓言便會高歌讚頌,抵達,知己知彼。
我和我的馬,奔最遠的海市。
躍上馬,奔越所有看過的沙漠和國度,月亮也被我拋棄後頭趕不上我,而誰想念我,而誰呼喚我,而誰而誰都不再那麼重要,荒漠廣大的,只剩下我與馬前行,踏遍所有沙塵,溫差所有心靈,誰令我感動,都是過去式,重要的都在背後隨流沙存入地底,沒人想知道的快樂。
一雜草,便要我臣服。
一顆日,便要我埋頭。
一絲雨,便要我神佛。
天天剩下的只有前進,就算迷路或者後退,都是前進。
沒有人可以保證,我們的天真,是不是殘忍相對而來的。
沒有邊境的黃沙,如渴望的世界,浩瀚無窮。
也想同蠍子共同殺死所有稱為的,我自己。
我和我的馬,睡最貴的蜃樓。
離開了家,心自由或者不自由都要在廣大無人之地才能明白,腳下到哪都是家。到哪都有留戀,到哪都有留念。
我已經回頭了,所有過往和回憶,我都回頭一個一個檢視一個一個挑剔,一個一個刪去,刪去我自己,讓自己還給自己。
臣服自己。
埋頭世界。
神佛虛無。
你還追趕什麼呢,你還不追趕什麼呢。
中庸總是最難,我們沙漏,我們倒轉,不斷不斷來回。
夢裡的世界,早陪我睡過千萬遍,醒來的肉身。
我單槍匹馬,不必沙漠。
為什麼會看到廣告
28會員
285內容數
留言0
查看全部Beck的沙龍 的其他內容
放下一切走進書,在書裡溜過春夏秋冬和所有虛無的夢。
冬季陽光需要挾帶寒冷才多少珍貴,書中的世界有時像日出、有時像黃昏、有時更像鬼魂,看到的字跟作者給予的字,有時經過腦袋過濾後成了不同出口,或許幻覺是最有趣的禮物,能從四處牆生出空氣,也能輕易的,將自己輾成空氣鑽入被地震裂過的隙。
開著車,我們的快樂隨著海,拍打每一次的礁岩,有時一點點,有時激烈的。
都是時間給的火花。
開著車,我們的安靜隨著路,隨著轉過的彎,隨著經過的顛頗,緩緩悠悠的隨著路,帶我們可以去到的地方,和你。
突然遙想從前還未有路的誕生,而我們在哪兒遊蕩。
給了時間成了一切。
給你的話:
給你的日子,是一張紙,密密麻麻的字,沒辦法給你看到那些畫面,雖然有點可惜卻又多點神秘,請求需要,靠你的腦海來看。
他們說的森林,跟我去過的其實沒有不同,只是身體已無法再年輕氣盛的站至山頂吶喊,所以我開始懷疑是自己的身體想愛上海,而不是我。
美好留在原地,我把自己趕出山林,不意外。
這一天來到距離鬧區不遠的曉咖啡,一整間獨棟的老宅咖啡廳,特別的富有味道。
也因距離離鬧區不遠,所以若來附近遊玩可以考慮將它列入其中的清單內,算是蠻方便做歇腳的,而且附近算是蠻清幽的很適合散步。
裡面的位置不同樓層有不同的感受,店主的用心通常從那些小小燈具就可端倪一二。
推薦大家可以放入口袋名單。
工作與職場大概佔據人生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遇到的問題百般花門,人也是各種米養出來的各式各樣,說誰好或是不好,其實每一個地方的老闆跟主管們都各有所好去聘用自己要的人。
做網路電商的速度節奏都算相當的快,當時只要更換一個大主管,我跟同事就要全部重做簡報,然後再次說明所有未來的目標和規劃。
放下一切走進書,在書裡溜過春夏秋冬和所有虛無的夢。
冬季陽光需要挾帶寒冷才多少珍貴,書中的世界有時像日出、有時像黃昏、有時更像鬼魂,看到的字跟作者給予的字,有時經過腦袋過濾後成了不同出口,或許幻覺是最有趣的禮物,能從四處牆生出空氣,也能輕易的,將自己輾成空氣鑽入被地震裂過的隙。
開著車,我們的快樂隨著海,拍打每一次的礁岩,有時一點點,有時激烈的。
都是時間給的火花。
開著車,我們的安靜隨著路,隨著轉過的彎,隨著經過的顛頗,緩緩悠悠的隨著路,帶我們可以去到的地方,和你。
突然遙想從前還未有路的誕生,而我們在哪兒遊蕩。
給了時間成了一切。
給你的話:
給你的日子,是一張紙,密密麻麻的字,沒辦法給你看到那些畫面,雖然有點可惜卻又多點神秘,請求需要,靠你的腦海來看。
他們說的森林,跟我去過的其實沒有不同,只是身體已無法再年輕氣盛的站至山頂吶喊,所以我開始懷疑是自己的身體想愛上海,而不是我。
美好留在原地,我把自己趕出山林,不意外。
這一天來到距離鬧區不遠的曉咖啡,一整間獨棟的老宅咖啡廳,特別的富有味道。
也因距離離鬧區不遠,所以若來附近遊玩可以考慮將它列入其中的清單內,算是蠻方便做歇腳的,而且附近算是蠻清幽的很適合散步。
裡面的位置不同樓層有不同的感受,店主的用心通常從那些小小燈具就可端倪一二。
推薦大家可以放入口袋名單。
工作與職場大概佔據人生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遇到的問題百般花門,人也是各種米養出來的各式各樣,說誰好或是不好,其實每一個地方的老闆跟主管們都各有所好去聘用自己要的人。
做網路電商的速度節奏都算相當的快,當時只要更換一個大主管,我跟同事就要全部重做簡報,然後再次說明所有未來的目標和規劃。
你可能也想看

















Google News 追蹤

嘿,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大家都在做什麼呢?
跨年夜的我趕工製作某個外包設計案,在工作告一段落時趕上倒數。
然後和兩個小孩過了一個忙亂的元旦。在深夜時刻,看到朋友傳來的解籤網站,興致勃勃熬夜體驗了一下,覺得非常好玩,或許有人玩過了,但還是想寫上來分享紀錄一下~

Hugo拿來挑戰烈焰猴的寶可夢是棄世猴,這一次的挑戰邏輯,就只是單純的利用格鬥招式來打岩石太晶的烈焰猴...

穿越來的高武力值吃貨受 X 有人妻技能的落魄將軍攻
強強之可愛的穿越基建文

今天台股跳空開低下殺,盤中下殺千點,最終是以下跌999.46點,以-4.52%坐收!
其中籌碼部分,外資是大賣千億,創下歷史新高的紀錄
在外資持續大賣之下,台股的走勢相對就弱勢許多
但在持續下殺過程中,我會開始尋找進場抄底的機會...
伺機再度抄底 00631L!!!
https:

友人啊,
你在歲月長河中,
磨去了獨特的稜角,
青春的熱血,
如黎明前的霧,散盡無痕,
你以純粹之心,
追逐著不確定的繁星,
夢境與現實,
交織成無盡的幻想,
星星之火,
雖渺小,卻有燎原之勢,
成功的畫卷,
往往在沮喪中展現其殘缺之美。

簡單收拾了一下隨身的衣物,帶上一些盤纏與糧食,我就踏上了前往邊境的道路。
從小養尊處優的我,第一次獨自出遠門,心中不免還是有些擔心。

「很久沒出門了。」我騎在神采奕奕的白馬背上,長舒一口氣地自語。
解開的手銬被重重地摔在地上,身後散發出貴族階級奢靡腐敗的惡臭,令人作嘔。我一刻也不想停留,驅馬離去。夕陽拉長了人馬的影子,一晃一晃的。

過去在新聞上提到塔利班時,都是他們不受控地破壞或屠殺等報導,當時心中只為那些受害者不捨,並讓身處台灣的我無法想像怎麼有如此恐怖又不自由地方。而七月因緣讀到兩本塔利班與女性有關的故事,讓我對塔利班政權下的人權迫害又有更多的認識,尤其是女性。
我只能說只要塔利班政權還存在的一天,不論是阿富汗或是巴基斯

當一群深具野心、勇於跨海工作的人,撞上僵固的法律與移工制度;這就是在「另一面」的臺灣,正不斷發生的事。
《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由記者簡永達耗時七年,從臺中第一廣場開始,跨越臺灣與越南多個城市所採集合成的故事,整本書分為「地下社會」、「危險之島」、「異鄉家人」、「人權大浪」四大主軸。

嘿,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大家都在做什麼呢?
跨年夜的我趕工製作某個外包設計案,在工作告一段落時趕上倒數。
然後和兩個小孩過了一個忙亂的元旦。在深夜時刻,看到朋友傳來的解籤網站,興致勃勃熬夜體驗了一下,覺得非常好玩,或許有人玩過了,但還是想寫上來分享紀錄一下~

Hugo拿來挑戰烈焰猴的寶可夢是棄世猴,這一次的挑戰邏輯,就只是單純的利用格鬥招式來打岩石太晶的烈焰猴...

穿越來的高武力值吃貨受 X 有人妻技能的落魄將軍攻
強強之可愛的穿越基建文

今天台股跳空開低下殺,盤中下殺千點,最終是以下跌999.46點,以-4.52%坐收!
其中籌碼部分,外資是大賣千億,創下歷史新高的紀錄
在外資持續大賣之下,台股的走勢相對就弱勢許多
但在持續下殺過程中,我會開始尋找進場抄底的機會...
伺機再度抄底 00631L!!!
https:

友人啊,
你在歲月長河中,
磨去了獨特的稜角,
青春的熱血,
如黎明前的霧,散盡無痕,
你以純粹之心,
追逐著不確定的繁星,
夢境與現實,
交織成無盡的幻想,
星星之火,
雖渺小,卻有燎原之勢,
成功的畫卷,
往往在沮喪中展現其殘缺之美。

簡單收拾了一下隨身的衣物,帶上一些盤纏與糧食,我就踏上了前往邊境的道路。
從小養尊處優的我,第一次獨自出遠門,心中不免還是有些擔心。

「很久沒出門了。」我騎在神采奕奕的白馬背上,長舒一口氣地自語。
解開的手銬被重重地摔在地上,身後散發出貴族階級奢靡腐敗的惡臭,令人作嘔。我一刻也不想停留,驅馬離去。夕陽拉長了人馬的影子,一晃一晃的。

過去在新聞上提到塔利班時,都是他們不受控地破壞或屠殺等報導,當時心中只為那些受害者不捨,並讓身處台灣的我無法想像怎麼有如此恐怖又不自由地方。而七月因緣讀到兩本塔利班與女性有關的故事,讓我對塔利班政權下的人權迫害又有更多的認識,尤其是女性。
我只能說只要塔利班政權還存在的一天,不論是阿富汗或是巴基斯

當一群深具野心、勇於跨海工作的人,撞上僵固的法律與移工制度;這就是在「另一面」的臺灣,正不斷發生的事。
《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由記者簡永達耗時七年,從臺中第一廣場開始,跨越臺灣與越南多個城市所採集合成的故事,整本書分為「地下社會」、「危險之島」、「異鄉家人」、「人權大浪」四大主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