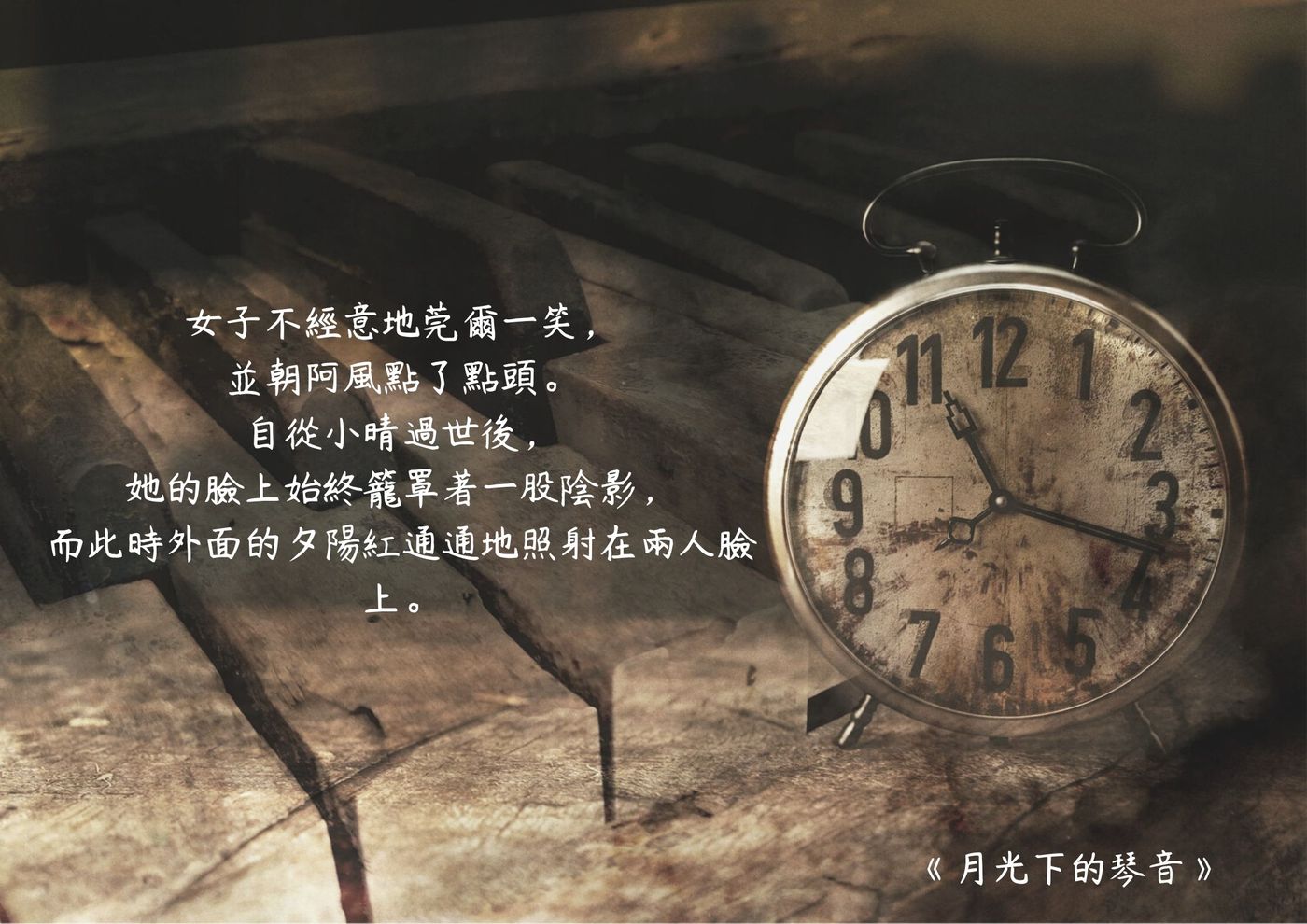「阿毛,男人與女人是不同的物種,不同的計時方式。」男子一頭亂髮,遮掩美人尖,鬍渣修飾臉頰的輪廓,眼皮在崩塌的邊緣。他坐在祭司屋前的木製台階上,捲起有放鬆療效的草藥,叼在唇間,指尖點燃另一端。「如果你能想像女人從初經那刻起所背負的詛咒與祝福,將那份痛楚與焦慮作為你身體的延伸,看見彼此的未來,倫理關係才真正可能。」
阿毛依著男子的大腿躺下,如往常。
「你的身體會傳送一些訊息,她的身體也會。訊息如同颱風,掃過我們原本就處於混亂中的大腦。」月光下的教區,每扇燈火搖曳的窗戶都有故事正在發生。於此唯一的光點,只有燃燒中的手卷草藥。「沒有人給我一個足以放棄的理由,故事的結局就你知道的那樣,你醒來,你在橋的另一頭。」
阿毛用鼻頭磨蹭男子的腿,如往常。
「誰的美夢,誰的惡夢?清醒後殘留的是餘韻,還是傷痕?」男子吸了一口手卷草藥,從鼻孔緩緩吐出。
阿毛突然抬起頭,站起身望向街道,尾巴來回拍打男子的臉。金屬配件的碰撞聲和腳步逐漸逼近。
「妳那可愛的學徒和被監護人拒絕招待我進屋。」男子以聲音表明身分。
「我放學徒先回家是希望她早點休息,不是為了招待你。」腳步聲的主人脫下皮革手套,輕撫阿毛的後頸,填滿阿毛的飯碗。「陪伴有病的人很辛苦吧?阿毛是好狗狗喔。」
「妳覺得我該參加葬禮嗎?」
「阿毛,下次這傢伙靠近,直接咬死。」腳步聲的主人穿回手套,越過男子,踏上台階。
「我以瑟恩家的前第一順位繼承人身分,想和『瑟恩專案』的召集人珮翠絲Ina 交換情報。」直球拋出,男子深深吸了一口草藥,等待藥效,等待回應。「說起來,我也算嫌疑人吧?」
「你早就放棄繼承權了。如果你是嫌疑人,全程和你一起在艾歐蘭為你擔保不在場證明的我,豈不是共犯?」珮翠絲奪走男子指縫間的捲紙,同坐在台階上,隔著一隻阿毛的距離。「抽完這根我就要睡了。」
「等等,我有處方簽。」
作為回應,珮翠絲深吸一口手卷草藥,緩緩吐在男子臉上。
「我很期待在喪禮上華麗登場時,家族成員的表情。」男子搔搔阿毛的下顎。「可是,妳知道的,我的登場只會讓案情更複雜。我討厭麻煩。」
「說些我不知道的事。」珮翠絲揉搓眼眶,舒緩疲倦。「我和一群以菁英自居的官僚周旋整晚,不要逼我把你踢下橋。」
「上次離開前,我送他的反曲弓,和一些,恩,小技巧,他幾乎完全掌握了。那孩子發育得很快,無論是肌肉、腦袋還是喉結。也許他會開始好奇生父是誰,前提是徵得他的生母允許。」
「阿毛,咬他。」
阿毛輕輕含住男子的手腕。
「鞣過的皮革不好吃喔。」男子將手交給阿毛,單手抽出另一根捲好的草藥,就著嘴,彈指點燃。「他這年紀的孩子想證明自己特別,又不想被同學排擠在外。他拋出了訊息,他以笑容掩飾,我無法置之不管。明年春天,他應該可以順利通過考試,選擇自己的未來,選擇是否與生父相認。」男子和珮翠絲望著教區,望著路燈,將阿毛的嘴推回飯碗。
「我讓你接近他,只因你們同樣接受Nita Ina 庇護,你是給予指導的前輩,不是送禮物誘拐孩子的戀童癖。」珮翠絲又吸了一口,捲紙燃燒的邊緣幾乎快碰到她的手指。她綁著和兩人見面時同樣的馬尾,和少女時期同樣的馬尾,隨著晚風輕輕搖晃。「沒有你的那一年,發生了很多事。在那之後,我沒有停止評估,也許在你死掉的那一刻,我才有辦法說出口,說你是怎樣的人。」
「妳就當我死了。那孩子和阿毛一樣,值得更好的未來。」我撫摸阿毛的背,讓手找點事情做。「瑟恩家的第一繼承人找過我,為滿足舊日的陋習,延續骯髒的血脈。現在,族長死了,許多事情會改變,也許那孩子能從詛咒中解放。」
「你以為周遭的人都比你笨,所以你可以操控、玩弄他們的人生?」再一口,時間的星火淹沒於她的指間,化為她雙唇吐出的煙霧,飄向她所仰望的星空。「河水帶著那孩子擱淺於此,Nita Ina 親自將他託付給我,滿月之夜,伊拉瑟米安的看顧下,眾祭司與司教的見證下,託付給我。這就是真相,那孩子和你沒有關係。」
珮翠絲沉默,留下阿毛咀嚼的聲音。男子瞥見她的肩膀在陰影中顫抖。男子用小腿頂了頂阿毛。阿毛抬起頭看看男子,轉頭看向顫抖中的珮翠絲,蹭入她懷中。
珮翠絲輕撫阿毛的肩頸,古老、不神祕的儀式。男子點燃另一支手卷草藥,修飾時間。
「有考慮共同監護嗎?」男子趁珮翠絲懷中抱著阿毛,沒手攻擊時,拋出提議。「就是,呃,找另一名監護人分擔。」
「名額已滿。」珮翠絲的目光透過阿毛的毛髮射穿男子。
「可靠嗎?」
「質疑我的能力,質疑我的眼光。」珮翠絲放開阿毛,搶走男子手中的手卷草藥,「誰給你的資格感?」
「不是資格感,是自卑感。」
男子偷窺珮翠絲的側臉。她叼著手卷草藥,手拖著下巴。
「是阿毛。」珮翠絲眼光的餘角瞥了男子一眼。
「明智的選擇。」男子雙手捧著阿毛的臉、揉搓。「好狗狗,可惜你不是人。」
阿毛擺脫男子的手,反咬一口。口水沾滿皮革手套。
「阿毛,他有毒。」珮翠絲沒積極阻止阿毛。叼著手卷草藥的嘴角微微上揚,瞇眼看著男子,猶如初次見面彼時。
「妳有考慮過——」
「沒有。」
「一起離開這裡。」男子輕輕推開阿毛,甩甩手套上的口水。「艾歐蘭不錯,如果妳願意的話我可以妥協。雖然離開這座隨時可能被入侵的島嶼是更明智的做法。世界很大,有個船長欠我人情。」
「太多牽絆,離不開了。」
「我讀過一則屬於舊日的故事。」男子清清嗓子。「從前從前,有一座城市,想離開的人必須接受一項試煉——」
「故事會很長嗎?」珮翠絲難掩哈欠。
「當作床邊故事,如何?」
「我不想跟孩子們解釋為何你從我的臥房走出來。」
「妳負責的案子很危險,我可以介紹一隻大狗——」
「我怕他跟新來的貓打起來。」珮翠絲轉身掀開男子的兜帽、揪起男子的領口,一腳跨過男子的身體,踩在階梯上,用抽剩的手卷草藥堵住男子的嘴。
珮翠絲的嘴唇越過男子的臉頰,在耳旁低語。
「我會在橋的另一頭等你。」
她的溫暖就在男子伸手可及之處,攬入懷中的重量男子無法承擔。
「你在發呆什麼?」
「我們那何時會踏上那座橋?」男子收起手,收起妄想。
「用你的話來說:『不是今天。』」她鬆開手,體溫遠離,留下味道。
「謝謝。」
「你抽太多了?」珮翠絲俯視男子,眉頭深鎖。
「會痛啊。」男子摀著胸口。
「滾回你的鳥窩。」珮翠絲咕噥了什麼,拋開男子,回到眷舍。
「阿毛,除了那三個孩子,有多少人在這扇門後過夜?」
阿毛看了男子一眼,將臉埋入飯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