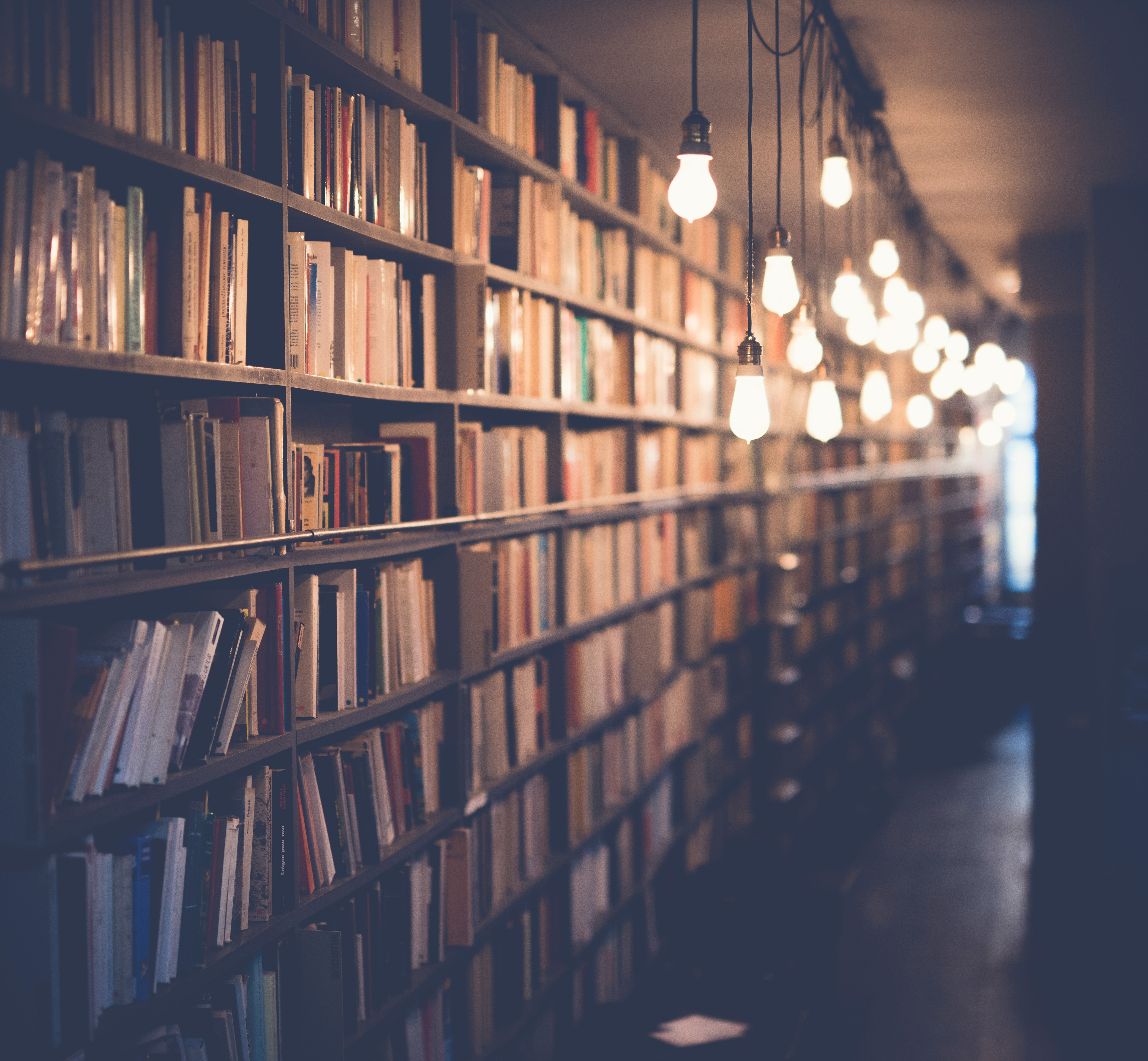儲藏室鐵櫃第三格抽屜裡,躺著1999年的公共電話卡。塑膠表面浮著白翳,卡號被刮損成模糊的暗碼,像被歲月咬缺的月相。
那年全市裝設IC卡電話亭,藍色機身在放學路上接連綻放。總故意繞過兩條街,只為看徐蔚寧踮腳撥號的樣子。她馬尾晃動的弧度,和話機按鍵的嗶嗶聲響,在青春期的心跳裡譜成某種摩斯密碼。
「10位數的卡號就是10次通話機會。」她撕開新卡封膜時,睫毛在頰上投出柵欄狀陰影。我們共用電話卡,約定存夠錢就致電電視台的流星雨熱線。她總把餘額倒數寫在掌心,課間攤開給我看逐漸萎縮的數字,彷彿我們正共享某種生命的沙漏。
最後一格晶片在冬至前夕耗盡。她將空卡按在我外套口袋,「等新的許願週期」,呼出的白霧纏住路燈光暈。後來她父親調職,搬離前夜我攥著儲蓄罐奔過五條街,卻在電話亭外看見她緊貼玻璃的臉——正在通話的,哭花的,被話機藍光浸透的臉。
成年後收藏了上百張廢卡,唯獨這張留有指甲刮痕。刮開氧化層那日才發現,背面用鉛筆寫著極淡的「對不起」。窗外捷運轟隆碾過,恍惚又聽見話筒裡的忙音,穿過四分之三個世紀的時差,在耳蝸深處震盪成宇宙誕生前的餘波。
那些未說出口的密語,終究隨著銅纜一起鏽蝕。而我們都成了斷訊的衛星,在各自的軌道,永恆重播那年凍結在話亭玻璃上的告白口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