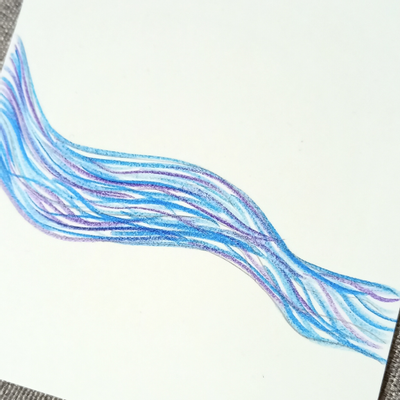他的喉結起伏,像一隻鴿子在求偶時反覆膨脹收縮的脖頸。
「妳知道嗎?有人說,很不敢看我的眼睛,我有一雙穿透力很強的眼睛,這讓他們害怕。」
這句話,為確保她有聽見,他說了不只一次。他又向她強調,但是,愛不是理解,是無懼地敞開。這是從網路上看到的句子。她一聽笑出來。「聽起來好像暴露狂,好唐突。」
「暴露」,唸出來就像女生在他的臉頰上吹一口氣。而「唐突」這個說法,則讓他非常高興。他喜歡她比起前幾個曖昧對象明顯豐富的日常語言。喜歡她在閒聊時隨意丟出知識的碎屑,可愛,但都只是些半吊子。他的想法是,因為聰明得恰到好處,她尚能保持溫柔。通常她不會堅持爭論,就算不同意,也只會抿一下嘴唇,把眼神別開。
今天他們出門逛夜市,已是十月中旬,位處亞熱帶的鬧區向來無視季節,人們在這氣味複雜的大烘爐之中行走覓食,時不時,一隻黏膩冒失的手臂貼上來。安慰的是,她今天的妝很高明,除了濃淡適宜之外,被島國那惡名昭彰的潮濕熱氣一潑,如最後一口噴在水墨畫上的水,暈開服貼得恰到好處,有一種包容的氣象,能讓他原諒世界對他犯過的一切錯誤。他檢視她的牛仔短裙,腿型不算好看,勝在皮膚十分光滑細膩。牽起她的手時(一雙柔嫩居家的手),他感嘆自己已經成熟得能夠理解「有話聊」的cp值遠遠高過一雙美腿。
只是不知為何,她今天很快樂。快樂得過頭了,驕傲自滿起來,甚至許多次打斷他說話。她用比平常高八度的聲音說要買排隊美食,然後轉身,馬尾飛揚,很快地隱入人群之中。那馬尾輕浮地把他應得的尊重搧到一邊。
他闔上半張的嘴,買好飲料,又站在原地等了五分鐘。
一架民航機像大鳥張開翅膀低低飛過,金屬硬肚子貼著建築的頂端,很短暫的一瞬間,所有人都縮回了自己的世界。
沒有攤平的衣領冷不防劃過耳尖。那癢意,小蟲一樣地,從耳廓一路嚙咬著他身上不安的皮屑,肥碩起來,他感覺那小蟲正蠕動著抵達背部,但是,他以全副的自制,絕對不允許自己動手去抓。
他想起昨天的夢,打了寒顫。
擠到夜市入口處,牽一台租借的市民腳踏車,再繼續艱難地擠出人群,遲滯許久的秋意彷彿此時才降臨,嗖地鑽進薄短袖裡面,奶頭立起來。他朝空氣流動的方向看過去,馬路對面,掉光了葉子的行道樹上,一隻鴿子停在那裡,全身都覆蓋著瑩瑩白光,填補了月的欠缺,永恆的圖象,他心底被人類虛構文明刨挖出來的坑洞頓時現形。
你問愛是什麼?愛,媽屄的,愛是一把鐵鍬。
他認得那隻鴿子,多年以來在他的窗外徘徊不去。他歪頭看牠歪著頭,那注視,指向明確的一個點、一束親切而溫柔的光。在謊言搖搖欲墜之際,在他自己都快要無法自我說服之際,現實裡幾乎已經不存在這種光。儘管有時他覺得,自己願意永遠陷落在那個小小的、顫動之上。
手機上Google地圖顯示,從這裡騎腳踏車到女孩家,需要四十五分鐘。他挺起胸膛,像個英雄一樣啟程。車輪滾輾過去,時間被甩在後面,前進或者後退,這是一個相對的問題。
她曾跟他抗議,你總是心不在焉,看來看去,到底在找什麼東西。找尋,這個關鍵字讓他陷入無措,只好胡亂糾正她,這叫做被動式調情。跟誰,她很快追問。妳現在不是正看著我嗎?他絕不會承認自己還在找她,或她們,在此,區分單數與複數沒有意義,他心裡恆常想著的、他永遠的日出與日落,任何一個可能會愛上他的女孩,所有他本應擁有卻注定失去的女孩──他訝異自己記性之差。像是現在,已經快要想不起她那張過於平凡以至於不知道該讓觀者眼睛聚焦於何處的臉。然而想不起她,等同想不起自己。記憶讓他辨認出自己的位置。
他從未想過,離開他之後,「她們」是否仍是原本的樣子。不過,在複數的她們之中,以他為中心,作為一切的起始,他緊緊把握住她的名字,小婷,好聽又好記。而這個名字,如今除了順序本身,他不打算賦予其更多重量。純粹是記憶的局限之故。他們。她們。隨便,為了完成一句話,你選定一個字,就不必再選另一個字。現在只有四十五分鐘。不要拘泥於細節,不要總是在自己面前樹立敵人,到頭來,大家都不過是有需求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他習慣了胡言亂語。不妙的是,比起他認識的每一個女人,他太慢發現語言的欺騙性。他們總說男人是編織謊言的人。事實上如果有得選,他只想當一隻咕咕啼叫的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