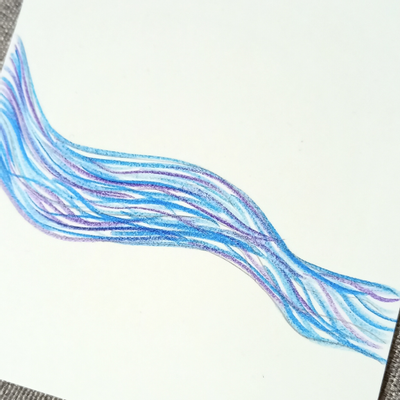文/文成序二創
我曾經聽見貝多芬的吶喊, 不是在音樂廳,也不是在課本裡, 而是在一個雨夜,耳機裡的第三號交響曲, 那聲音像是從他破碎的耳朵裡滲出來, 穿過時間,撞進我的胸口。

這幅畫面捕捉了貝多芬在風雨交加的夜晚,孤獨地坐在窗前,彷彿在與命運搏鬥。他的眉頭緊鎖,雙手深陷琴鍵,窗外的雨水如同樂譜般流動,映照出他內心的吶喊與不屈。這不只是音樂的場景,而是靈魂的震盪。
我感受到他的手在琴鍵上顫抖, 不是因為技巧,而是因為憤怒。 他曾相信自由,曾相信拿破崙, 但當權力變成皇冠,他撕掉了獻詞, 像是撕掉了自己的一部分。
我看見他坐在維也納的窗邊, 筆記本上潦草的音符像是傷口, 他不再聽得見世界, 但他聽得見自己—— 那是最痛的聲音,也是最真的聲音。
我曾經摸過那段旋律的邊角, 在第二樂章的葬禮進行曲裡, 我摸到理想的遺體, 它冷卻了,但還有餘溫, 像是某種信念還在呼吸。
我無法言語那種震動, 它不是感動,是某種被喚醒的羞愧, 我曾經逃避過自己的聲音, 但貝多芬沒有,他選擇留下, 選擇在失去中繼續創作。
我確信,那不是一首交響曲, 那是一封信,寫給每個在黑暗中還在尋光的人。 我曾經聽見貝多芬的吶喊, 而現在,我也開始吶喊, 用我自己的語言,用我還能聽見的誠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