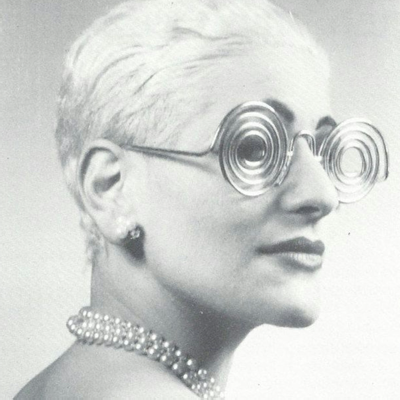《卡提耶-布列松:二十世紀的眼睛》(Henri Cartier-Bresson: L’Oeil du siècle)
作者:皮耶.阿索利納/衛城出版
閱讀這本書、卡提耶-布列松的經歷時,總像是在每個轉角處就會撞上一個名人,或是看見一件有趣的事情在眼前發生。
讀傳記有趣的是——名字不再只是個名字,不是頭銜,不是作品,不是某個領域裡的象徵,而是真正開始認識一個人。
或許在此會展開的叩問是——我們怎麼能保證全面瞭解他?事實上,我們始終也只能認識人的某些面向。
「被拍的人保留了自己一部分的臉孔,而攝影師則得到了他一部分的靈魂。」——《卡提耶-布列松:二十世紀的眼睛》
如果要向不認識卡提耶-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人介紹他——可能是作為卡繆《異鄉人》書封的經典人像照。可能是拍攝了甘地之死、國民黨覆滅之時、巴黎解放。也可能是許多人像如沙特、西蒙·波娃、畢卡索、馬諦斯、榮格、尚·雷諾瓦。或者是創立了紀實攝影的指標性組織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
——卡提耶-布列松與機運和時代站在了一起,也以觀景窗的視野掌握了那個時代。
馬格蘭攝影通訊社是由布列松和同為攝影師的卡帕(Robert Capa)等人共同創辦(1947)。在那個時代,是他們將底片(影像)作為本位——攝影師擁有影像作品的版權且有權要求雜誌社如何使用——讓攝影師與底片共為主體,確立了攝影師是攝影師。
創辦人也成為了他代表性的身份之一,影響著後世凝視他的方式。
▌卡提耶-布列松的觀點
若談論到布列松的作品特徵,絕不可避免提及的是幾何學與超現實主義。
他在年輕時向立體派畫家洛特(Lhote)學習並愛上了幾何學,也是從那裡聽到了源自於柏拉圖(儘管他以為是來自拉斐爾)的這句話:「唯幾何學家方可入內」(Nul ne peut entrer ici s'il n'est pas géomètre,書中有兩種譯法:唯幾何學家有資格進入),這句話也是後來其接受世界報採訪時所使用而遭受批評的標題(1974)。註1
布列松在藝術圈子裡遊走,他畫素描、油畫也與各種名人、藝術家參與同一個沙龍、聚會,對超現實主義的觀點與思考也是在這些人與想法碰撞中逐漸形成。
後來布列松在前往非洲象牙海岸進行旅途時拍攝了第一批照片,在非洲的經歷為他觀看馬丁·芒卡西那張《坦噶尼喀湖的三個男孩》(Three Boys at Lake Tanganyika,註2)時增添了不一樣的情緒。這張照片本身不可思議巧合而成的光影構圖、水花、人體、動作,靜止卻富含生命力的瞬間在非洲土地上發生且被記錄了下來,這同時也是展現了攝影力量的瞬間,對布列松來說充滿了深刻的震撼與意義。
而布列松(確實不是羅伯·布列松)也曾夢想拍電影,嘗試去找了超現實主義導演布紐爾自薦卻被拒絕。再找了帕布斯特也被拒絕。在最後給了他一個助手職位的是尚·雷諾瓦,也才因此有機會投入電影行業,儘管後來因為生計轉向攝影,但這個經驗也讓他在未來拍攝紀錄片時能建立起更明確的藍圖。
二戰期間,卡提耶-布列松成為了戰俘將近三年。在戰俘營內與人暢談自由後的計畫時,布列松說的是:他要當畫家。但在第三次逃脫計劃才終於逃出戰俘營的布列松,選擇找回並拿起了他的徠卡相機——他認為攝影是在那個時刻最適合的工具,他決定以攝影師的身份紀錄下那個躁動不安的世界。
布列松接了肖像照的工作,紀錄了戰後的巴黎景色,也花更多時間走訪各個國家拍攝,他前往印度拍攝到甘地生前最後一張照片還有其葬禮(註3),他也在一九四五年前往中國拍攝政權交替的時刻,他也曾經成為冷戰時史達林逝世後,第一個得到蘇聯簽證的攝影師。
這些經歷都化為布列松的養分,成為他攝影視角的自然本能,也決定性影響了其攝影之路。
在一九五二年,布列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攝影集《匆忙的影像》(Images à la Sauvette),當時他是被出版社要求——或者說逼迫為這本書寫下了一篇前言,並被命名為〈決定性瞬間〉。而在美國出版時捨棄了原本的書名「匆忙的影像」,選擇使用現在廣為人知的《決定性瞬間》(The Decisive Moment):
「世間萬物皆有其決定性瞬間,創作一幅傑作就是要意識到並抓住這個瞬間。當你身在革命中的國家,一旦錯過,可能就無法再找到或感受到。」
「對我而言,攝影就是在幾十分之一秒裡同時意識到一件事實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大力動員各種視覺形式來表現這一事實。主題的大小不在於收集事實的多寡,因為事實本身沒有什麼意思,重要的是在眾多事實中選擇、抓住那個真正和深刻現實相關的事實。在攝影中,最微小的事物都可以是偉大的主題,而那微小的人性細節更可以成為基調(leitmotif)。」
而「決定性瞬間」就此成為了紀實攝影界的重要觀點。
▌卡提耶-布列松——是個怎樣的人?
卡提耶-布列松是個法國當地的資產階級大姓,但他選擇背離家業投身藝術,而這個姓氏帶來了一些壞處,但更顯而易見的是益處——居住的地點、寬裕的資源、家族的人脈都是讓他更容易深入藝術圈子中的原因。
布列松有專橫又脾氣糟糕的一面,曾跟幼時便結交的好友、後來成為小說家的蒙迪亞哥(Mandiargues,註4)結伴探索歐洲,期間兩人步調太不一致,儘管時常吵架後又會和好,這段關係還是走向了破裂。但後來在已是戰後的十年後,布列松也重新與蒙迪亞哥一起踏上旅途、進行了和解之旅。
雖然布列松是在非洲拍攝了第一批照片,但在非洲時實際上他大多時間都花在打獵上面(打獵是他幼時與父親的共同活動),拍照甚至是打獵的閒暇之餘才做的事。
書中也提到了許多布列松拍攝那些藝術家、名人肖像照時的故事。他拍攝肖像時與被攝者像貓與老鼠的對峙——要時常跟不喜愛被拍攝的藝術家相互角力來捕捉想要的畫面。
而布列松拍攝了那麼多的名人、友人,但他有一些一直沒拍攝的對象,其中一個人便是印度導演——薩雅吉·雷(Satyajit Ray)。薩雅吉·雷與布列松相互欣賞,薩雅吉·雷的處女作《大地之歌》便是受了卡提耶-布列松攝影時堅持使用自然光的做法所影響(註5),所以在拍攝電影時盡可能利用日光,而布列松則敬佩雷的為人與導演能力。因為他們有許多共同話題,所以布列松不想讓相機破壞他們之間的關係。
有不少地方也可以看出布列松對不同領域專業的尊重——他將沖印工作交給信任的朋友(雖然其中一個原因是他不喜歡也不在意暗房作業),將攝影書籍的出版與策展交給德爾皮爾(Robert Delpire,註6),也是德爾皮爾想到可以找沙特替布列松的攝影集《轉折中的中國》(D'une Chine à l'autre,1954)寫序。
他也讓其他專家進行策展,自己只負責把關照片的挑選。
實際上布列松對於繪畫的企圖也顯而易見——『「你不知道?」萊達驚呼道:「你不知道卡提耶-布列松認為攝影只是消遣,他認為自己本質上還是一個畫家。」』——他就是這麼一個志向為畫家的攝影大師。
書中還有提到一個我很喜歡的趣味故事:「有一次他(布列松)接受心臟手術,手術前他淘氣地要主刀醫生看看他口袋裡放了什麼書,答案是波特萊爾的《我心赤裸》」。
而對於走遍世界的布列松,也有個問題是:「你最喜歡的旅行是哪一次?」,他的回答是:「身為戰俘的三次逃亡。」曾經作為戰俘的遭遇,確實對他帶來了極大影響。
《二十世紀的眼睛》中鉅細靡遺展示了布列松的生長脈絡、經歷與許多面向,這個世人熟知的「新聞攝影大師」跟朋友之間的相處、爭吵,還有遭遇各種挫折的時刻,對攝影的各種堅持與對暗房作業的隨意態度,或是現在看來過於古板的各種理念也是——透過這本書,我們都得以看見更多布列松在頭銜之後的樣貌。
▌離開攝影
卡提耶-布列松在一九七〇年代決定離開攝影,奔向他心心念念的志業——繪畫。儘管他在攝影方面留下了那麼多的成就,他還是毅然決然與攝影訣別,也退出了馬格蘭攝影通訊社。但這不意味他不再拍攝了,只是不再從事報導攝影工作與接受肖像攝影委託。
實際上,布列松的許多同事、朋友或是相關從業人員難以諒解他,對他們來說他背棄了攝影,並且他直言不諱的性格同時繼續干涉著攝影界,他甚至提出攝影不是藝術,也有人說他不願承認攝影藝術,是想確保自己在無法定義的攝影藝術中維持自己獨一無二的地位。
或許換個角度觀看——攝影對他的藝術價值在他多年留下的成就之中已經再也難以突破,而他在繪畫的成就遠遠不及於攝影方面的成就,對他來說繼續磨練的畫技是深思熟慮的創作過程,按下快門則是他的自然衝動。為什麼對他來說不是藝術?或許是因為構圖早已成為他的本能。
不過這個觀點我覺得也同時能展現布列松期望破除的偶像思想——是因為他的身份所說的是正確的,還是我們認為那些話語是正確的。
「首先要擁有視角,技術手段只是用來傳達視角的工具,因此毫不重要,重要的是捕捉到人或事物的本質。」布列松從一開始想從事繪畫,到後來成為攝影師、拍攝紀錄片,最後又回歸到繪畫,都示意著這句話的本身意義。
曾作為布列松老師的洛特,在臨終前看了他的照片後說了這段話:「這些創作的養分都來自你做為畫家的養成過程。」
對於藝術創作我們總是習慣性地尋求理念,或是以更後設的角度賦予理念(或許如同我現在正在做的事)。我們能從布列松的照片中看到他對幾何與超現實主義的著迷,他的經歷積累讓他以一種自然的姿態去捕捉現實中的超現實。
越過那些象徵性的名家與歷史事件資訊,回歸到紀實、鑑賞或是解讀影像本身、捨棄對新聞攝影來說最重要的資訊之後,端看構圖、光影、幾何形狀、線條,圖像上的輪廓、黑白階調。
我覺得紀實的迷人之處即是能在這些構成的瞬間影像裡看見生命與生活的自然張力。
而卡提耶-布列松,或是任何的紀實攝影——都是提供我們一個觀看世界的方式。
我不是什麼專業攝影者,只是一個喜歡偶爾拍照的人(有時候還會嫌棄相機的重量)。但我想,我拿著相機站在路口,如果問我這張照片是怎麼拍的呢。我可能會說,因為所有時機都對了,但在擊發快門之前或是之後,在照片沖洗、放大在螢幕檢視之前,我也不知道自己拍到了什麼。
接下來,就是觀者的事了。

「被拍的人保留了自己一部分的臉孔,而攝影師則得到了他一部分的靈魂。」——《卡提耶-布列松:二十世紀的眼睛》
(文中使用照片與封面圖素材皆為自攝)
其實討論卡提耶-布列松的專業文章已經不少,我認為自己很難再提出有新意或深度的觀點與分析,但還是想為閱讀這本書的心情與想法留下一個記錄。
攝影大師的觀點很重要,但是那些藝術名家不斷出現的生活經歷、作為人的生活化細節也是值得閱讀玩味的地方。
註1
〈Nul ne peut entrer ici s'il n'est pas géomètre(唯幾何學家方可入內)〉1974
https://www.lemonde.fr/archives/article/1974/09/05/nul-ne-peut-entrer-ici-s-il-n-est-pas-geometre_2528131_1819218.html
註2
照片/《坦噶尼喀湖的三個男孩》(Three Boys at Lake Tanganyika)
https://iconicphotos.wordpress.com/2010/08/04/three-boys-at-lake-tanganyika/
註3
India and the Death of Mahatma Gandhi
註4
蒙迪亞哥(Mandiargues,另譯名為芒迪亞克)
照片/〈André Pieyre de Mandiargues〉Henri Cartier-Bresson 1932-33
https://www.moma.org/collection/works/54799
不重要的趣聞補充:蒙迪亞哥曾被懷疑為《O孃》筆名(Pauline Réage)背後的作者
〈Le Masque de chouette dans Histoire d’O : une étude sur Mandiargues et son « masque »〉
https://www.jstage.jst.go.jp/article/ellf/115/0/115_222/_pdf/-char/ja
Pauline Réage
https://leatherhalloffame.com/inductees-list/58-pauline-r%C3%A9age.html
註5
薩雅吉·雷(Satyajit Ray)
https://121clicks.com/articlesreviews/satyajit-ray-talking-about-henri-cartier-bresson/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04/aug/05/guardianobituaries.artsobituaries
註6
德爾皮爾(Robert Delpire)也是紀實攝影師羅伯‧法蘭克(Robert Frank)攝影集《美國人》(1958)的出版者。
延伸閱讀:
卡提耶-布列松部分攝影作品
https://www.magnumphotos.com/photographer/henri-cartier-bresson https://www.moma.org/artists/1000-henri-cartier-bres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