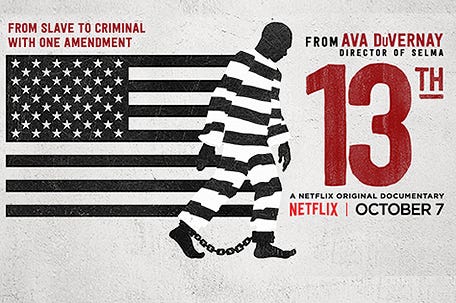[00:00:06] 主持人:今天想要先跟您談談美國之音的歷史任務和組織的來龍去脈。您最近 (Aug 22, 2020 ) 評論說:“美國之音的定調就代表川普化共和黨在競爭性排華時代的輿論導向。美國之音改組以前的導向,代表全球化時代兩黨建制派。……儘管美國之音理論上和大多數時間並不是執政黨的喉舌,而是全體建制派共識的宣傳機器,但在新舊建制交替的視窗期,卻會表現為首先接受新建制一方的喉舌,例如1948年的美新處更像民主黨帝國主義者反對共和黨孤立主義者的喉舌。”我們經常在看美國之音的報導,但是對它的歷史和政治任務定位其實並不熟悉,可以請您稍微再發揮一下這個議題嗎?
[00:01:13] 劉仲敬:美新處和美國之音都是被動的產物。宣傳這個概念,在美國的意義是十九世紀後期產生出來、然後擴散到英國和全世界的那種政治經紀人的廣告技術,它在美國人心目中是一種商業化的經營。專業化的廣告人員幹的事情不是意識形態擁護誰或反對誰,而就是消費者調查一類的東西。它會產生出像小布希時代的卡爾·羅夫 (Karl Rove ) 這樣的人,他的任務就是調查本區的政治消費者的各種傾向。像賣牛奶的人去調查哪家有幾個小孩、他們會消費多少牛奶一樣,做一個大致上的估計,然後你才可以確定你的生產和廣告。他的工作方式都是廣告商性質的,廣告商性質的宣傳在立場上是消極的,它不準備改變它的消費者構成,也不準備對消費者施加影響。所以在美國人的心目中,宣傳就是這個樣子的。
[00:02:25] 二十世紀才剛剛產生出來的這種新型的、由布爾什維克和納粹推行的宣傳,對美國人來說是非常陌生的。這種宣傳要求赤裸裸地 (像戈培爾所說的那樣 ) 建立一個自我完善的、閉環式的思維鎖鏈,把整個人的全部生活和思維都圈在一條鏈裡面。這種宣傳方法對於美國人來說是完全陌生的。他們首先接觸這一套的時候是1930年代,通過德國的統戰機構和林白 (Charles Lindbergh ) 這樣的孤立主義者對美國社會施加影響。包括運用美國社會的進步派的資源推行種族優越論,把種族優越論和雅利安主義跟人類學聯繫在一起,把它說成是一種科學的概念。而把像布萊恩 (William Jennings Bryan ) 所主張的那種反進化論的、基督教式的、傑弗遜式的民主說成是過時的、中世紀的遺留,在科學進步的新世紀註定會被納粹所代表的科學進步浪潮所淘汰。
[00:03:39] 用這種方式來培養支持者,然後產生了十九世紀的人還不怎麼熟悉、但是我們現在已經非常熟悉的那種不可說服的人,就是索爾仁尼琴描繪的那種在勞改犯的營地中被其他勞改犯嘲笑的老共產黨員。他面不改色地說,蘇維埃現在才只有幾十年歷史,犯一點錯誤也是很正常的。雖然他自己已經被“犯一點錯誤”搞進來了,但是他仍然對歷史進步的必然性和規律抱有極大的信心。儘管他周圍的那些文化不高的勞改犯都覺得這一套純粹是扯淡,覺得他是一個傻逼,但是他自己在他的思維閉環中是一點都不會改變看法的,是那種不可說服的人。這種意識形態方面的新人,人數是非常之少的,但是他們可以構成一個破壞性極強的硬核,用美國人習慣的那種常見的民主式方法是說服不了他的。
[00:04:36] 這樣的搞法就像是,你開著割草機,在一片有很多鐵片和荊棘的草地上,而你的割草機是為草設計的。開著開著,過不了幾下子,割草機的刀刃就要砍到鐵片上,必須把鐵片砍開,而平常你只是打算在草地上順順地開過去的。這樣的感覺是他們以前不熟悉的,這時候他們才多多少少意識到文宣的重要性,才產生出文宣機構。文宣機構跟二戰時期的美軍一樣,是帝國主義的產物和美國被迫介入國際社會的產物。同時,它也跟羅斯福新政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如果不是羅斯福新政的話,美國沒有這一套機構和人手。我們要注意,羅斯福新政產生出來的霍普金斯 (Harry Hopkins ) 和諸如此類的人,就是美新處和以後美國之音的階級來源。這批人在美國社會本身的地位是非常邊緣的。在羅斯福新政以前,他們也就是像紐約先驅論壇報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 和東部的各大報紙產生出來的那一小撮人,在二、三十年代的好萊塢B級片描繪的哈代法官 (Judge Hardy ) 那種正常的美國家庭和社區當中非常罕見,而且不像是成功人士。
[00:06:01] 比如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當了飛行員或者其他什麼,回了家,主要不是依靠他們的專業技巧,而是依靠他們在大學時期的同學關係或者在軍隊裡面形成的人脈關係,從事某種職業。這個職業對於他們來說主要的要求是有很多好朋友,而不是很有專業技巧。專業技巧這個東西像愛迪生和威斯汀豪斯 (George Westinghouse ) 所代表的美國工程師傳統那樣,不是像歐洲、更不是像東亞做題家社會那樣看你的文憑,而是基本上沒有什麼文憑要求,大部分技能是你在工作中學來的。你需要的就是,你的好朋友相信你,你也相信他們。在這樣的人際關係裡面帶一帶,你多幹兩年,自然就幹出來了。而那些新時代的、準備吃某一種思想飯的人,如果他還能立足的話,肯定也就是在紐約的大報或者出版社這些地方才能立足。難以想像,除了在東西海岸大城市的出版業以外,他們還有別的什麼生存機會。小地方的報紙,他們肯定是生存不下去的。
[00:07:10] 像奧哈拉 (John O'Hara ) 描寫的 (注:短篇小說“Ninety minutes away”,出自《The Hat on the Bed》 ) ,本地的紀事報 (Taqua Chronicle ) 有一個記者 (Harvey Hunt ) ,他在報導一次員警抓妓女事件的過程當中跟員警吵了一架,就帶著一個被員警抓的妓女 (Jean Latour ) 投奔紐約了。他是一個訓練有素的專業記者。小說中描繪說,他在本地的小報紀事報是很受器重的。老闆是想勸他,將來等我退休了以後報紙就交給你,希望你娶一個本地的好姑娘,以後就安定下來。但是他內心深處就有以撒·辛格 (Isaac Bashevis Singer ) 描繪的猶太知識份子和啟蒙自由主義者那種放蕩不羈的血,暗地裡並不喜歡辛克萊·路易斯 (Sinclair Lewis ) 的《大街》 (Main Street ) 描寫的平靜鄉鎮生活。因此他就找到了一個藉口,服從了自己內在的衝動。他知道他從員警手裡面救出來的那個妓女其實是一個非常壞的女人,一到了大城市肯定會拋棄他。他剛剛一走,就發現那個妓女偷了他所有的錢,然後揚長而去了。但是他絲毫不打算回去,因為這其實就是他內心的召喚。
[00:08:23] 那麼紀事報這樣的小報紙報導的是什麼呢?就是本地的日常生活。這些人對於他們來說都是彼此之間認識的人。這個跟大報紙報導遠方的事情、根據意識形態偏向來描繪好人和壞人是不一樣的,你描繪的人都是你最多一、兩個星期就要見到的人。你在報紙上寫了他什麼或者說了他什麼,就跟你自己在星期天的教會裡面說了誰的好話或者壞話一樣,你肯定知道過不了兩、三個月就會傳到他耳朵邊上。大多數美國人的精神生活是受這樣的小報報導影響的。比如說我看到的這樣的小報和地方報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報導的就是本地的子弟是怎樣回家的。這就是對於他們唯一重要的事情。而艾森豪將軍在蘭斯 (Reims ) 或柏林舉行的儀式只有一個邊角料。對於他們來說,本地最出色的划艇手死在馬恩河上了,他沒有跟戰友一起回家,這是頭等大事。而艾森豪將軍和杜魯門總統幹了什麼事情,柏林又發生了什麼事情,只在花邊和報欄中間淡淡地提一下。前者是他們認識的人,我的中學同學再也回不來了,我的一個中學女同學失去了她的丈夫或者男朋友,這件事情我是一輩子也忘不了的。我看著我的兒子長大的時候,忍不住要提到的就是這件事情。這件事情要伴隨他一輩子的。艾森豪將軍所做的事情,那是遠方的事情,跟我們沒有直接關係。
[00:10:14] 這樣的小報當然並不能夠滿足胸懷壯志、對於人類社會有一整套看法的霍普金斯這一類人,但是這一類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社會氛圍中是發不了財的。誰能夠發財呢?除了那些特別有天賦的人以外,一般的美國人發財是不需要特別有天賦的,只需要好朋友特別多。換句話說,你發不了財是因為你秉性乖戾,所謂的滾石不生苔,到處都交不到好朋友,你這個人怪怪的。人緣好、品行好、到處都有好朋友的人不需要很聰明。你待別人,別人也待你。花花轎子人抬人。在美國經濟長達百年的上升期當中,只要是跟大夥都處得好的人,是不可能不發財的。進步青年不能發財的原因,就跟小說家描繪的那個在地方小報混不下去的人一樣。你想,地方小報社的記者和老闆的區別是很小的,而且一個小鎮也沒有多少報紙。他只要肯混下去、真正娶一個本地姑娘的話,他就是本地的報社老闆了。那麼本地的報社老闆以及本地的警察局長、本地的法官、本地的牧師,這就是本地的寡頭精英集團了,他就是本地的第一流人物。按照他從紐約那些大城市學來的新聞技巧,他的專業能力是超過本地人的,所以本地的老闆才會重用他。他只要肯融入當地社會,比如說當地如果在南方的話,當時就必然是民主黨預選中間能夠左右選民的那幾個大佬之一。但是,這樣的生活在他看來比不上在紐約顛沛流離、租房子、住筒子樓、時刻都會被解雇的那種生活。
[00:11:55] 像依修伍德 (Christopher Isherwood ) 這樣的英國作家,他就說 (注:出自“Prater Violet” ) ,他唯一瞭解的就是這些浪人進步青年 (I didn’t know how anybody spoke, except public-school boys and neurotic bohemians. ) 。他佩服莎士比亞,因為莎士比亞好像有一種特殊的能力,無論他自己是什麼人,他寫貴族也好,寫教士也好,寫社會的各個階級也好,都好像很能進入角色。但是依修伍德發現,他自己寫的話,除了進步浪人青年以外,他根本不知道別人是怎麼說話的。無論理論上安排的角色是誰,這個人說出來的話都像是進步文學青年說的話,而不像是他們本來按照小說的安排應該說的那種話。就是這一撥青年,在新政時期,在霍普金斯的率領之下,在羅斯福政府中找到了機會,然後又把他們的進步理念傳播到全世界。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比如說在國民黨統治的重慶,在西南聯大這些地方,他們就是美國的化身。對於費孝通、四十年代的民盟和民主青年這些人來說的話,他們認識的美國就是美新處。他們並不知道,他們認識的美國在美國所代表的這個集團,在美國社會本身就是極其邊緣的。而且,如果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羅斯福新政的話,這批人就像是風中的柳絮一樣,會很快消失得無影無蹤,大家不會認識到他們曾經存在過。但就是他們,才是最適合 (很可能是唯一適合 ) 承擔文宣責任的人。
[00:13:35] 像《光榮與夢想》這本書,我發現直到不久之前它仍然是中國的大學教授們瞭解美國最喜歡的書。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大學教授們心目中的美國就是《光榮與夢想》的美國,就是甘迺迪的美國。這個美國跟佛蘭克林·羅斯福的美國是有傳承關係的。那本書上曾經寫到過,霍普金斯招攬的那些進步青年認為,有人說權力使人腐化,這是不對的,從霍普金斯和他的同道身上體現出來的是權力使人進化。他們懷著宗教式的熱情在忘我地工作,他們的使命就是在羅斯福政府推行新政,同時在世界上推行美國價值觀。美國以前是出過很多傳教士的,但是把美國民主當作一種宗教式價值觀推廣到全世界這件事情主要是由他們開始的。而他們在這件事情上找到了自身的存在感,否則在此之前,他們只是美國社會上極其邊緣的浪人。按照他們那種生活方式,他們是發不了財的。而那些留在紀事報裡面安安心心當記者、最後當上老闆的人,會變成普通的富裕中產階級的領袖。美國的有錢人,大部分是由這些人構成的。羅斯福政府經常說華爾街害了他什麼的,這一點並不符合事實,但是它卻反映了,為羅斯福政府工作的那些人是很窮的,主要收入都依靠政府部門的薪水。當然,這份薪水是不高的,比起比如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就到證券交易所去工作或者從事商業的人來說差得很遠。柯立芝曾經說過,商業才是美國的唯一業務。
[00:15:25] 正常情況下的美國人,就是進步作家所諷刺的巴比特那種人 (注:出自辛克萊·路易斯 (Sinclair Lewis ) 的小說“Babbitt” ) 。巴比特先生有一句名言叫做:大學不是你學東西的地方,而是你交好朋友的地方。這才是大學的本質和真諦。左派作家 (這個“左派”還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那種意義上的左派,而是二十世紀初葉的進步分子 ) 就把這種人描繪成為志得意滿、以為天下沒有誰比自己更正確的市儈。但是他們也承認,這種人是軟心腸的市儈,當他的好朋友被老婆欺負而出了事情的時候,他就感到非常心神不安。在他的生活當中,一個男人被兇悍的妻子欺負了,然後開槍打了妻子,就是他能夠預見的最大的重大事故了。巴比特是早晚會發財的。而六十年代越戰時期的“兔子” (Harry ‘Rabbit’ Angstrom ) 這樣的人,最後在他的晚年,在厄普代克 (John Updike ) 的小說中間,也變成了一個二十世紀末期進步主義時代的新巴比特式人物,搭上了冷戰時期黃金三十年經濟繁榮的便車,變得“兔子富了” (Rabbit Is Rich ) 。這些人共同的特點就是庸俗,至少在進步作家的眼裡面是庸俗的。
[00:16:41] 不庸俗的、胸懷鴻鵠之志的、有格拉古兄弟那種志氣的人只有去政府部門,他們在政府部門是不可能掙到很高薪水的。這一點就決定了他們對資本主義抱有不友好的態度。這個階級在羅斯福時代才剛剛開始,但是在費孝通這一類的人 (恐怕是在全世界的人 ) 心目中,因為是美國士兵把美國的形象帶到全世界的,除了可口可樂和娶本地姑娘的美國士兵以外,美國形象的主要締造者就是美新處這幫新聞記者,多半是新聞記者或者諸如此類出身的進步青年。我們都知道蘇聯和共產主義者的宣傳 (包括它在第三世界的宣傳 ) 是怎麼樣的。美國的冷戰當局顯然就認為有必要在第三世界國家抵制一下蘇聯的宣傳,所以才有美國之音這樣傳播美國價值觀的機構產生。但是他們傳播的美國價值觀對於比如說艾森豪時代占絕大多數的美國人口來說,恐怕根本不是他們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他們的價值觀。
[00:17:49] 他們把美國描繪成一個民主版的蘇聯。蘇聯人在全世界傳播共產主義,而美國人要在全世界傳播民主思想。在這一方面,其實他們的宣傳是不如蘇聯的,因為民主思想不是一個可以傳播的東西。民主是各利益集團為自身利益服務的工具。如果你居然要別人來教你如何維護自身利益,要遠方的美國人來替你維護自身利益,或者像南越那種情況一樣,你是為了美國人才打越南戰爭的,好像越共殺的是美國人而不是殺的你似的,這本身就是極其荒謬的事情。按說的話,民主這個東西是不應該像共產主義那樣作為宣傳的物件的,但是冷戰時期的宣傳戰就是這樣展開的。這就是為什麼蘇聯在宣傳戰中好像經常占上風的原因,因為民主不是一個適合宣傳的東西。但是,主要是民主黨統治時期培養起來的這些進步青年,在這種宣傳戰中間找到了自己的感覺。他們在真正的美國民主當中並不佔優勢,但是他們成功地使得包括今天中國的民小在內的人以為民主和美國就是他們宣傳的那個樣子,而這一點跟真實情況是非常不符合的。
[00:19:06] 從這個角度來講,他們的宣傳跟蘇聯對共產主義天堂的宣傳是一樣的。它給“宣傳”增加了我們今天的含義。不是說牛奶商雇傭的調查人員調查你們家有三個孩子還是四個孩子。本區的孩子很多,我開一輛霜淇淋車或者牛奶車過來是劃得來的,足以收回成本;如果本區沒幾個孩子的話,那算了,收不回成本。而是宣傳出一個與自己真實形象不符的形象,騙你上鉤。然後接下來的事情就不一樣了。等到始亂終棄那個環節不可避免來臨的時候,史達林同志就會把逃到蘇聯的希臘共產黨員乾脆殺光,而美國人這時候就做不出來了。他就會不得不覺得,在最後一天晚上撤出最後五千人當中的五萬人,把他們弄到美國去安居樂業,是他在道德上的義務。這樣一來就產生了一個極其荒謬的概念,就是說美國好像有義務把全世界由於建立民主失敗而無法實現民主的難民都弄到美國來,因為是美國教唆你們搞民主的,然後搞不成以後就得安置你們。這就是奧巴馬式的義務了,就是說美國原則上講有義務安置全世界六十億人口當中的一半。這顯然是不可實現的,於是又產生了美國道德虛偽和諸如此類的說法。這些事情其實全都是美新處這幫人在1948年被動被拖入冷戰的時候搞出來的。
[00:20:38] 我們要注意,冷戰最積極的人其實是美國的進步派、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人和布爾什維克。它不是像蘇聯人和今天的某些費拉右派所說的那樣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矛盾。純正的資本主義者或保守主義者對冷戰的興趣是消極的,但是問題是他們沒有辦法。像哈代法官這種人,在捲入了冷戰的時候,你能怎麼樣呢?他不能像羅恩·保羅那樣說我們不管。我們不管的話,人家都要打到你門口來了,似乎這也是違反道德直覺的。所以范登堡參議員 (Arthur Vandenberg ) 就在這個時候宣佈他放棄孤立主義,因為他誠實地看出孤立主義已經孤立不下去了。但是這樣就等於承認民主黨是正確的了。要知道,羅斯福政府干涉海外的動機,在阿爾夫·蘭登 (Alf Landon ) 那個時代仍然是共和黨反對的。民主黨、羅斯福、新政和福利國家的勝利,有一半是受國際形勢的推動。像阿爾夫·蘭登以及他的前身柯立芝和哈定所主張的,其實就是南北戰爭以後十九世紀末期的那個傳統的美國。我們好好做生意,依靠兩大洋的保護,不關心外事。這其實是美國的傳統政策和大多數美國人的希望。之所以實現不了,這是民主的一個最根本的、核心的弱點:因為人民並不是上帝,他們必須面對全世界人民都贊成卻實現不了、全世界人民都反對卻會實現的各種演化。
[00:22:06] 二戰以後的演化絕不是美國人民所希望的,美國人民根本不想到海外去作戰,但是卻被迫出現了不但要到海外去作戰、而且在美國士兵幾乎已經復員以後又需要集結幾百萬大軍到歐洲去的形勢。德國和法國已經被打爛了,組織不起像樣的防禦,而只有美國有足夠的人力。這些都是不得人心的事情,而民主必須負責去做到所有這些不得人心的事情。傳統的共和黨人在這種情況下完全失聲了。他們攻擊民主黨的那些事情,被證明是由於外部政治勢力演變而非做不可的事情。所以羅斯福才能連任四屆。如果沒有二戰的話,他連任兩屆就下臺了。而連任四屆的羅斯福,創造了美國冷戰的整個機器。儘管今天的費拉右派說羅斯福是左化的罪魁禍首,但是我們不要忘記,羅斯福政府創造的這套機器是美國有可能進行冷戰的根本,沒有他就沒有冷戰。沒有他的話,美國無法對抗蘇聯,沒有辦法作為一個帝國而存在。
[00:23:13] 從杜魯門總統的經歷,你就可以看出美國傳統的政治機器和作為帝國的美國之間的矛盾。杜魯門代表的是誰呢?他是南方民主黨人。直截了當地說,就是今天費拉右派當作共和黨基礎的聖經地帶白人的代表。在羅伯特·沃倫 (Robert Penn Warren ) 寫《國王的人馬》 (All the King's Men ) 的那個年代,共和黨在南方白人聖經地帶當中得到的選票跟亞伯拉罕·林肯得到的選票一樣多,也就是一張也沒有。各州當地的選舉是,民主黨的初選就是真正的選舉。投票日的新聞可以不看,因為民主黨內部競爭產生出來的候選人鐵定當選,那是民主黨的鐵票區。杜魯門就是這個鐵票區的代表,他是佛蘭克林·羅斯福的政敵。他的政見按照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共和黨極端保守派的政見。如果他和川普都倒回到1944年,他會認為川普代表進步派,而他是保守派。但是民主黨的政治機器是一個封建聯邦,東北部的新英格蘭的民主黨是不可能單獨贏得選舉的。
[00:24:28] 我們得回溯到南北戰爭以後共和黨長期執政的歷史。海斯 (Rutherford B. Hayes ) 的妥協和蒂爾登 (Samuel J. Tilden ) 的退讓 (Compromise of 1877 ) 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南方民主黨人和北方民主黨人結合起來以後就可以戰勝南北戰爭以後的共和黨了。而南北戰爭的爆發和民主黨的失利,歸根結底都是因為南方民主黨和北方民主黨的分裂。如果南方民主黨和北方民主黨仍然是一個黨,那麼林肯的共和黨和產生共和黨的輝格黨毫無希望在1860年獲勝。如果南方和北方的民主黨願意聯合起來擁護道格拉斯法官 (Stephen A. Douglas ) ,林肯永遠也當不上總統。就是由於南方民主黨和北方民主黨的分裂,少數派的共和黨才得以上臺。而紐約州州長蒂爾登在南方和北方的民主黨共同的支持下挑戰共和黨候選人海斯,實際上蒂爾登和克利夫蘭 (Grover Cleveland ) 就是道格拉斯法官在南北戰爭以後的翻版。南方民主黨通過支持東北部自由派民主黨,扳倒了共和黨,把美國政治又重新扳回到兩黨制的軌道上來。南北戰爭以後的二十年,似乎是只有共和黨人才能當上總統,像是光榮革命以後的英國曾經一度只有輝格党才會勝利那樣。
[00:25:53] 這樣一個格局,要求民主黨黨內實行封建諸侯的分贓制。這就是為什麼羅斯福的副總統每隔一屆都要換一個人。我們都知道,周王室東遷洛陽以後,上卿要由鄭國國君或者晉國國君擔任,總之是要由擁護周天子的幾個強藩擔任。這幾個強藩和它們的代表在洛陽擔任要職,是周天子獲得安全的根本。同樣,在紅白玫瑰戰爭中間,蘭開斯特家族必須要讓薩默塞特公爵 (Henry Beaufort, 3rd Duke of Somerset ) 在政府當中擔任要職。而薩默塞特公爵下臺以後,又要由劍橋伯爵或者其他伯爵來擔任,總之是由各封建貴族輪流坐莊才行。這就是為什麼杜魯門必須當副總統的原因。當然,羅斯福沒有料到,他死了以後,杜魯門一下子就當上總統了。杜魯門本人接管羅斯福的攤子,他就面臨著當時德國猶太人曾經說過的那種,當上總理的希特勒就不再是國社黨人了。這是根據他們的塔列朗式經驗所說的,你得以國家利益為重。這時候你當上了總統,就像是《是,大臣》那部小說和電視劇中所描繪的那樣,可憐的哈克根據他跟選民打交道的經驗進入部委,然後被偉大的韓弗理爵士和伯納德爵士玩得團團轉。後者雄辯地指出,我們全都是為了你好。你如果按照選舉之前的那一套,傻不唧唧地去搞什麼競選承諾,你混不了兩天就下臺了,選民也會拋棄你。我們才是你忠實的僕人,我們能夠把你送上首相的寶座,你只要聽我們的就好了。於是可憐的哈克爵士發現他鬥不過這些偉大的公務員,最後一步一步被對方牽著鼻子走。
[00:27:41] 杜魯門的情況也是這個樣子。按照他自己的選區來講的話,他對紐約人的東部海岸那一套和聯邦主義本身的敵意應該是比西部人尼克森更大的。但是他接了民主黨的總統攤子以後,他就必須實行冷戰政策。而這樣的政策要求美國政府在反對南方聖經地帶白人所支持的種族隔離方面發揮首要作用。一方面,美國現在是一個帝國了。它不再是一個瑞士,而是一個羅馬。它需要大量能戰的士兵,動員所有可以動員的兵源,包括黑人的兵源。黑人士兵的權利不再是可以忽視的了。另一方面,在宣傳戰方面,黑人問題向來是蘇聯宣傳的一個重點。美國國內推行廢除種族隔離制度最積極的這撥人,就是有國際經驗、在外交戰方面跟蘇聯打過對台的那些人。他們急於為了改善美國的國際形象,要過早地、在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解除種族隔離。杜魯門當了總統以後,在南方聖經地帶白人的眼裡面,他實際上已經背叛了民主黨的傳統。他們有封建主義的忠誠,封建主義的忠誠是有時間滯後性的。我報宗主之恩,不是報現任這個沒有出息的領主之恩,而是報我的祖先在德川家康時代得到的恩惠。雖然今天的將軍很沒有出息,但是我的祖宗受過老將軍的恩惠,我必須履行托孤之義,必須在把這個恩報完了以後才能夠有行動的自由。所以,附庸對宗主的報恩是有時間滯後性的。李將軍和克利夫蘭總統時代留下來的餘脈,可以保證羅斯福和杜魯門以後的民主黨繼續控制南方二十年。但是到了麥高文 (George McGovern ) 和韓弗理 (Hubert Humphrey ) 的時代,也就是詹森總統的時代,南方白人終於集體投奔了共和黨,於是今天的人反而以為南方聖經地帶的白人是天生的共和黨。
[00:30:05] 封建主義就像是查理斯·蘭姆 (Charles Lamb ) 在他的散文《拜特爾太太談打牌》 (Mrs. Battle’s Opinions on Whist ) 中所描繪的那樣。拜特爾太太是一位有趣的人。別人說打牌是一個娛樂,我在生活無聊的時候打一打牌,她聽了這話就不高興。她說,打牌才是我畢生的主要事業,如果不打牌,我活著幹嘛?她打牌喜歡打惠斯特 (Whist ) ,討厭打“誇德里爾” (Quadrille ) 。她說,“誇德里爾”爾虞我詐,充滿了馬基雅維利主義色彩的政治鬥爭,簡直就像是義大利城邦和雇傭兵隊長毫無信義的鬥爭;而惠斯特是需要穩定的結盟和好夥伴之間的高度信任,簡直就像是英法兩大國自百年戰爭以來的世仇一樣美好。封建主義就像是這樣,世恩和世仇。儘管我本人跟你無怨無仇也無恩無義,但是我要對他報恩,是因為他的祖先在南北戰爭的時候對我的祖先有恩,我要把你當作體面的敵人。什麼叫體面的敵人?我覺得你其實是好人,而且你也沒得罪過我,但是你的祖先在南北戰爭的時候是我的祖先的敵人。我為了做一個高尚的人,不能背信棄義,不能背叛祖宗和朋友,我要把你當敵人看。但是我確實覺得你是一個很體面的君子,所以我們之間的爭鬥就變成了紳士之間的鬥爭,變成了費厄潑賴 (Fairplay ) 的鬥爭。
[00:31:25] 費厄潑賴的前提是什麼?是封建主義。為什麼你們費厄潑賴得起來?我們不要神話英國人,英國人也是人。不要以為英國人天生是上等人,在生理結構上和荷爾蒙激素的構成上就跟下等人有所不同。英國人為什麼是上等人?我作為一個托利黨人,要對比如說哈利法克斯爵士這樣一個倒了黴的輝格黨人慷慨對待,因為我覺得他老人家實在是一個很好的人。但是既然他是一個很好的人,我為什麼不跟他合夥呢?那是絕對不行的,沙夫茲伯裡勳爵的祖先在當年砍查理國王頭的時候曾經投過贊成票,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這一點。而我的祖先在砍查理國王頭的時候是忠誠地逃亡到法國去的。儘管這個事情已經過了一百五十年或者更多年,但是我不會背叛我的祖宗和自己人。我永遠是一個托利黨人,他永遠是一個輝格黨人。但是,要我對他下手,這是辦不到的,因為他確實沒有做什麼不對的事情,我只能跟他費厄潑賴了。但是如果是當年正在砍查理國王頭的那個時代,或者是血腥瑪麗正在把新教徒扔進海裡面淹死的那個時代,那完全不是這個樣子的。當時我的祖先碰到你的祖先,是肯定會直截了當地殺過去的。為什麼我們之間的舊仇會變成費厄潑賴呢?因為封建主義的緣故。我不是報我自己的仇。我的生理結構和荷爾蒙讓我在殺你的時候感受不到肉體的快感,直截了當地說就是這樣的。我是出於道義和榮譽感才必須反對你的,因此我反對你的方式就是非常紳士的。這就是費厄潑賴的真正來源。
[00:33:15] 美國南方聖經地帶白人在杜魯門時代就是這樣含淚投票擁護民主黨的。這時的民主黨享有一個特殊的優勢:它擁有今天我們熟悉的民主黨在進步主義和帝國主義方面得到的新選民,同時又沒有失去南北戰爭以後僅僅為了他們祖先傳下來的記憶而擁護民主黨的舊選民。林肯等於共和黨,共和黨等於林肯。一看到共和黨這個詞,就想到萬惡的林肯和亞特蘭大的熊熊大火 (Battle of Atlanta ) ,條件反射地燃起了憤怒。這撥人還能繼續效忠它。但是等到越戰時期,民主黨候選人麥高文和韓弗理公開支持那些打砸搶的左派的時候,他們終於忍無可忍了,背棄了民主黨,改投共和黨的選票了。美國之音也好,美新處也好,都是二戰後期和冷戰時期美國進步主義者、國際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這批進步青年搞出來的機構。他們在全世界依靠美國國力 (我們要注意,美國國力的絕大部分並不依靠他們 ) 傳播的價值觀,從事的宣傳戰,以及把美國人拖入了他們本來不必承擔的各種義務當中,都是由這一撥人搞出來的。他們本身是水上的浮標,他們代表了美國選區政治和封建政治的重新組合。
[00:34:42] 在1948年的時候為什麼杜魯門能夠贏?當時杜威以為自己是贏定了的,報紙上甚至登出了杜威戰勝杜魯門的新聞,結果出來以後發現居然是杜魯門贏了。杜魯門當時的民主黨是很想推舉艾森豪做候選人的,但是艾森豪表示他老人家不想參政。後來他參政的時候,他決定做共和黨的候選人。可見民主黨自己也不覺得杜魯門這個地方性人物能夠取勝。按說的話,杜魯門是本州最精明的人,但是他對華盛頓應該是水土不服的。按照舊時代的美國,他會認為做一個資深參議員或者本州的州長對他更好一些,也更有利於他積累政治資本、為他的選民服務,是不會做總統的。但是由於他是羅斯福的副總統,他已經參加了國際會議,全世界都認他,這樣就迫使他繼續參加一場好像沒有希望的選舉。而這場選舉之所以能贏,其實就是出於上述的因素,民主黨在當時還能左右逢源。以及更重要的就是,共和黨沉溺于柯立芝和阿爾夫·蘭登時代的舊世界。那個世界是林肯和格蘭特將軍的世界,美國人在兩大洋的保護之下悶聲發大財的世界。他們對於美國扮演帝國主義者的角色非常不適應,提不出什麼方案。他們在佛蘭克林·羅斯福時代攻擊民主黨的理由,現在看來反過來都變成了民主黨有理由當政的理由。
[00:36:19] 當你的對手提不出有效的解決方案的時候,無論現任政府的解決方案多麼糟糕,它都會變成唯一必要的解決方案。應該說,1944年和1948年的共和黨還沒有從阿爾夫·蘭登的失敗當中緩過來,還沒有能夠提出新的方案。這時唯一提出國際性解決方案的就是民主黨,它就體現為羅斯福和杜魯門政府連續執政六屆的長期民主黨專政。這個長期民主黨專政跟林肯和格蘭特將軍開創的南北戰爭後的共和黨長期統治一樣,是塑造美國冷戰時期性格的一個關鍵。十九世紀後期美國的性格是由南北戰爭以後的共和黨長期專政所塑造的,後來克利夫蘭和捲土重來的民主黨不得不適應共和黨人已經建立起來的這個建制。而冷戰時期恰好相反,是羅斯福和杜魯門的民主黨建立了冷戰建制,而艾森豪的共和黨必須接受和適應冷戰建制才能捲土重來。
[00:37:25] 我們要注意,阿爾夫·蘭登時代的共和黨以為世界還是柯立芝總統時代的世界,他們可以打著柯立芝總統的旗號打敗佛蘭克林·羅斯福,捲土重來,而他們輸得很慘。1944年的共和黨和1948年的共和黨還沒有從阿爾夫·蘭登的失敗當中緩過來。他們已經知道柯立芝的綱領是行不通的,但是新的綱領應該是什麼?他們拿不出新的綱領來。沒有綱領的共和黨是贏不了的。於是,他們在1952年推出了艾森豪。艾森豪的綱領是一個溫和版的羅斯福綱領,共和黨的捲土重來意味著共和黨的投降。如果我們用雜文家那種只顧“語不驚人死不休”、不顧公正和比例感的方式描繪的話,那麼艾森豪在1952年的勝利就是民主黨從內部接管了共和黨,是共和黨對民主黨的投降。艾森豪本來是很有可能在1948年當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的,是他自己不幹。如果他願意幹的話,杜魯門本人都願意把總統讓給他。從這你也可以看出,他的政見絕對不是傳統共和黨人的政見。而共和黨人經過了一連串的失敗以後認為,只有讓這樣的人出來當領袖才能夠獲得成功。這就像是,社會民主黨發現,只有修正主義者才能領導社會民主黨執政,只有社會主義黨派內部的資本主義者才能讓社會黨執政,是一個道理。
[00:38:53] 當然,倒退一下時間,克利夫蘭和蒂爾登是什麼呢?他們至少是南方民主黨人向共和黨人的體面投降。他們放棄了南方獨立和維護南方特殊制度的主張,等於實際上是放棄了導致南北戰爭爆發的南方民主黨人的所有主張,才使得民主黨重新執政。民主黨在蒂爾登時代的復興和在克利夫蘭時代的重新執政,是民主黨人發現只有名義上反對林肯、而實際上執行林肯政策的民主黨人才能夠把民主黨人帶回白宮,就跟只有名義上擁護社會主義、實際上執行資本主義政策的社會黨人才能把社會民主黨送上總理寶座是一個道理。當時是民主黨,1952年是共和黨。冷戰時期的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鬥爭,是民主黨人和民主黨化共和黨人之間的鬥爭。艾森豪和尼克森執行的都是淡化版的民主黨政策,他們並不準備廢除帝國主義或者取消福利國家,只是打算在枝節問題上弄得稍微溫和一點。當然,英國保守黨也是這個樣子的。我們不能認為麥克唐納 (Ramsay MacDonald ) 、艾登 (Anthony Eden ) 或者威爾遜的政策跟卡拉漢 (James Callaghan ) 有十分明顯的區別。柴契爾夫人以後保守黨和工黨又顯得有明顯區別這件事情,在1945年到1979年這段時間是不存在的。邱吉爾之所以在戰後失敗,跟阿爾夫·蘭登在美國失敗的原因也是一樣的,就是因為他適應不了這個新環境。而艾登卻是可以的,艾登是保守黨的轉型者。艾登以後希思首相 (Edward Heath ) 的保守黨就已經跟工黨的區別很有限了。
[00:40:52]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民主的虛偽性。民主在什麼情況下才能夠有效運轉呢?答案就是,兩個主流政黨只在細節上有差別。這也就是秦暉所說的那種共識政治。保守派政黨和左派政黨的差別在哪裡?它們征的稅比左派政黨征的稅要少4.5%。這是秦暉說的,我沒有查看過它的來源。他的意思就是,歐洲大陸的左派和右派主流政黨的差別就在於,右派政黨上了台以後,各方面算總帳要減掉4.5%的稅。就爭這一點。你不可能是為了僅僅4.5%的稅去跟別人拼個你死我活,4.5%的稅不足以造成這樣的深仇大恨,所以共識政治就這樣運作了。共識政治下的兩黨,實際上正如馬克思主義者正確指出的那樣,是同一個資產階級利益集團的兩個不同俱樂部,只有一點點細節上的分歧。民主政治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能運行良好。如果存在著深刻的、需要砍人頭的那種利益分歧,比如說清教徒在克倫威爾時代所面臨的那種我要殺你、你也要殺我的情況,對不起,廣大民小和田園保守主義者絕對神吹的英國紳士精神立刻就不見了,最安全的辦法還是砍掉你的腦袋。對不起,英國人可以在以前紳士,在以後紳士,但是在這個時候我們還是暫時不要那麼紳士,先以砍頭為重點,砍完了以後我們再紳士也還來得及。這就是臺灣不適合民主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臺灣的政治鬥爭是屬於克倫威爾式的政治鬥爭,它不屬於那種4.5%的稅收鬥爭。
[00:42:37] 這樣一來,教條主義的費拉右派就會得出很荒謬的結論。比如說,民進黨是不是左派,國民黨是不是右派?至少國民黨的“財經幫”是不是右派?因為他們實行的是自由主義和親企業的經濟政策,他們不是跟大財團有密切的關係嗎,所以他們應該是右派,民進黨應該是左派。但是保守主義在其他方面又有一些定義,比如說依靠政黨統治國家的党國機制又是左派的一個特徵,那麼國民黨到底是左派還是右派呢?因為它是一個列寧黨的政黨機構,所以它應該是左派;因為它跟大企業集團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所以它應該是右派。那麼國民黨到底是左派還是右派呢?從理論上解釋不清楚,從統戰角度上你就可以上下其手了。如果你要反對國民黨的話,你就說,國民黨是左派,請你反對它,因為它是列寧黨,不反對能行嗎?如果你要擁護它,你也可以反過來說,國民黨是右派,因為國民黨有“財經幫”,所以你要支持它。但是同時,你如果要把統戰的立場顛倒過來,你也可以把相反的說辭再搞一下。
[00:43:45] 這樣又涉及到後冷戰時代的另一個因素,這個因素其實在冷戰時代以前,在“一無所知黨”針對愛爾蘭移民那個時代就已經存在了,就是外來的種族集團漸次融入美國。這個機制在冷戰時期一度淡化,但是在後冷戰時期又漸漸強化起來。新來的種族集團總顯得像是左派,因為他們摸不著原有政治機器的竅門,沒有相應的政治經紀人集團,因此它顯得像是反體制的。這時候就有坦慕尼俱樂部那樣的腐敗政治家出來充當這個溝通作用,可以收割一大批選票。但是在傳統的保守派看來,這是破壞美國的政治傳統。但是這樣的新來的政治集團早晚會像甘迺迪時代的天主教集團一樣,變成美國建制派的一部分。這是由於封建性的本質造成的。美國兩黨缺乏意識形態上的分野,它們是各地方封建集團的聯盟。而總有一個時期,比如說南北方的民主黨認為我們可以為了打倒共和黨人而重新修改一下封建聯盟的版圖,做諸如此類的行動。
[00:44:54] 這也是美國很難出現第三黨的原因。每一次出現第三黨,比如說十九世紀的人民黨、二十世紀初葉的進步黨以及不久之前奧巴馬時代的茶黨,它只要規模達到可以橫跨幾州的封建集團,可以擁有大批選票,那麼它就像是豐臣秀吉時代的一個諸侯一樣。有資格上洛的天下人就感到,這些沒有野心上洛、也沒有實力上洛的地方級諸侯是我收編的對象。如果我不收編,讓我的敵人收編了,那我他媽的豈不是吃虧?像德川家擁有關東的一大片領地,而他是一個很保守的人,不覺得他有資格跟織田信長或者今川義元一起上洛,這就好辦了。我是只跟上洛的天下人競爭的,而你只想在地方上當一當諸侯,我們之間並沒有你死我活的矛盾,希望你加入我們的陣營。蓬佩奧國務卿其實就是茶黨的人,他們很容易被共和黨收編的。而人民黨和進步黨以前的情況也是這樣。
[00:45:58] 在意識形態壁壘比較強的地方,在黨務工作人員已經形成利益集團的情況下,它是不會管意識形態和選舉版圖的。我不能讓我們原來的敵人騎在我們頭上。“什麼?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反革命。專制國家的毛澤東可以這樣,而我們是民主國家。我們要讓你明白,領袖並不能夠騎在我們頭上,我們不會容許領袖這麼幹的。”因此,新生的政治力量只能自立新黨,新黨就會漸漸產生和壯大。但是美國各政黨是沒有常務黨務工作者這回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機構都是臨時湊合起來的,所以他們沒有這樣一個利益集團。因此,勃艮第公爵和奧爾良公爵跟圖盧茲伯爵之間是可以隨時合縱連橫的。勃艮第公爵隨時可以跟英國國王結盟,也可以跟佛蘭德伯爵結盟,也可以跟馬克西米利安皇帝結盟,也可以跟法蘭西國王結盟,這都是現成的事情。共和黨和民主黨也無非是跟我一樣的幾個封建集團,我們改變我們原有的結盟版圖就足夠了。進步黨人希歐多爾·羅斯福是可以做共和黨的總統的,茶黨的蓬佩奧也是可以做國務卿的,將來也是可以做共和黨總統的。這裡面並沒有任何原有的老黨員的障礙。這個就跟羅森堡公爵和勃蘭登堡伯爵都可以做神聖羅馬皇帝是一個道理。你們都是大諸侯,神聖羅馬皇帝由你們輪流做。杜魯門就是民主黨人的這樣一個大諸侯,民主黨另外搜羅其他幾個大諸侯也不是什麼很成問題的事情。所以,新生的政治版圖很容易以諸侯的方式,跟兩黨內部原有的其他諸侯合縱連橫一下,就變成兩黨的一部分。而兩黨本身都是沒有固定的意識形態的,這樣的封建性聯盟也就不會有任何問題。
[00:48:02] 順著這樣的版圖一路演化下去,就變成,新興的移民集團可以根據他們原先在歐洲和本土並沒有什麼關係的符號進行聯盟,比如說愛爾蘭人和義大利人可以結成天主教集團。他們在十九世紀的美國,就是今天的奧馬爾 (Ilhan Omar ) 和AOC。他們不能融入當時的政治機構,通過腐化美國的方式在美國取得存生。我們要注意,在甘迺迪時代,他們是民主黨人。民主黨意味著反建制派進入建制派的一個中轉站。然後在甘迺迪以後,他們變成了共和黨人和保守派,反而比新英格蘭舊的清教徒更加保守。現在的最高法院的天主教法官,多半是他們產生出來的。但是如果何清漣在十九世紀的話,肯定要把他們說成是不可救藥的左派。建制派和左派是有一定的共性的,就是說他們都有破壞性。但是關鍵的區別在於,他們有沒有自己的社區。如果有社區的話,他們的集團是會不斷衍生的,衍生出他們維持自己社區的倫理。這跟舊的清教徒的倫理可能也只是大同小異,因為維持家庭和維持鄰里關係所需要的道德觀本質上都是差不多的。最終他們會在下一次政治衝突中,例如六十年代左派大暴動的時期,突然發現,有產階級的階級共性高於一切,然後就變成了保守派。在這個時候,突然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傳統區別變得一點都不重要了。你也可以設想,有朝一日,甚至可能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有產階級的區別也會變得毫不重要。
【15000字到此為止】
【本文完整版共20600字,剩餘5600字的內容以及完整視頻,請加入劉仲敬文稿站 (lzjscript.com ) 會員進行觀看。
如已經購買會員且登錄賬號,可以直接點擊下面的鏈接閱讀完整文章並觀看視頻:
https://www.lzjscript.com/archives/5862
如遇到任何付款方面的問題,可以在推特私信聯繫 @mhb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