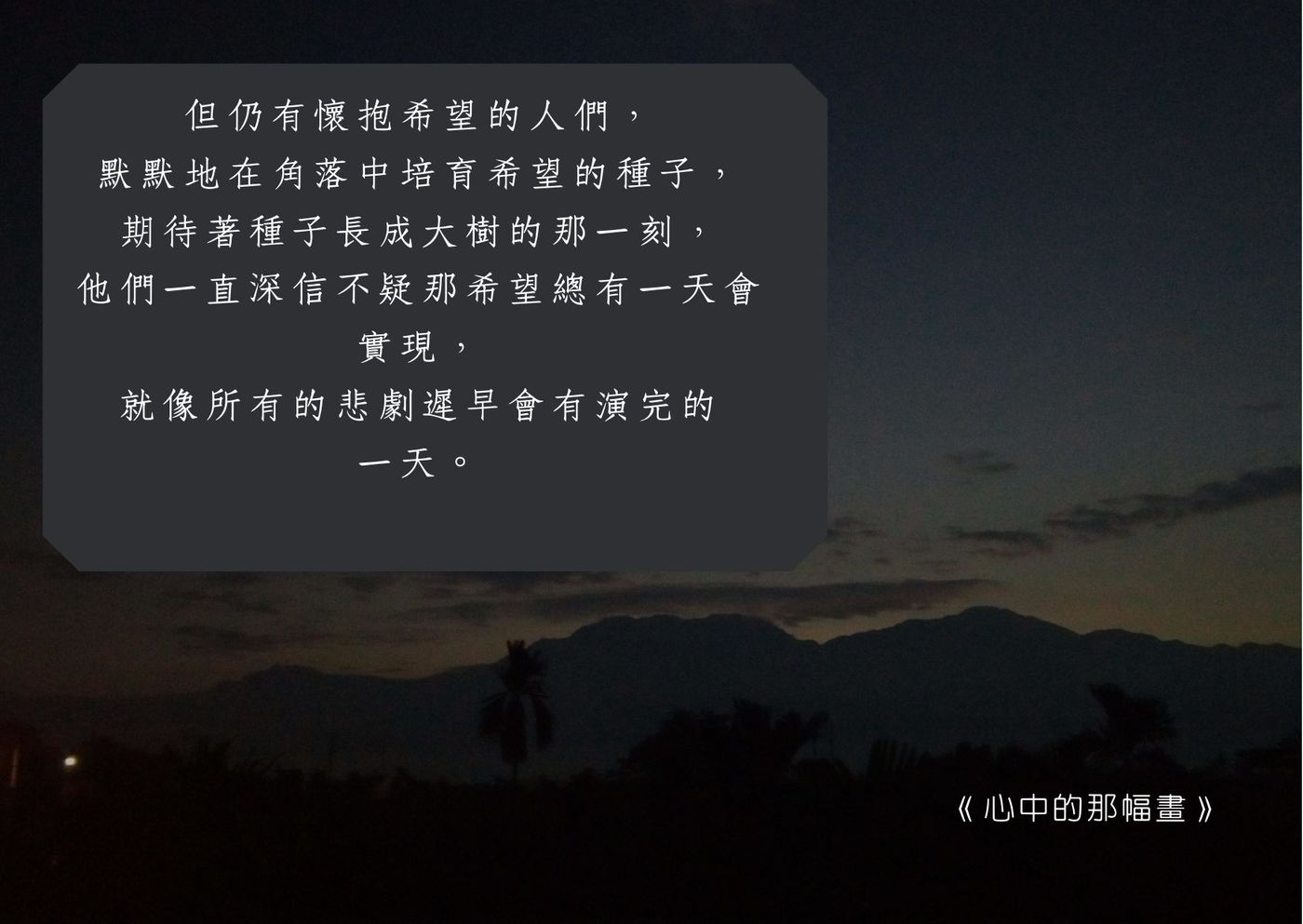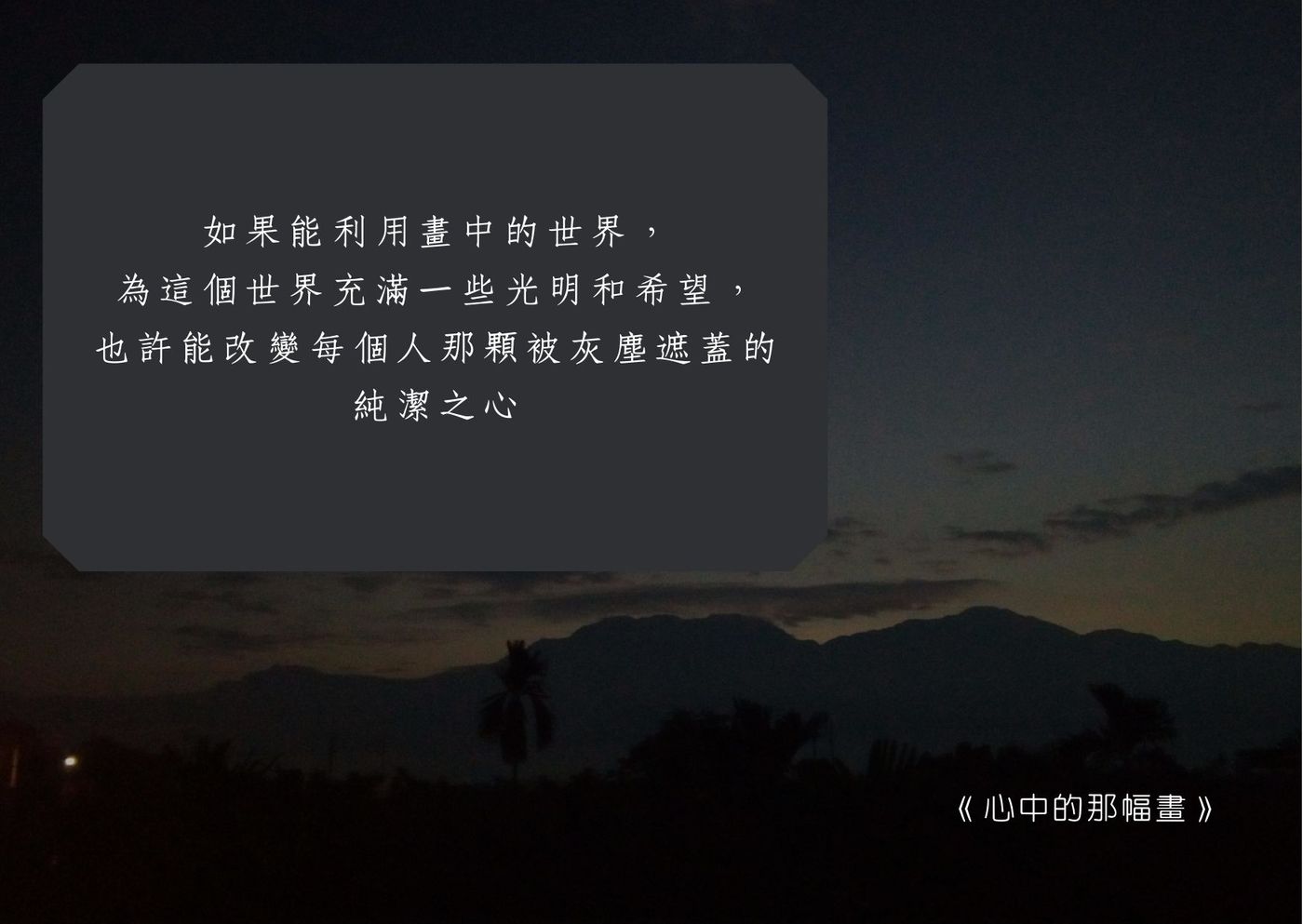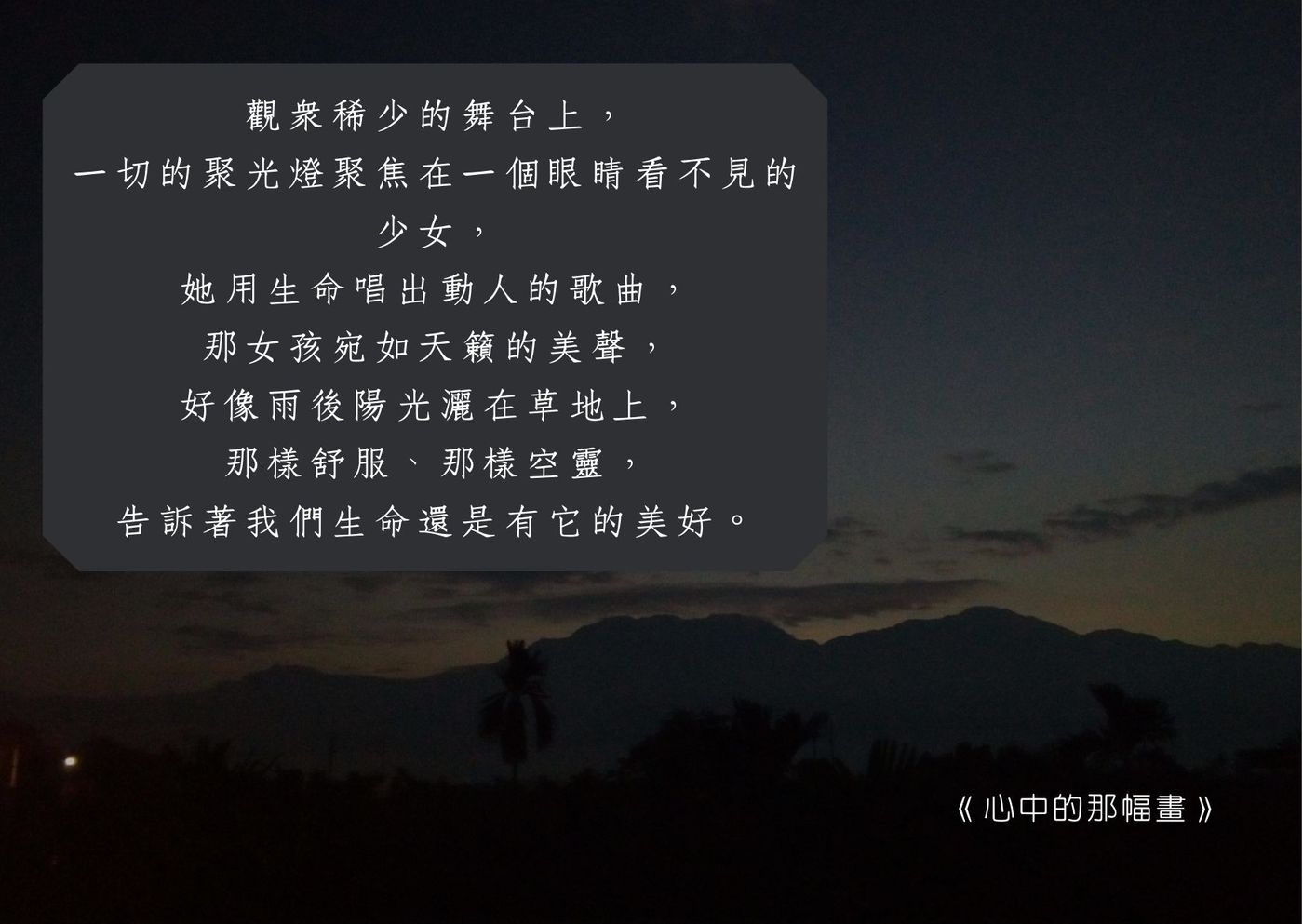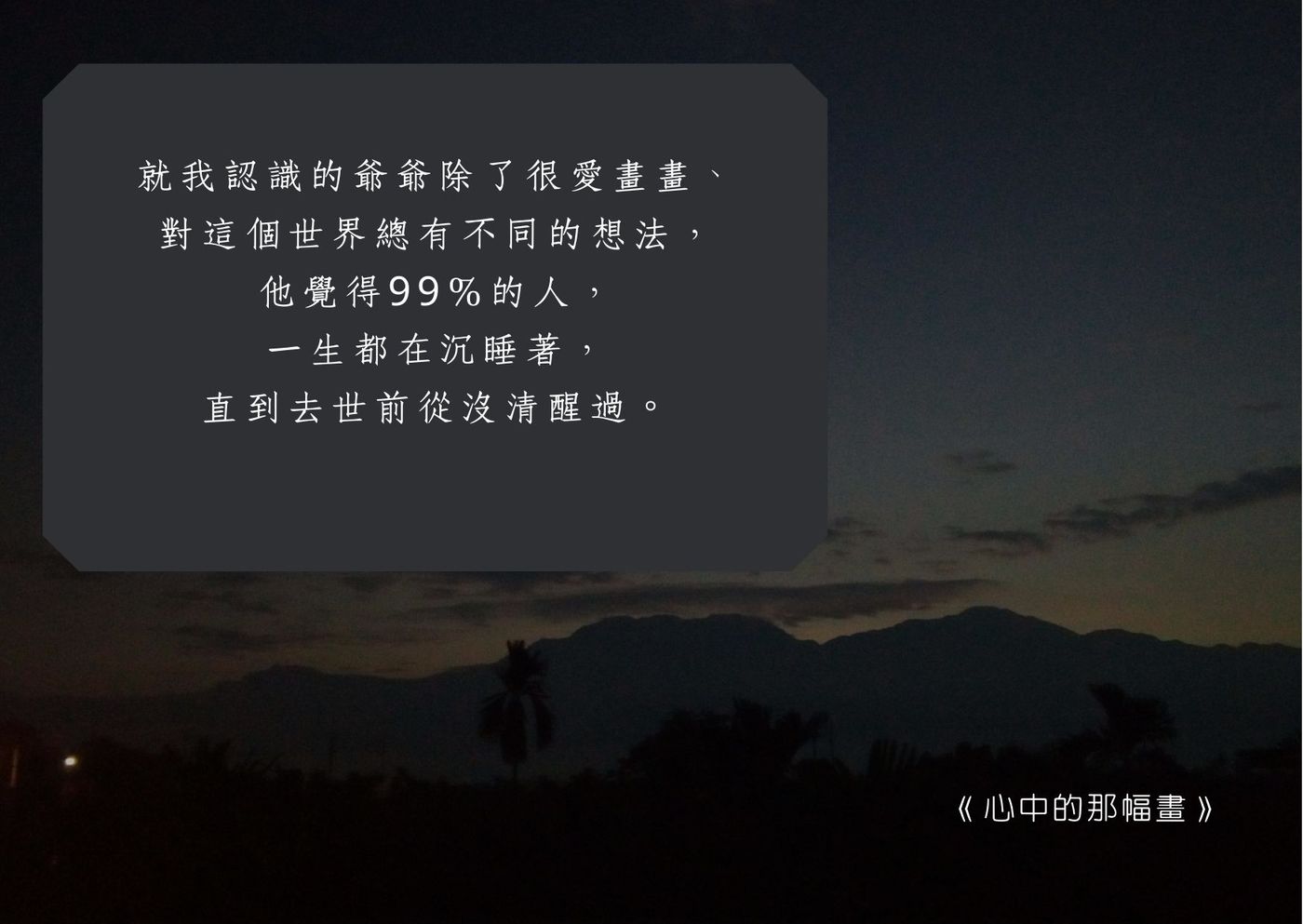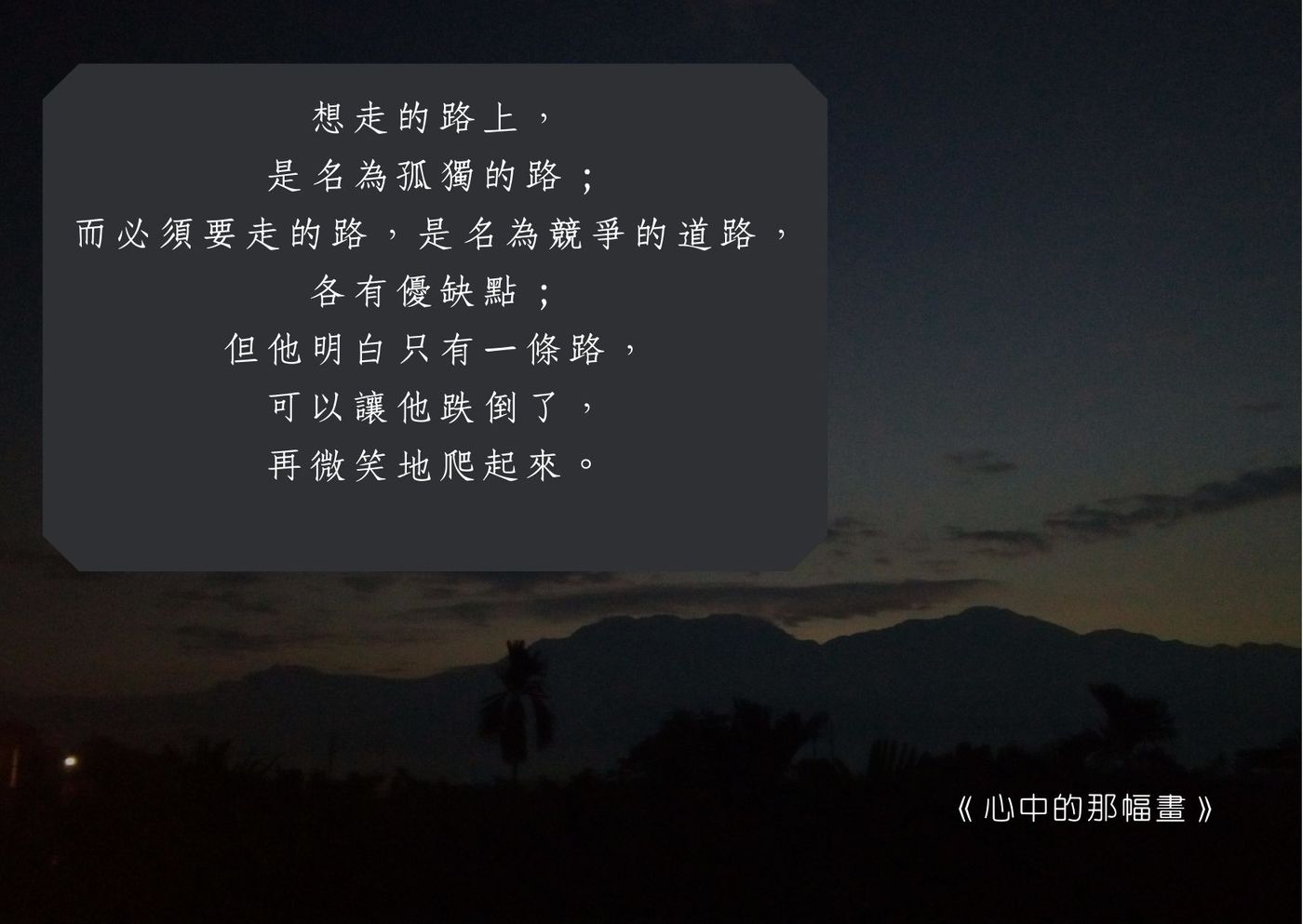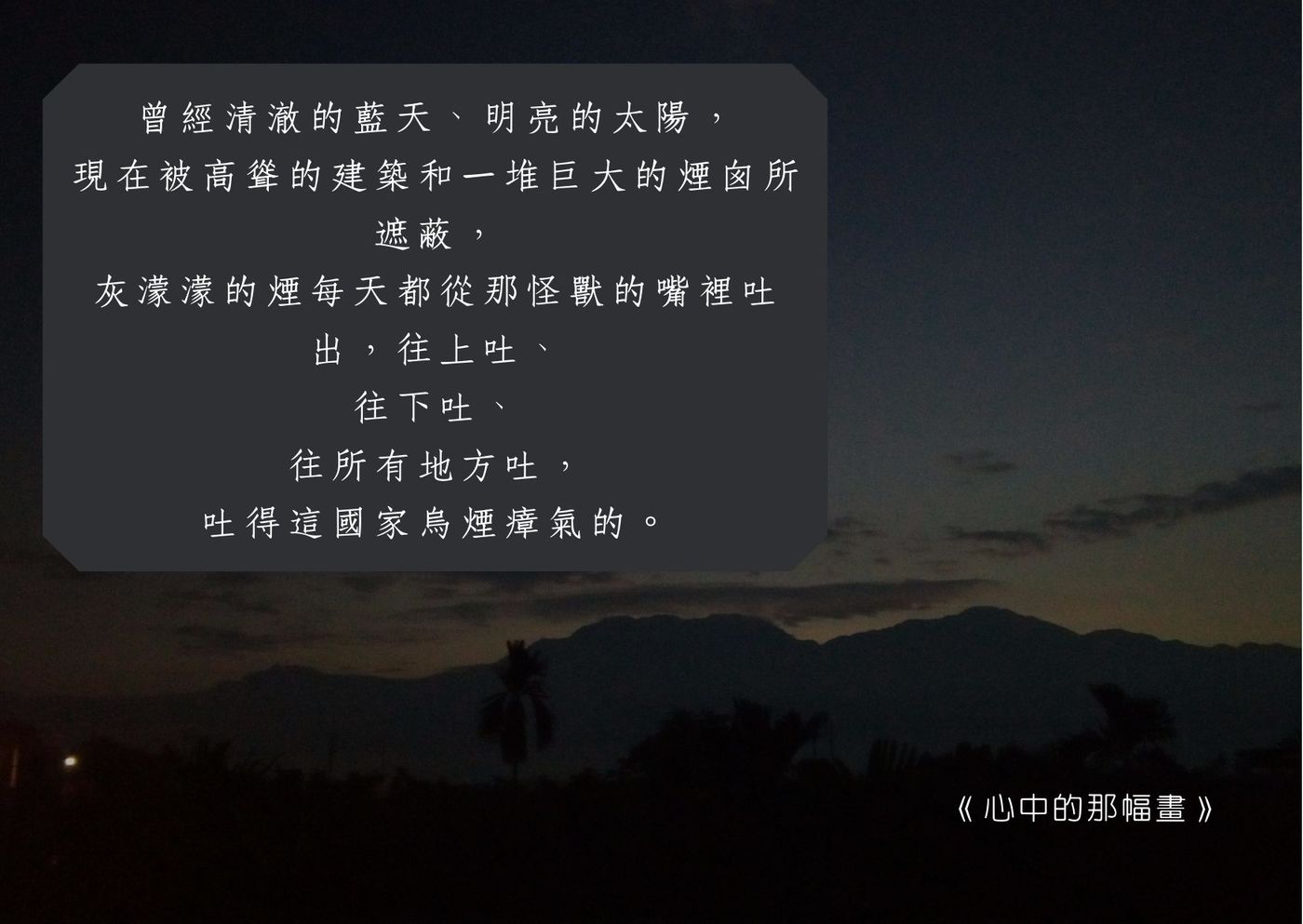为什么别人在生活,而我在生存?一个学生曾经这样发问,看着他紧蹙的眉,愁苦的脸,一时语塞。生存和生活,这是太过沉重的话题啊!
临窗呆坐,看雨后的天空,一束光愣头青一样突然穿过云隙直直的刺下来,金色的光清澈而洁净,又那么倔强充满活力,让我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人。
三十多年前,我们曾在同一个美术班学画。那时我刚刚学持画笔,他已经可以画出令人惊叹的波塞冬了。后来,我改学文学,毕业后做了很多年记者,接触过很多画家,但在我看来,对绘画能那么痴迷、那么狂热的,却仅他一人。早年在他简陋的画室曾见过第一个真正的人类头骨,放在一个铺着红色绸布的雕花木盒里。他说,那是为了画好头像,从古墓中挖来的。那时他总是饥肠辘辘,每天只吃两餐,每餐只有一个馒头,所有的生活费都用来买了画纸和颜料了。
那是我还很年轻,学画不过是票友,不懂很多东西,包括他的疯狂。但依旧看得出,他的画笔是灵动的,每一笔都像是在倾诉,每幅画都美得令人窒息。老师也说,这孩子是个天才。
但画笔无法改变命运。那年他专业课考分很高,却没能通过文化课考试,做村长的父亲希望他回家过平静的生活,种种田,或者找一份工作,养家糊口,生儿育女,赡养父母。他说,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他说,他很痛苦。
高考之后,我们都忙碌着登上这辆或那辆车,奔向自己的未来。他的痛苦如窗外吹来一阵风,从耳边划过们,也就消失了。
再见到他,我已大学毕业。那年暑假,闲极无聊去参加柏林禅寺的生活禅夏令营。在寺院身处,一个身着土黄色僧衣的熟悉身影正在扫地,他已做了俗家弟子,负责打扫寺院,类似于预科班的学生。他还是老样子,脸上、手臂上、僧袍上沾着油彩颜料,但一张脸似乎灵动了,有了笑容,快乐的笑容。诵经打坐间隙,常会跑去和他闲聊几句。他说,没关系,我要做绘画最好的僧人。那一刻,他眼里闪动着火焰,希望的火焰。
那时曾欣喜的想,他终于找到了逃脱的方式,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去活了。但没过多久就听说,他被家人发现了,一家人出动,在寺院里又哭又闹,他在僧房里绝食反抗,父亲拿出一根绳索,说,要么拴着他回去,要么自己吊死在佛塔上。他终于还是回去了。据说,很快就结婚了,生活很安稳。
又过了好多年,去山中采访,恰好路过他的村庄,特意停下车去看望他。
找到他竟然如此容易。一进村就看到一个熟悉的瘦削身影,他佝偻着背,戴着满是油渍的围裙站在街角的大黑锅前,在炸油条。
看着那双握画笔的手熟练地揉面、切面、搅动油锅中的油条,然后过秤,然后卑微地点着头、微笑着接过三两元纸币并目送客户离开。是的,他在微笑,他依旧可以微笑,但眼睛里再也没有了火焰,没有了光,木讷的硬壳,遮住了所有的表情,鼻翼两侧两条深深的沟,像经年流淌的泪水。
心,疼了一下,又一疼了一下,险些落泪。
结局早已注定,无论该庆幸还是悲伤。最终只是远远地看着,没有去见他,我想他一定也不想再见到我们和那些与画笔相关的往事。
我一度相信与天下父母一样,他的父母也对他也有着浓得化不开的爱。但,这份爱也太沉重、太坚韧,足以将一个天才扼杀在琐碎里。我一度不停地替他追问,当爱变成了一条系在颈项上的绳索,当绳索越收越紧勒进皮肉,那还是爱吗?
又过去了很多很多年,久得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但依旧记得他笔下的波塞冬,记得他的画带给我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