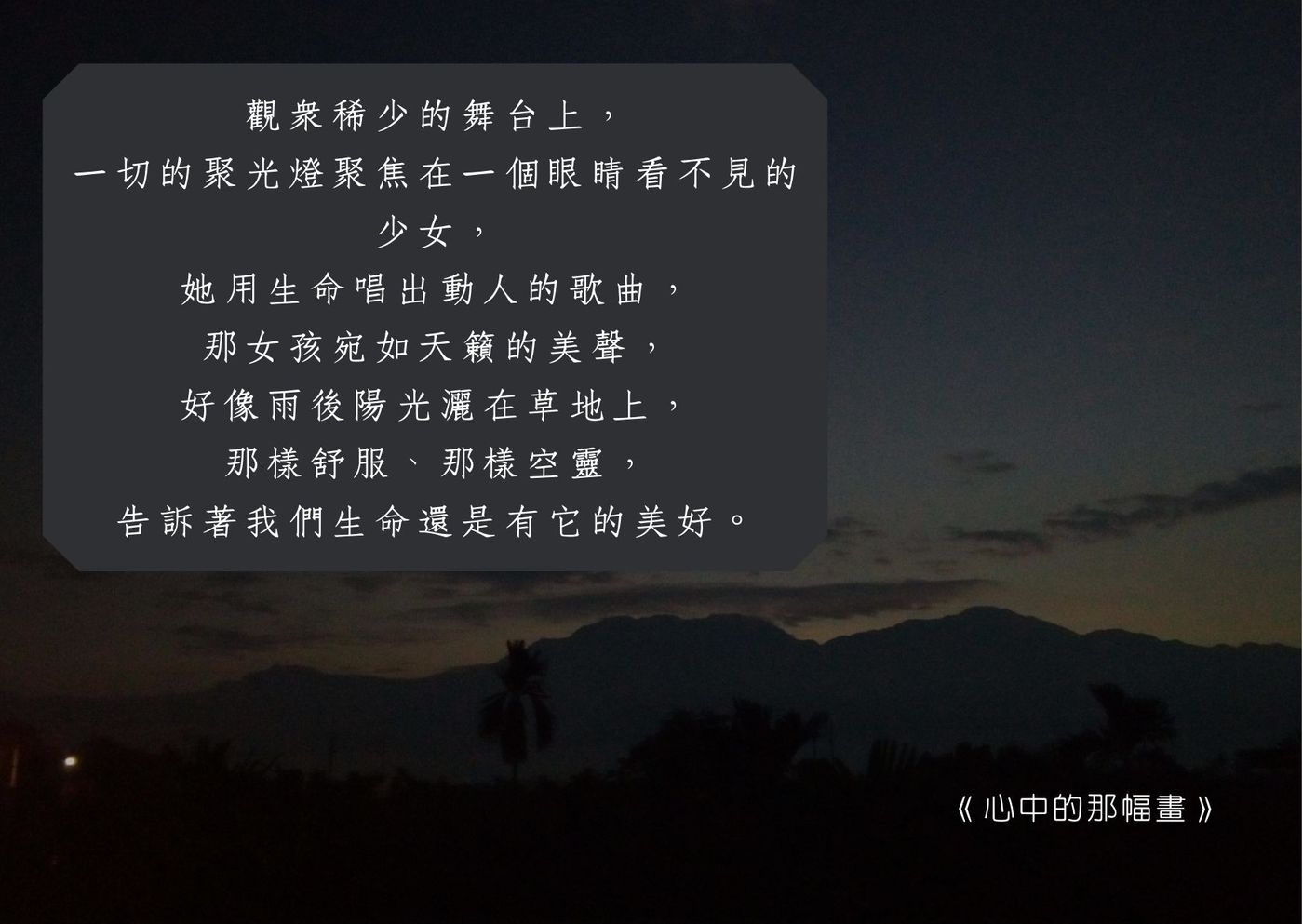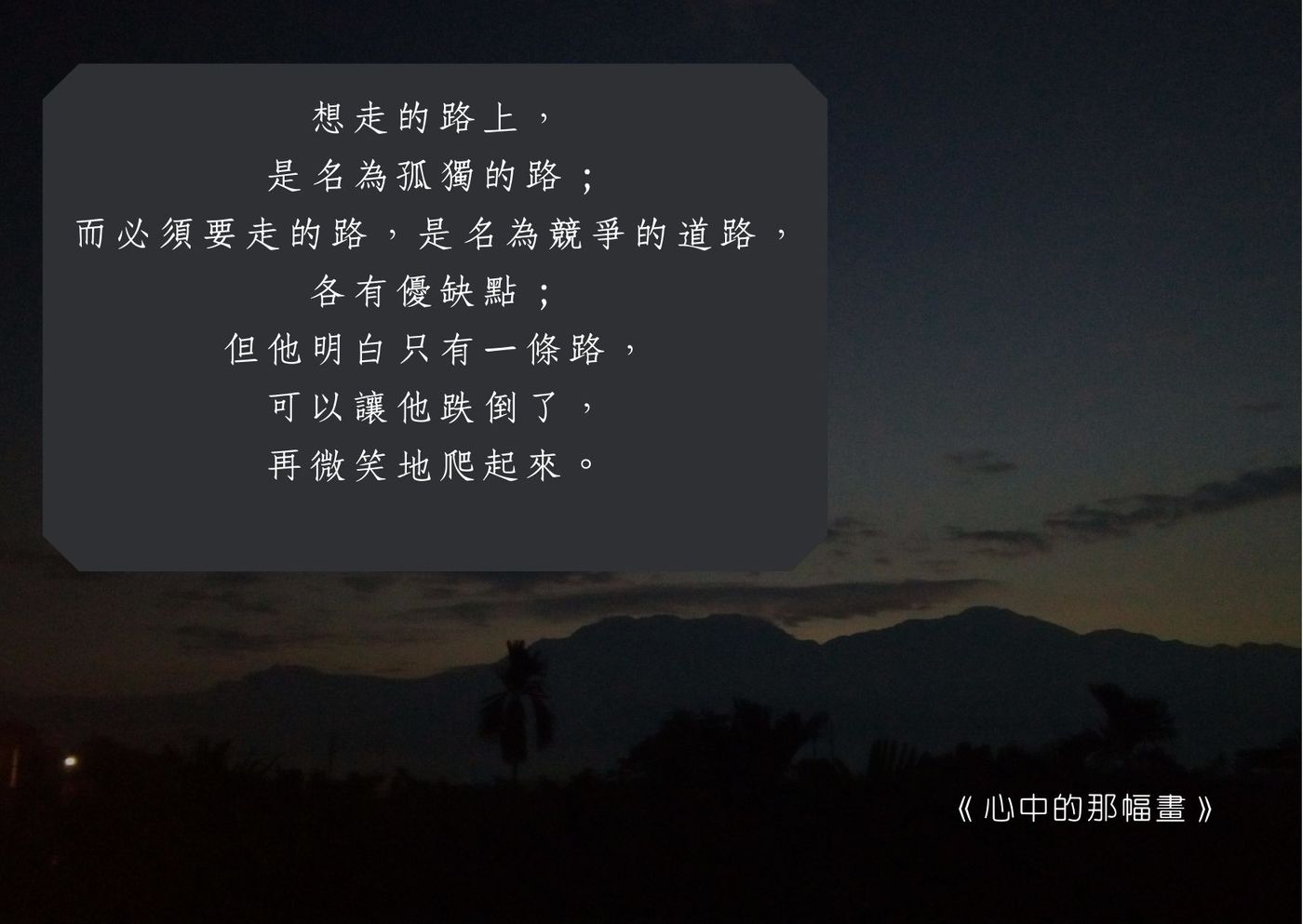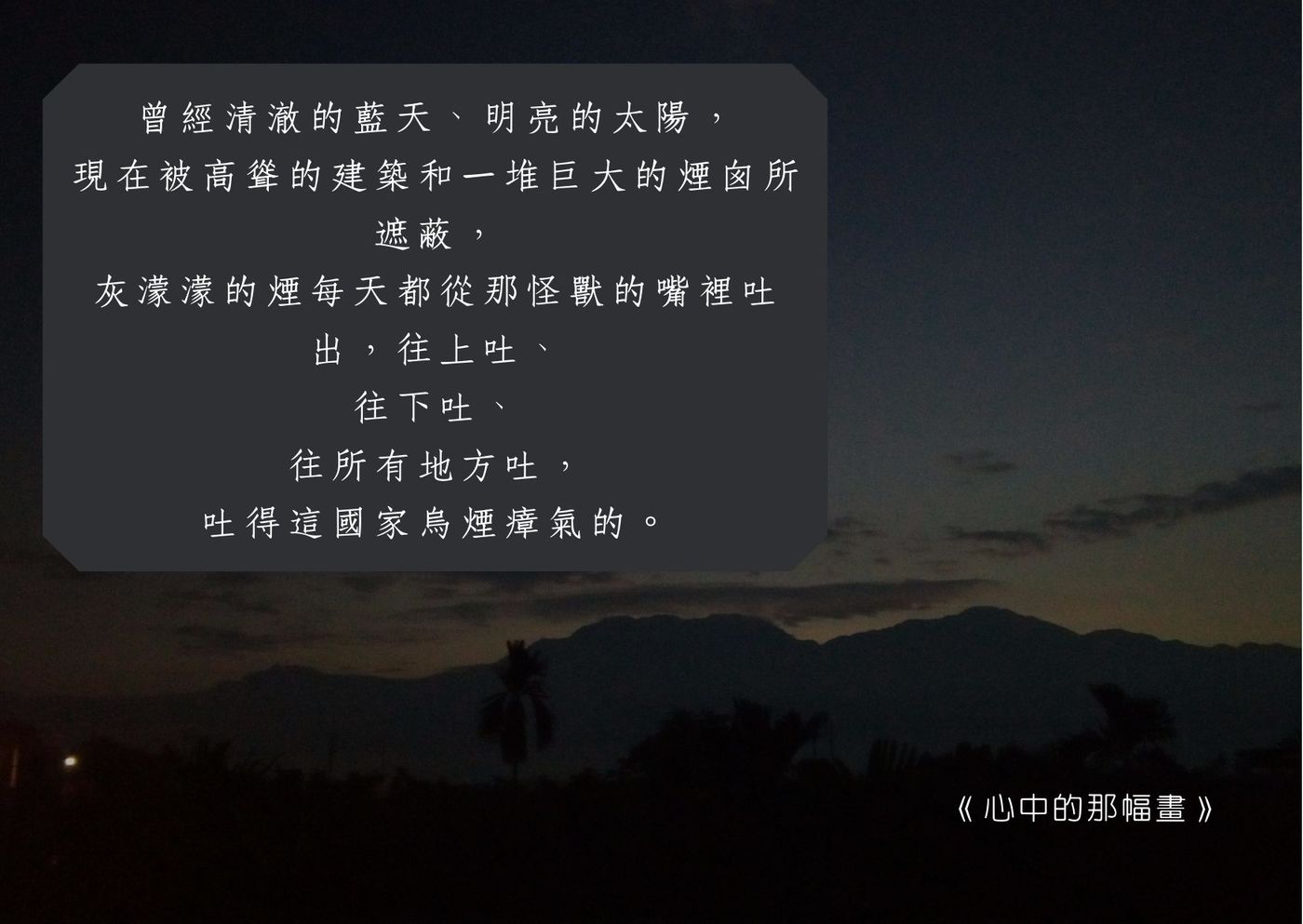故事不長,一篇即完,假如能讀到最後,你會發現,我只想表達一個溫馨的故事。
我從小沉溺於畫畫,當筆尖觸碰紙紋的那刻,腦海裡就會串連起一系列嶄新的想像,起初會以火柴人的形式記錄下來,後來,逐漸能描繪出立體的畫像,漸漸的,未來想以畫畫為生,也成為我的夢想。
可惜在我中學那年,父母離異,在這高壓的環境下,我失去畫畫的權力。父母都在爭奪我的扶養權,但我認為這塊土地已經失去「家」的含意,而我抱有夢想,堅信一切僅有可能,只要憑著信念與熱忱,我就能在這個社會中生存下來。
因此,在禮拜天的中午時段,我趁著父母到律師行處理離婚手續的事務,翻出小學露營時媽媽帶我到百貨公司採購的肩背式行李袋,隨意塞進一些自認為實用的寶物後,就告別了這個「家」。
那年,我才十四歲。

站在高鐵站入口,迷茫與恐懼等複雜的感情與我的心混為一體,在外人眼中,我可能就像一名失去方向感的孩子,我用絕望的聲調慢慢的從口中吐出了一句,「請給我一張能到台南的車票。」
仰頭望向隔著玻璃板的售票員小姐,我能從她的視線中感受到一絲稀奇的目光,萬幸的是,她沒有選擇打電話報案,我才能順利的坐上高鐵。
隨著高鐵高速的行駛,不時還能感受到些許震盪,我知道這是一趟沒有目的的旅程,選擇台南也是因為想盡可能的遠離台北。
看著略為模糊的窗框,我有點後悔這種交通方式,由於窗外的景色不斷的快速倒退,顯然讓我無法分清是否已經遠離家鄉,更重要的是,眼前的殘影似乎想把我的回憶逐一吞噬,同時滅絕我倒退的道路,幸好,高鐵此時進入一道漆黑的隧道,讓我流下的眼淚難以被人所見,保住了僅有的自尊。
經過沙崙站,順利抵達台南高鐵站,此時的時間已來到晚上八點十五分,第一次來到陌生的環境,由於身上只剩兩千台幣,我沒有選擇投宿任何的旅館,而是來到人行橋的端口。
那裡是一處正方形的空間,頭頂上的告示版告訴我這裡是連接著前站與後站的位置,我放下行李袋,從裡面拉出一張單薄的棉被,打算在這邊露宿一晚。
從父母的紛爭中,讓我得到遠超同齡人的成熟思維,我清楚暸解這樣的日子只是短暫之計,如果長遠下來,在還沒餓死之前,大概就會被路人通報,結束這段旅程。
正當我打算思索接下來的規劃時,我感受到一股視線,順著該方向一看,那裡同樣有一名遊民,乍眼一看,年齡接近四十左右,男子似乎也發現我的回望,但他沒有選擇回應,隨即就低下頭,自顧自的不知道在揮動什麼。
我的視線無法從男子身上脫離,並不是因為他身上散發著什麼獨特的氣質,而是我發現鋪在他腳邊的白色卷軸,我有一種預感,如果把卷軸攤開,會是一張又一張的畫紙。
我站起身來,緩緩的走到男子的身前,他同樣注意到我的舉動,停下手邊的動作,保持盤腿而坐的姿勢,以仰視的角度抬頭望著我。
或許是因為男子瀏海遮掩著眼睛的緣故,他的表情似乎沒有任何的變動,此時,我注意到他手中拿著一枝隨處看見的鉛筆,便大膽指向身旁的卷軸,問說:「不好意思,請問那是畫紙嗎?」
男子頷首回應:「是的。」
「那你是一名畫家嗎?」
「不是,我是一位作家。」男子拿起身旁的卷軸,從中拿出一張遞到我的下巴前。
我慎重的打開卷軸,在觸碰的瞬間,我確定它是畫紙的材質,而且還具有一定的品質,證據在於紙張的表皮已有一角泛黃,卻沒有濕滑易爛的感覺。
我保持站立的姿勢,繼續閱讀紙上的手寫文字,男子沒有阻止的意念,看來他不期待能從同為街友的少年手中進行一筆買賣。
不得不說,紙上的文字細緻整齊,不潦草,且筆力甚為遒勁,裡面的內容同樣精堪,只用一張卷軸的幅度,就把故事的主題完美點綴,最後的結局收尾更留下一段感人肺腑的餘溫,至少像我一樣沒有任何閱讀習慣的人而言,也能從中感受到筆者的功力。
我無法克制心中的疑惑,發自內心的直白問說:「我覺得你的文章很好,可是為什麼要用這種形式販賣?畢竟都2017年,大部分人都放棄手寫的方式。」
看著眼前低頭不語的男子,我反映到自己的問題是多麼的無禮且愚笨,我猜測既然是遊民,那他應該是缺乏錢財才無法依靠網絡從事寫手的工作,更不用說帶著手寫的故事去找出版社協商,可能出版社看到滿滿一卷手寫稿的同時,早已在心中立下「怪人」的烙印。
正當我打算轉身回到棉被位置的一刻,男子開口打斷了我剛要邁出的步伐,「我自認是在寫作上有才能,但我缺乏很多其他方面的優勢。」
「例如?」我偏著頭,一副不解的表情追問。
「我與社會早已脫軌,不會使用科技,想當然的,我也不會用電腦打字,但我仍然希望我的文字能在世上繼續留存,畢竟這是我惟一存在的證明。」男子回答道。
我無法理解他對我說這番話的含意,但明顯感覺氣氛一下變得沉重起來,不知怎麼回應,只能說出一些敷衍的祝福,隨即輕微的點點頭,結束這一次的對話。
接下來的一段日子,我靠著在打工版上找到的一些非法零工過活,以一雙泥腿,打拼奮鬥,過著勉強滿足一天溫飽的生活。
顯然,我低估了「社會」這一隻怪獸的兇殘程度,我花掉一些工薪來喬裝打扮一下,盡量以一些配件來擋住自己的面孔,避免被人發現未成年人士留宿街頭,一旦被人發現,憑著我身上的身份證明,應該只要一天時間,就會被送回台北的家。
我曾經想過把身份證也一并拋棄,但以現在的科技技術,萬一被警方發現,應該也只能拖延數天的時間,內心的不甘與無助湧上心頭,我開始懷疑自己是否走進一條不歸之路,但這點懷疑,不足以成為我回到破碎家庭的決心。
這段時間,我與橋上的男子更為熟悉,也暸解到他名叫蔡奇憶,我想稱呼他為蔡奇憶先生,但被他斷言拒絕,稱只要叫他的全名或奇憶就好。
我從蔡奇憶的對話中得知,原來他不是遊民,只是為了體驗生活,不……準確來說,是為了從生活中進行觀察,以獲取寫作的靈感,才會幾乎每天都到車站的橋上蹲坐,順便賣一些自己的作品。
很快,一年後過去,我的生活依舊沒有任何改變,未成年的零工往往都是一些體力活,且工作機會不大,遇到比較幸運的日子,可能一個禮拜有十二小時的時數工作,也有可能一個禮拜沒有工作,在空餘時間,我會趁著深夜撿起破爛,同時,我必須盡可能的維持正常飲食,才能負擔起這樣的高強度工作。
我惟一的娛樂是與蔡奇憶閒聊,從他口中聆聽他各種作品背後的靈感,或是未來作品的想像,這樣的日子,是我最快樂的時光。
每一次對話結束,我都很想把這些故事畫成圖像,可惜沒有多餘的體力與金錢讓我浪費在這種事情上。
某天,我抬頭看著清晰的夜空,空中沒有一點雲層,上面綴著零零散散的星體,月亮雖不圓滿,但殘月也有另類的美,就在此時,我看見蔡奇憶正在踏步走來,心裡想著難得他會主動找我聊天。
我直視著蔡奇憶的雙眼,發現他的眼神開始不自覺的閃躲,隨後,他挺起胸膛,深吸一口氣,似乎要宣告什麼重大事情似的說道,「你要不要搬來跟我一起住?」
我露出震驚的表情,但很快,我透過蔡奇憶雙眼的高光中,感受到他認真的神情,我無聲的點點頭,口中乍然無法說出感激的話,因為真的埋藏太多的思源。
接下來的一段日子,我跟隨蔡奇憶學習各種的編劇技巧,從三幕劇到角色設定,蔡奇憶先生都不遺餘力的通通指導予我,按照他的說法,「收留你是因為想在這個世界上留下更多我的存在證明,你不要想太多,更不用特別感激什麼的,這是互相利用,你必須成功,才能回應我在你身上的投資,如果覺得困惑,也可以解釋成工具的存在。」
人在屋簷下,我沒有任何的質疑或反駁,只能接受這樣的說法,而在日常生活中,蔡奇憶待我如親人般,不僅資助我完成高中課程,還打算為我報名大學,只是我們的相處方式不像父子,反而更像師徒,卻比真實的血緣關係更為濃厚,如同我們之間存在一條隱形的絆線,把我和蔡奇憶牽連在一起。
我們一起生活時間只有四年,那年我十九歲。
蔡奇憶因為右腦的惡性腫瘤發作而離世,我靠著醫院病房的的鐵制扶手,不顧周圍眾人的目光,一直號啕大哭,那天晚上,星空同樣清晰,月亮一樣不圓,卻像一把鐮刀般,挺直的掛在半空。
後來,我沒有放棄畫畫的習慣,但是寫作變成了我主要的工作,以及舒發故事的橋樑,令我改變夢想的原因有兩個,第一是我發現社會的現實,我所學到的技能都是寫作的技能,未來以此為出路的成功率會更高,這是缺乏父母及人際關係的我必需看清的現實。
其次,我還有那一句承諾要兌現,盡心竭力的成為蔡奇憶的「工具」,透過我的能力,讓世人記得他存在世上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