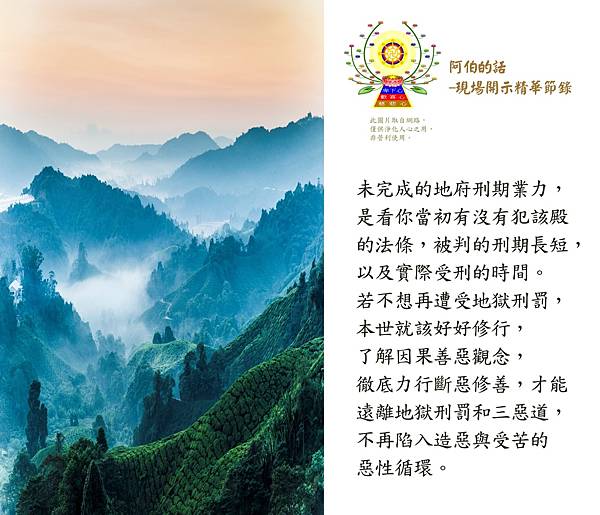生,當如夏花之絢爛;死,當如秋葉之靜美。
前言
週二傍晚應大女兒之邀上台北去品嚐她極力推薦的美食。原本她詢問我們和二女兒一家是否訂餐慶祝母親節,可是就在問詢之時,當日已被預訂,她有點不甘,一心想讓我們也能品嘗到,乃有週二之約。食物好吃,服務亦佳…,鐵板燒原來也可以如此精緻,如此優雅,長知識了…
如何面對生死課題
席間,大女兒提及看了我前些日子寫的楊月娥和黃大米的故事,她想藉此機會了解一下我們夫妻對生死和照護的看法。在食物好,氣氛佳的時候提此問,嗯,滿貼心的。年輕時讀及「人是向死的存活。」—從生下來那一刻開始,人的每一天—甚至每一分每一秒—都趨向並接近死亡。記得當時深有感觸,但因年紀尚輕,距離尚遠,所以未曾深究。今歳數已高,碰多了,看多了,聽多了死亡的案例,自然也對此課題有所思索和決定。
不能自理就不要拖延
之前多次跟家人提及:不能自理,就不要拖延,請給我一針,我會萬分感激。而且,對我,對家人都好。家人似乎都聽聽就過了。有時也會反問:那來的針?誰打?想想也對,即令法令許可,也不應是家人來處理。何況法令許不許都待了解…在我蒐集的資料中,如果是需要做出家人生死的決定時,對當事者都會是長久的折騰,他們會一直質疑:這個決定到底對或不對?如果不對,如果太快決定了,怎麼辦?因此一直在那兒糾結,一直在那兒惶惑,一直走不出來…歐美有些國家或地區,針對無法復原,或者醫療只是拖延生命的病人,允許—甚至要求—不予醫療,保險也不給付,我認為值得參考。
重要的是活著時
楊月娥在照護故事中提及:當初決定她母親要不要氣切時,她的決定是放棄,但她哥哥卻是同意,因為他哥哥想像著要帶媽媽去旅遊,去吃美食,去彌補他覺得對媽媽的虧欠,而楊月娥則覺得哥哥的期盼她早已做到了,因此覺得放手讓母親走反而更好;黃大米的故事中,我個人認為大米因為長期與家人疏離,因此她之所以積極出手搶救,或許有點像楊月娥的哥哥,覺得對父親有些虧欠,而大米的哥哥,則因長期和父母一起生活,長年照顧,因此可能不是那樣想……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想法,我要說的是:還可以走,還可以動,腦筋也還好,那麼想做的,想玩的,想吃的,就不必太過忌諱。家人還能在一起時,多抽點時間,多找點機會,聚聚聊聊,彼此關心,相互感恩,這些都要比什麼照護不照護更重要吧?
苟延殘喘有何意義
我服噟百丈禪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說法。一切要看能不能自理,能自理,那就繼續活下去;生活無法自理,那就不要再生活下去了。沒有品質,只在那兒苟延殘喘的掙扎有什麼意義?有什麼意思?人既然是向死的存活,那麼死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必然的,只是或遲或早而已,活著,就好好的痛快的活著,不能好好的痛快的活著,需要看人臉色,看人施捨,那樣幹嗎?我贊同泰戈爾那句:「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該盡力的已經盡力了,可經歷的已經經歷了,那麼當死亡到來時,就沈靜的、安詳的(甚至有些欣然的)接受這必然的結局。
先向過往過錯致歉
這一生中,我也曾說錯話,做錯事,對那些因為我的錯或我的過,而感到不滿,甚至懷恨在心的人,我鄭重道歉!對不起,我沒有蓄意傷人的意思,不料卻造成了你的受傷,在此向你致歉,請你原諒我。對於曾經接觸過的人—尤其是我的家人—我則只有感恩和愛,謝謝你們,因為你們寬容和接納,我才有今日,也才能成為現在的我…。
我沒有什麼遺憾,也沒有什麼愧疚。還活著,我會充實快樂的過活,不能如意自主的活了,我也希望能欣然無憾的告別。
結論:斷食是良方
以前還在想怎麼辦才能做到不必麻煩別人,自己就能如願的告別人間,日昨看到畢柳鶯醫師寫的《斷食善終——送母遠行,學習面對死亡的生命課題》記錄她在母親及家人同意下,用斷食的方式送母親離開。原來不能自理了,最自然,最少痛苦的走法就是這麼簡單可行。
後記:
- 六0年代前,醫療沒有這麼發達,病了,沒醫療或沒法醫療,一段時間後,慢慢的、自然的就走了,大家也都習以為常,因為生老病死原本就像大自然的運作一樣的自然…。醫療進步了,自然的死亡反而成了難題,反而成了困擾和掙扎…。幹嗎呀?
- 又,畢柳鶯的故事另文介紹。
- 又,上述只是個人的看法,別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和想法,我理解,也尊重。並認為:不同看法無妨並存,也不必去探究是非對錯,就因為看法多樣,所以社會才會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