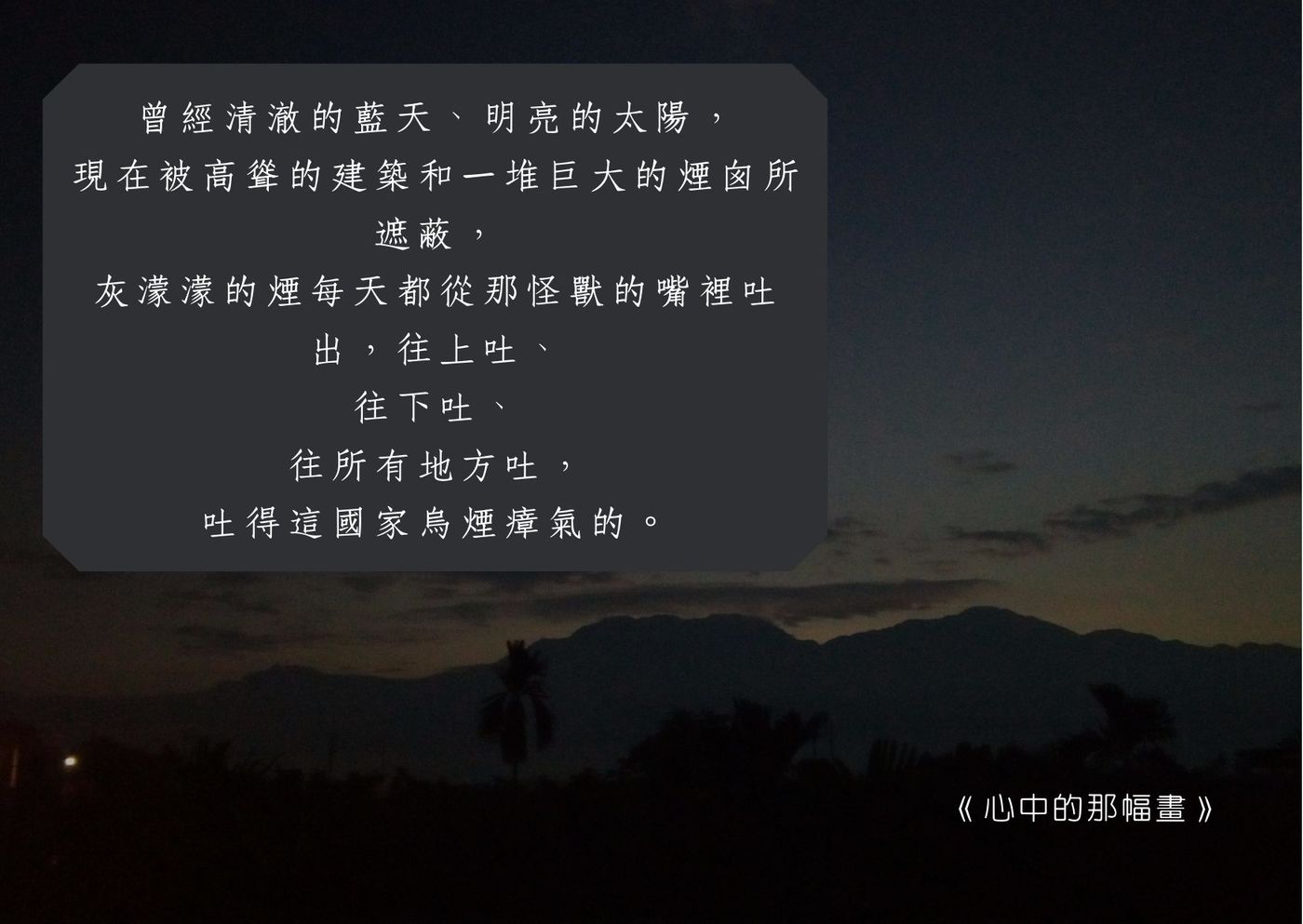我想要交往一個男孩子。
(要用交往一個,而非和一個男孩子交往。他是男孩子群體裡的之一,而非唯一。)
他很神秘、很深層,話很少,永遠就那樣安安靜靜的。
我們會一起看海、看電影、聽音樂。
一起不耐煩的等待世界末日。
他喜歡用他憂鬱的眼睛看每顆鏡頭都美得不可思議的文藝片。
他喜歡用從不講話、而且也不打算講話的語氣告訴我今天要去哪個片海灘。
我們在熟悉的城市裡有很多個秘密基地,在廢墟的老宅裡放一個沙發,上頭有乾淨溫暖的毛毯,冬天時就一起去那裡取暖。
我們在海岸邊的小洞窟裡有一個書架,上面堆滿了一再重複看的小說和文章,就那樣躺在潔白的沙灘上一遍一遍地看,永遠都會忘記,永遠都會再一次重看。
你會突然的低聲唸出你早已記住卻再一次在泛黃紙上看到的句子,我會無聲的聽著,像我不存在的那樣無聲。
我們在某個樹林裡的樹屋中放一個很舊很舊的音響,輪流播著彼此不認識,卻試著辨別的歌,我們跳舞、我們歡唱、我們睡覺、我們憂傷,在這座城市的每一個角落。
(角落後面好像很適合接做愛,像散文裡大家喜歡說的那樣。)
我們在一面新粉刷牆面的商場裡,用一整個晚上拿著壓克力顏料胡亂的畫,你畫著我從來沒有見過的風景。
(海在樹的上方。)
我畫著你認為世界不曾存在的動物。
(有著企鵝模樣的貓。)
我們畫很美很美的男孩子。
我們畫很英俊很英俊的女孩子。
(這句話本身就有刻板印象。)
一直畫一直畫,直到清晨的陽光從一旁結帳櫃檯的落地窗打入,我們才從十幾層樓高的窗戶一併跳下,我們死不了,我們跳進了完美的湖裡,在湖中央的一塊小木板上曬太陽,曬到皮都脫了一千七百層才甘願回家。
後來我們就分手了,沒有再見過,像從來沒有交往過那樣。
我們都在彼此的世界裡人間蒸發。
(你說我們從來都不是在人間呀。)
我想交往一個女孩子。
(要用交往一個,並非和一個女孩子交往。她是女孩子群體裡的之一,而非唯一。)
我們一起在平行時空裡看了一部電影,是在講一個女孩子和男孩子交往的故事。
電影裡的男孩子除了低聲念出他在海邊看的書上的句子以外,就沒有其他台詞了,整部電影沒有配樂,寂寞的寂靜,只有一幕他們在樹屋裡跳舞時才突然有了聲音,我們倆都被聲音給嚇到,聲音好大聲好大聲,像是突然闖入了某種怪獸嘶吼一般。
(但很好聽,怪獸嘶吼的聲音很好聽。)
我們在平行時空的電影院裡接吻,平行時空裡沒有人,電影裡的兩個演員穿梭在原本時空裡我們熟悉的那座城市裡,穿梭中,我們知道他們做愛了,但沒有任何一顆鏡頭拍出來,但我們能夠感覺得到,甚至是穿插於哪一顆和哪一顆鏡頭之間。
我們在那個電影院裡的每一個院廳不斷地輪迴,看一部電影,哭、笑、接吻,再起身去下一個院廳,哭、笑、接吻,沒有時間、沒有地點,所有電影交織成一個世界,我們相愛,在沒有時間裡的平行時空承諾永恆。
我們看著電影裡的電影院,觀眾們看著電影,有點像在看我們,但我相信不是,那只是導演過於熟練的拍攝眼神。
後來沒有人知道我們分手了沒有,在那個時空裡沒有事實或虛假這兩回事,我們就是看電影、擁抱接吻,相愛,就只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