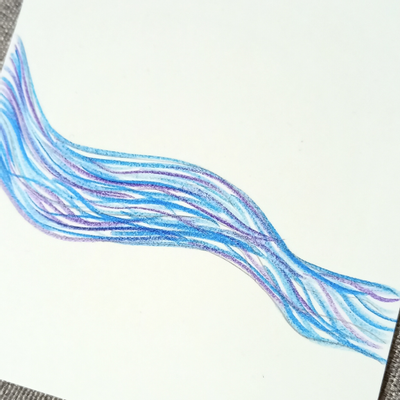足聲吶喊近在耳邊,雙眼仍疼到睜不開,潘文雙與安奉良掩目伏身,不知如何是好。另兩人同樣滿臉的紅粉淚水,好在感官過人,察覺吹上右頰的風勢加快,桓古尋拔刀一斬!當先衝上的追兵腰部冰涼,上下半身旋即分離!
寧澈亦無多想,左臂下意識前伸,「咯。」袖裡劍破頸而出!
戴賢彰喊說:「不要強碰,斷他們後路!」
安奉良將唾沫吐向衣襬,再用濕衣擦去刺目的粉末,總算能視物辨路,眼見敵兵騎馬包抄,他直接甩出吞雲戟,揮人下馬。三節銀戟猶在半空,旋又轉向,鋒援一重,再一人落馬!
一個箭步縱上馬背,左邊的潘文雙亦輕身拽住韁繩,安奉良遂扭頭喝道:「快!」桓寧二人蹬地一高,分別坐上安奉良、潘文雙後頭。
「駕!」人影馬身瞬時突圍!
鐵蹄踐過泥窪亂蕪,躍過塌樹青岩,紛繁的尖杈長枒因人馬飛奔啪啪斷裂,在皮膚上留下數不盡的紅痕,四人雙騎沒命似地前奔。
「射!」高世倜一聲令下,寧澈環住前人柔軟的小腹,雙雙俯身,奪命連箭擦背而過。桓古尋則旋腰舞刀,打落勁矢。
人能閃躲疾箭,馬可不行,一箭命中馬臀,座騎受驚人立,潘寧兩人失衡掉地!寧澈右掌一按,趕緊起身,舉劍盪開迎面而來的箭矢,再挽起纖細的胳膊,「往溪澗跑!」
同伴墜馬,桓古尋對安奉良說:「你去幫他們。」「那你呢?」安奉良問。
桓古尋應道:「我要引開騎兵,爾後在聯絡點碰頭。」「小心點。」知他馬術非凡,無須擔憂,安奉良隨即翻下前座,猶在馬背上的人擭繩右扯,馬首朝西偏去。
安奉良甫下馬,未鬥合的吞雲戟破空入體,捅著一人的背脊,後再使力一抽,戟鋒連著溫熱的血液被收回掌中,接著他邁開雙腿,一邊殺除擋道者,一邊跑向寧潘兩人。
「喀、喀、喀……」三節戟棍夾肘絞緊,後卸下一條臂膀!伴隨淒厲的慘叫,安奉良攻無不克,卻也漸漸陷入敵方包圍,銀戟再度插進胸腹後,背後響起達達蹄聲,安奉良應對不暇,九環刀當頭斬至!
「呃!」座上人倏然倒下,頸部血柱噴薄,中間嵌著一枚柳葉鏢。
「快來!」前面不遠處的潘文雙高喊。安奉良趕忙跟上。
三人重返山澗,隨波而游。
另一廂的桓古尋拖著一大群追兵,顛簸之中,臀腿感受馬匹傳來的力量,漸能掌握其狀態,於是他踩著鐵鐙,臀部稍稍離開馬鞍,不一味向前,而是大膽跳過攔路的橫木、不悉深淺的池沼、高低落差大的地面。雖減緩逃跑的腳步,卻使後邊騎術不足的兵馬裹足脫隊。
白麟刀劈開遮目的枝葉後,前途再現一層樓之差的斷崖!桓古尋卻夷然無畏,策馬加速,座下駿馬亦不退縮,四蹄離地的那一剎那,一人一馬彷若飛天奔月!
為減輕馬兒的負擔,技藝超群的騎師襠胯懸空,靴底也沒踩實馬鐙。人與馬達到最高點後,疾疾下降,蹄鐵觸底前,他右手攀住從眼前經過的樹枝,卸去泰半墜落的勁道,待馬蹄穩穩踏實,人亦順勢坐回鞍韉,繼續馳騁山林。
「啊啊啊──」後兵不是不及勒繩,摔個四腳朝天,便是馬齒露白,不聽人指揮跳崖。
惟高家兩兄弟不受阻擋,相繼躍往底下兩隻沒受傷的馬,窮追不捨。
桓古尋騎的馬終非星湖雪那種神駿,一路縱高奔快,體力逐漸消耗殆盡,明白牠支撐不了多久,遂不再催促,任由後方兩騎迫身。
銳利的蛇鐮槍觸及腦勺前,桓古尋抱住橫出的樹枝翻上,緊跟在後的高三世倜這才驚見前有障礙,呼聲尚在喉頭,鼻梁先撞粗枝,後碰固柢!
「鏗!」蹲在樹上的桓古尋持刀格開第二支槍,高大世倫一招不中,迴槍再刺,逼人下樹,隨後一腳登木,藉之騰起,手中長槍如棍直下!桓古尋轉身閃遠,旋又揚刀搶近,可惜刀鋒堪堪擦過臉面。高大撤步避走後,刀客跨足追擊,弟弟世倜提槍接招。
雙槍迅如遊龍、魅似毒蛇,白麟刀左攔右擋,健腰前彎後仰。為免後患無窮,桓古尋不敢真下殺手,然高氏兄弟系出武門,心懷顧忌,便是險象環生!
「嚓!」縱然快速閃左,蛇鐮槍仍剜下肋部的皮肉,但戰況危急,桓古尋甚至不覺痛感,他蹦腳側身,槍桿掃過其下,另一根槍桿隨後竄上,敲落他的身軀。桓古尋連忙彈腰再起,直刀架住復返的蛇鐮槍,且聆:「鏘──」刀刃貼著槍身,迫向高大的臉龐。高世倫雖及時屈膝矮頭,但緊接著腿脛一痛,被人踢倒在地。
桓古尋正欲逃之夭夭,但這對兄弟實在纏人,手足倒下,剩下的那個不退反攻,攻勢還更加猛烈,不留餘地。鐺鐺鍠鍠,白麟刀與蛇鐮槍數度交鋒,不分軒輊,眼看地上的高大即將爬起再戰,桓古尋故漏空門,引誘高三的槍頭冒然攻擊,他速圈左臂,捉住槍桿,右刀一挽,欲剁桿上前手!嚇得高世倜鬆開指掌,卻正中對手下懷。
大手猛如鷹爪,改擒未及遠開的左腕,而後長槍下繞,被帶至高世倜手臂外側,長桿使勁一壓,高世倜頓時咬牙切齒:「啊啊……住、住手……」肩關節幾要脫臼,他半彎著身,戰姿大幅走樣。
機不可失,桓古尋的膝頭速沉速起,一肩扛起高三,同時運功鎖竅,將人扔向他大哥!
「喔喔……」蕩元令及澤山錄雙重加持下,兄弟倆摔成一團,頭腦七葷八素,映入眼簾的視野比糨糊還糊,等回過神來,要緝捕的人已杳然無蹤。
寧澈這一廂尚於山澗中載浮載沉,他們揀了一塊漂木作浮板,水勢因應地形變化,流速時緩時急,水深亦同,深時沒頂吃水,淺時就足尖點石,敏捷通過。雖弄得髮膚衫褲又濕又沉,且全身磕磕碰碰的,免想也知必留瘀青,然好處是能藉溪水溪石躲藏,大幅降低岸邊箭雨的威脅。
「哎!」不過水裡狀況多變,一個不留神,兩顆巨大的礁石卡住狹長的漂木,安奉良手滑沒拿穩,木頭立時脫手,身體也順水而遠。後至的寧澈想搬開長木,卻忽被素手摁頭下水,因為又有飛箭襲來,只好作罷。
「噗通、噗通、噗通!」過不多時就逢小瀑布,三人接連掉入下邊的深潭,潘文雙和安奉良身子猶未浮出水面,便被水流沖往下游,然游不過一丈,霍地回沖,原來是寧澈運使澤山錄,強制改變流向,把人帶往瀑布的後面。
「噗哈!」寧澈一手揪著攀附岩壁的樹藤,一手揩面,「沒有浮板太危險了,容易撞傷腦袋,得再找塊木頭。」
看著水簾外一道道的身影,潘文雙說:「可是在這兒待得越久,對咱們越不利。」
安奉良面朝下游,問:「你能用水送我上去嗎?讓我砍下那棵樹的樹枝。」他講的是岸上石堆間一棵生得很斜的樹木,其枝幹跨越一半的水道,伸至溪流中央,其中一根分支粗逾人體,很適合拿來當浮板。
「可以是可以……」寧澈猶豫:「不過必會惹來周遭注意。」
「只能博一博了。」安奉良接合吞雲戟,「砍樹後咱們全速前進,這邊的追兵多為徒步,及不上溪流之快。」
「就這麼辦。」潘文雙扯下長長的藤蔓,道:「我先去前頭綁好樹枝,免得待會兒水勢太大,沖走樹枝。」
於是她游到該樹下方,擺臂振腕,將長蔓掛上枝頭,再垂降下來,左手握緊藤蔓兩端,纏繞於腕,右手則抓住凸起的礁石,然後點頭以示就緒。
安奉良揣著吞雲戟,道:「我也好了。」
鳳眸闔上,一個深深的吐納後,寧澈彷彿置身高空,俯視這座深潭,信手撥弄,便是狂瀾四起!
溪水陡然暴漲,不只嚇醒夜眠的林鳥野獸,戴、高二族的家兵亦是驚叫連連,匆忙逃離溪岸,戴少宗主一步登高,就見朦朧月華下,淙淙白水中,一抹難掩光彩的銀芒閃現。戴賢彰不作他想,彎弓就射!
「呃啊!」吞雲戟輕鬆斫木,然其主左背中箭,頹然落水!落水後側顱還撞著石頭,神智立失!
瞄準血水流淌之處,戴賢彰再射一箭,然而箭羽甫離弦,便被一炫精光削成兩截,正為潘文雙出鏢斷之。
「救人!」清喝一聲後,倩影拍石縱身,力戰戴賢彰!
數枚暗鏢似柳非柳,挾風迅至眉睫,迫使戴賢彰抽刀防禦,因有夜色掩護,暗器往往近到一臂之距才會顯現,又一次被柳葉鏢破相後,他跳下巨石,朗聲:「放箭!」
此言一出,高處的潘文雙頓成箭靶,她翻身魚躍,無數箭矢於周身驚險飛過,戴賢彰算準其落點,跨跳至溪中某塊凸石,伺機制敵。
不過他雙腳才剛站好,便聞細微之聲劃開空氣,知是暗器,戴賢彰立即後縱。果不其然,一鏢射往原先踏足的圓石,然而下一瞬,左踝忽緊,竟遭一條紅色長綢纏縛,彼端一拽,失去重心的人跌在淺水石地,後腦磕著硬石,悶哼濺血!
「少宗主!」心繫主人的家兵們顧不上追人,匆匆上前察看。
重新入水的潘文雙即時與夥伴會合,寧澈右臂扶著昏昏沉沉的安奉良,左臂則將潘文雙攬進自個兒與浮木之間,口道:「抓好。」
一些家兵看見水中的目標,或提刀涉水;或拈弓搭箭,然則溪水復漲,瞬間將之沖得不見影兒。
下了坡來到平地,遠離追捕者,三人終得上岸小憩。
「真丟臉,居然還得仰賴姑娘出手。」安奉良額角仍在淌血,後背還插著箭鏃,但吐息平穩,該無大礙。
寧澈的唇瓣泛白:「你不但要謝謝潘姑娘,還要謝我,費了好大勁才拉住貴體,以及這根同梁柱一般粗的木頭。」
安奉良噙笑:「男子漢大丈夫,為何如此計較?」
沒有理會他們一來一往的調侃,潘文雙擰出長髮多餘的水分後,僅言:「七天。」
寧澈與安奉良登時收聲。
「短短七天,晉淵莊就把太湖搞得天翻地覆,趁亂坐收漁利……」黛眉和唇角越發下沉:「這一仗,咱們一敗塗地。」
*****
過了夏府的龍曜堂,上橋橫度貫穿宅邸的大池,即抵達北岸的炎光廳,朝東行是尺波堂及芳塵居,尺波堂是存放禹航會重要文書的庫房,芳塵居是夏老夫人的臥房,若往反方向的西邊走去則為棲室與迴江居,是老爺夫人的臥室書房。炎光廳是正廳,廳前特別闢出空地,便於舉辦婚喪喜慶時擺桌設宴,平日則用於接待貴客或商議正事。
「傷勢好點了嗎?眼睛還會痛嗎?」夏時鳴神色忡忡。
寧澈答:「玥姐說那些粉末是染了色的石灰粉,刺激眼瞳外,還會沾附頭髮跟衣物,標記中招者。所幸我們即刻跳進溪澗,阿尋後來也有洗臉,沒事的。」
「方大夫也說我的箭傷不深,這幾天別碰水別動武就好。」而後安奉良掌落憑几,憤憤不平:「晉淵莊那班小人,竟在那種地方設下機關!」
桓古尋呼出濁氣:「他們早算到我方會怎生應對撤退,連臉都沒露,就把咱們趕出太湖。」
這一趟蘇州行,寧澈、桓古尋等人倉皇出逃,雖全員安然,但吳蛟幫渠頭悉數身亡,幫內互鬥搶著上位,幫外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更令人頭痛的是,桓古尋及寧澈身陷殺害渠頭、高世保的風波,其後的禹航會亦遭牽連,與江淮的世家幫派交惡。
廊外跫然,季南軒季玉轤連袂而入,老大面容沉重,交上一信,「鳴少爺,戴氏及高氏正式來函,要咱們給個說法,否則……」夏時鳴拆信觀之,後閉目長喟:「這次真的輸慘了。」
季玉轤亦不復平時嘻笑之色:「鳴少爺,據探子回報,那兩家人於杭州往北的幾條渠道設置檢查站,江南河那邊還會叫船人打開貨箱給他們審視,導致河渠嚴重堵船,誤了時辰,船戶商人均苦不堪言,希望禹航會儘快處理。」
夏時鳴不禁咒罵:「這哪是豪門?分明是土匪!」
桓古尋道:「你就公開說和我們早已沒瓜葛,杭州是禹航會的地盤,他們不會輕易侵犯。」寧澈同意:「我這兒尚有兩副沒用過的面罩,我和阿尋頂著真面目出杭州後,再戴上面罩行動。」
「這時走出杭州,你們必死無疑。」夏時鳴眼尾一揚:「攜拯如初,既然當時選擇開口力挺,本少主就絕不反悔!」
「鳴。」安奉良勸道:「這僅為權宜之計,咱們跟晉淵莊仍有得鬥,斷不能於此受到他方掣肘。」
夏時鳴悶悶地道:「在這兒縮了一頭,還鬥甚麼啊?」
「弘渡和尚會於月底前往嘉興的悅來茶坊,我想這不是晉淵莊刻意走漏。」寧澈支頜思量:「他固定到嘉興,該是向彼時猶為縣令的李勳做彙報,但李勳業已辭官,會面的時地會隨之更改嗎?」
「那得看弘渡知不知曉李勳的身分。」桓古尋道。
「鳴少爺,屬下曾對李勳做過詳細的調查,當中有則消息我本來不怎麼留意,現下想來,與弘渡大有關係。」季玉轤道:「據侍奉他的僕人說,李勳這人酷愛飲茶,他可以一天只吃一碗白飯配醬瓜,卻不能一刻無茶,休沐時最大的樂趣便是去嘉興的各個茶攤茶坊品茗,然而古怪的是……」
寧澈一點即通:「他從不去悅來茶坊。」
「是。」季三道:「聽說是李勳嫌那兒的茶不夠香,其實是不想被發現他識得弘渡。」
夏時鳴納悶:「他不進茶坊,如何跟弘渡接頭?」安奉良推測:「不進茶坊應為表象,很有可能是易容裝扮。」
「唔……」桓古尋沉吟:「李勳在嘉興人望很高,當地人對他非常熟悉,光是戴假髮黏假鬚,就算沒聞著味道,也騙不了人,得像我們在吳縣那樣徹底改換外貌體型,才能瞞過大眾。」
季大則猜:「難不成同弘渡見面的人,不是李勳?」
寧澈不這麼認為:「不是李勳就沒必要去嘉興了,徒增風險。」
季玉轤提議:「屬下再派人去打聽打聽,看看弘渡究竟是去見誰。」
「好。」夏時鳴頷首,後命:「另外再找個時間,備些厚禮,我要親自拜候金、褚、花三氏宗主。那群揚州人想靠權勢壓人,杭州人豈能悶不吭聲?」
「勞煩了。」寧澈道:「我們倆準備一下,等會兒出發。」
夏時鳴很不情願做此決定,只說:「出了杭州後,萬事當心,等熄了戴、高兩族的氣焰,即可回來。」
「放心。」桓古尋拍拍胸膛,「我倆經驗豐富。」言罷,他偕好友長身離去,回到初鶯園的客房各自收拾行李。
桓古尋動作快,一下子就綄好包袱,隨後到隔壁寧澈的房間,他正慢條斯理地折衣服。
「又要逃命了……」桓古尋似自言,似喟嘆地說。
「咱們的逃亡生涯好像從未休止。」寧澈半開玩笑:「如何,中原是不是同你的大草原一樣有趣,一日也不得閒?」
「中原人心眼比蜂巢上的洞還多!」桓古尋撇撇嘴:「我都不懂那些人在爭甚麼!」
「爭名逐利,人心自古如斯。」整理好衣衫及日用品,寧澈拎起行囊,「不過這一回不全是冤枉,高世保的確是我和潘文雙殺的,倒是委屈你了。」
「我不介意。」桓古尋咿呀推門。
四月剩不到十天,大池裡的白蘋緗荷開得正盛,紛紛疊疊,近的像要撲面襲人,遠的則似平原開展無際,煞是壯觀。
「桓少爺、寧少爺,老夫人有事相請。」婢女款款行禮,敞臂朝右。
沈碧篁?自從上回她突然出現,同家人賓客吃了頓晚飯,後道出耿峻軒、寧慶、莫丹秋、跋達四人的過往,這位年邁的老婦人復回此前的深居簡出,僅子孫兒媳見得,其餘同居一府的住客都不常看到她。
「老夫人在開夜堂寫字。」婢女領頭穿越東庭大大小小的石洞,到達開夜堂門前,示意徑直進入。
開夜堂內除了字畫,便是放置字畫的書櫃,牆上一幅幅的墨跡收齊各派大家;櫃中一卷卷的丹青集滿歷代名手,數量委實驚人。
「抱歉,這裡沒有椅子。」沈碧篁人在裡邊的內室,她跪坐於席,身前鋪展一張白絹,手執墨條,在硯臺上畫圈研磨。
「您找我們有甚麼事?」桓古尋站在內室的門口,隔著一層珠簾。
沈碧篁專心磨墨,頭也不抬:「老身聽人講揚州的高氏戴氏、蘇州的吳蛟幫對咱們很是生氣,勉旃今辰天還未亮就出府疏通渠道,分流船隻,子謐亦是傷透腦筋。」
聞言,桓寧二人大感內疚,然不待道歉,沙啞的嗓音逕續:「而今的情勢,跟當年越來越像了……」
兩個青年面面相覷,均看出彼方的不安。
珠簾另一側的沈碧篁稍稍抬眼,後又垂下,岔開話題:「這兒諸多字畫,有喜歡的嗎?」
環目四周,晶瞳首先停在東牆的一首七言詩:「這一幅。」詩的頭兩句是:「涿野軒皇陳,丹浦帝堯心。彎弧射封豕,解網縱前禽。」內容主要是歌頌皇威,描寫秋日整軍的肅殺,以詩中所述來看,下筆之人字跡稍嫌秀氣,然細審後即瞧出其筆鋒靈動不失工整、端正卻不拘謹,張弛有度,絕非泛泛。一瞧詩末的落款:「臣褚遂良書。」
桓古尋評:「這詩氣慨萬千,通常寫的人字跡也會跟著硬邦邦的,這人卻寫出自己的風格,很有特色。」寧澈看了讚道:「褚河南奉君命作的詩也收得,老夫人當真神通廣大。」
沈碧篁磨好墨,沒有邀人入室,目光逕自轉至面前的素絹,懸肘大書,「褚河南遭先皇貶謫,昔日作的詩文亦被清出皇宮,咱家恰好在宮中有熟人,褚氏遂拜託我們收回,事後餽贈豐厚的謝禮,當中一項便是他的墨寶。」寫好一張字,將它放到一旁晾乾,再提筆寫第二張。
而後寧澈走到南牆,說:「論行、草,逸少子敬佔去一二,餘下的名家頂多爭第三,但論飛白,蔡中郎作為此道開創,無人能出其右。」他止步於長幅的詩帖前,上面寫:「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該詩描述婦人思念出遠門的丈夫,甚至在夜晚夢見與他相聚,醒來才想起丈夫猶在外地,將哀傷的心情形容得絲絲入扣。這首詩歌是否為蔡邕所作不得而知,但看得出他對此詩的體悟,筆到末處,墨汁近乎乾枯也不蘸墨,突顯悲戚之感。
「連蔡中郎的手跡都有,老夫人還有拿不到的神品嗎?」寧澈大為驚奇。
「老身年少時毛躁粗心,成事不足,幸得貴人指點書法,學著沉澱心緒,把躁動化為鎮定及動力,才改掉這個臭脾氣,不再到處添麻煩。此後書法成了老身的興趣,至今不厭。」第二張也寫好後,她倒了一杯茶啜飲,指了指甫完成的筆墨,「這兩幅字送予你們。」
二人方掀起珠簾,步入內室,錦席上鋪著兩幅白絹,第一幅寫「莫逆於心」,第二幅則為「相知於言」。
寧澈端詳好半晌,遲疑地問:「老夫人,教導您書法的那位貴人是……」
「不錯,是寧大哥,你的曾祖父。」沈碧篁眉目低垂:「日後的紛爭只會愈來愈多,愈演愈烈,咱們無法左右他人的所思所為,但對周圍的人、對在乎的人……可以做得更多。」
「這和這兩幅字……有甚麼關聯?」桓古尋手捏後頸,甚是困惑。
沈碧篁道:「彼此心中無所違逆,互無反感,即得成為摯交,但要真實熟知、瞭解一個人,須靠言語來表達,有何不快、有何困難,直說無妨,說出口後,明晰對方在意的人事物,體諒對方的難處,情誼方得長久。」
寧澈搔搔臉頰,「甚麼事都向人吐露,有點難為情呀!」桓古尋倒不覺得:「不會呀,事情老悶在心裡怎解決得了?當然是講出來一同想辦法好啊!」
老婦淡淡一笑:「保持這份坦率,但願你們挺過一切風風雨雨。」
桓古尋和寧澈稽首拜倒,接下禮物,鄭重收起。
告別沈碧篁後,便從東庭的小門出去,伶俐的僕役已牽來星湖雪及雲上日,兩人跨過馬鞍,沿著大道走了十里路,即入杭州城。
端陽節馬上就要到了,河渠除開南來北往的貨船,猶有不少壯漢在練習划龍舟,希望在五月五當天拔得競渡錦標。水上期待節慶的來臨,陸上亦不例外,多家小吃攤飄著粽葉的清香,正好肚子也空著,遂隨意挑了一間店就座。
「嗯……好久沒吃粽子了。」剛出蒸籠的粽子冒著熱煙,桓古尋吹了兩口涼氣放進嘴裡,語調滿是懷念。
俊眉一軒,寧澈奇道:「塞外也吃粽子?」
「不吃。」桓古尋口齒含糊:「只是母親每到這個時節,會向中原來的行腳商買些米,包粽子給我吃,塞外的豬少,她就裹羊肉兔肉,有時也會沾點蜂蜜,她走了以後,我就沒再吃過。」
寧澈吃的是筒粽,就是塞入竹筒的粽子。最初楚人悼念屈原即是把米裝進竹筒,再投河祭祀,後來屈原托夢說筒粽均給水中的蛟龍竊走,遂改以蛟龍害怕的楝葉彩繩包纏,粽子方成今時之狀。「幼時某年端午,我半夜貪食溜進灶房偷吃甜粽,隔天正餐又吃肉粽,當天下午就脹氣胃痛。往後每逢五月初,先慈都會特別吩咐廚工,晚上要把甜粽藏好,不讓我知悉在哪裡。」
「喔。」桓古尋恍然:「粽子不能吃太多啊,怪不得母親只准我最多吃兩顆。」
吃完飯後,二人牽著馬四處閒逛,其時的杭州人口不多,人聲不若揚、蘇鼎沸,但也沒到冷清,頗為悠閒自在。這裡的店家比較率性,客人進店不會熱情招呼,僅在櫃臺輕聲說了句:「隨便看。」
桓古尋換了新的剃刀及靴子,寧澈則買梳子和腰帶,以及乾糧、草料、肉乾、火熠子等等出門在外常用之物,並請人將方纔拿到的字裱上卷軸,裱好後一人收一卷。此外天候轉熱,雖不像冬日需攜厚重的衣袍毛毯,然夏天的江南蚊蚋多,驅蟲的薰香必不可少,走走停停購齊全部的物品,已是薄暮時分。
他們從南門入城,行過大半個城鎮,步出北門後,驀地相視而笑,接著衣袂翻飛,原地起跳上馬,迅速絕塵遠去。
「欸!」躲在暗處多時的許震海終於現身,施展輕功追逐,但人哪跑得贏馬?幸好頭前的金駿玄騅不一會兒便停下,等候七旬老人氣喘吁吁地跟來。
「你們……你們這兩個臭娃兒……存心想累死老夫啊……」許震海摘下頭巾,胡亂擦著汗涔涔的頭臉頸項。
「幹嘛這樣鬼鬼祟祟的?」桓古尋解下繫在行李旁的水壺,拋將過去。
許震海看都不看就接住,拔開蓋子咕嚕嚕地猛灌,然後把剩下的水全澆在頭上,「除非有人活得不耐煩了,不然目下誰敢在大庭廣眾跟你們搭話?」
「你囉。」三人二馬佇足梅樹下,寧澈隨手採了一顆青梅餵給雲上日,「晚輩剛好在想老先生何時會來找我們。」
「你還敢說?爺爺我年輕時都沒你倆這麼會惹事!」許震海一屁股坐下,續言:「到底是甚麼寶貝,不惜殺掉高世保也要偷出?」
兩個青年默然無語。
銳利的鷹目立刻射來:「是甚麼?是面具嗎?」
寧澈暗嘆一口氣,坦承:「是,不過面具現在不在我們身上,已被朝廷收走。」
話音方落,許震海右手一霍,沙塵飛揚!桓寧二人側頭閉眼,腳才退半步,寧澈就被掐住食指,無法啟動機括彈劍,緊接著猛禽般的手指襲面,俊容卻不閃不避,任人欺近。
「小娃兒,別以為我不會殺你。」許震海的指尖距離深邃的雙眸僅只半寸。
桓古尋亦只握住刀柄,沒有出刀,「即便殺了我們倆,你也得不到面具。」
灰白的髭鬚顫顫:「起碼我能宰掉兩個說話不算話的小子洩憤!」
「真把面具給你,在找到祕寶前,你會先見到閻王。」寧澈神情如常:「霽泉面具不是人拿得起的。」許震海怒氣稍平,鬆手退開,「甚麼意思?」
寧澈指著頭頂,解釋:「面具頂上鑲著眹珠,眹珠蘊含的靈氣足以毀天滅地,莫說身負澤山錄的功體,常人接觸久了也會引發眹珠波動,那股氣勁一旦潰堤奔湧而出,甚麼寶藏、醫書、堡壘……眼目所及內,蕩然無存。」
許震海瞇起眼,似在判斷他所言真假,「真有那麼邪門?晉淵莊那邊怎地沒出事?」
「他們大概也感覺到珠子的不穩定,很聰明地插了小針進去,阻撓內部氣息運轉,加上面具本身就有疏導之效,並將其放在無人走動的地下迷宮,故無發生災禍。」寧澈道。
「呼……」許震海冷靜後,復又盤腿坐地,「寶庫在哪裡?」
「不曉得。」桓古尋歪著頭,忽問:「假如根本沒有寶庫,或是沒有醫書,你怎麼辦?」
許震海眼神一黯,他不是沒想過這個情況,「不怎麼辦,接幸兒回老家,安穩度過餘生。我下地獄前,會先送幸兒去西方極樂。」
寧澈蹙起眉頭:「幸兒在宋城有李老夫人悉心照料,淨濁大師亦會定期為她渡氣,何必這般悲觀?」
「小娃兒何時變得如此天真?」老人苦笑:「遇見那兩人是幸兒生命中為數不多的福份,只嘆他們的年歲比起老夫只大不小,任一人離世,幸兒怎麼活?他們的善舉並非必然,亦非每個人都有同等的好心腸。」
桓古尋沉聲問:「幸兒她……她知道你的想法嗎?」
「不,我沒跟她說。」許震海偏開臉,遙望遠方,「她受的苦夠多了,沒必要再讓她煩惱生死,反正我下手的時候,幸兒不會感到任何痛苦。」旋又導回正題:「是面具要送回神都,還是要把劍送來?」
「你怎知霽泉劍在朝廷那裡?」不僅桓古尋,寧澈亦是訝然。
「也不瞧瞧你爺爺跑江湖跑多少年了?相較於面具,霽泉劍的音訊連個屁都無,肯定是被壓下去了,潘女娃也表現得對此劍不怎麼感興趣。嘿!人就是這樣,沒有的東西就常掛在嘴邊,有的卻隻字不提,生怕別人來搶。」許震海咧嘴邪笑:「而且我剛剛問寶庫所在時,你們不是答沒劍無從推敲,而是逕言不悉地點,由此可知,霽泉劍已然得手。」
寧澈面露不甘,卻不由得佩服:「不愧是夢裡索魂鞭,當真老奸巨猾。」
「不機靈點,老夫怎能活到今日?」許震海忖說:「你們還在此地,想是要送劍過來……寶庫的位置真的毫無頭緒?澤山錄不是能感應萬物?眹珠有跟你們講甚麼嗎?」
桓古尋失笑:「澤山錄僅是一門武學,眹珠更不是卦象骨卜。」而後搖頭一嘆:「可以的話,我完全不想踏入寶庫。」
「哦?」許震海挑眉:「大娃兒如是無欲無求?看一眼裡頭藏著甚麼寶物也不稀罕?」
「有甚麼好看的?我想要的物什又不在裡面。」寬闊的雙肩聳了聳,「況且寶庫藏的是不是寶還不一定呢!」
「真臭屁呀!」於是許震海問:「那你想要甚麼?」
寧澈代答:「獲得夏總舵主的認可,拿回他父親寄放於總舵主那兒的狼牙。」
「狼牙?」瞅向突厥人胸前的項鍊,許震海頗感興趣:「甚麼認可,幫他幹活?」
「不清楚……」桓古尋皺著臉:「上次花了好一番工夫才找出他來,卻只稱讚兩句就沒了……他該未把牙齒弄丟了不好講明,故意戲弄我吧?」
寧澈斜眼睨去:「進叔哪會這麼無聊。」
「你老娘沒說你老子做啥給人狼齒嗎?」許震海問。
桓古尋仍是搖首:「父親生前將狼齒交託給兩個人,第一個是青甲狼騎的芸夫人,我用好幾顆盜匪頭子的頭子換來她手上的狼齒,現剩進叔的那一顆,母親僅說我收集全了,就會明瞭父親的用意。」
許震海捋了捋白鬚,「他應該……是想叮嚀你些話。」清朗的男音微揚:「叮嚀?」
「老夫好歹當過人家父母。」許震海道:「做爹娘的,對孩子總是叨念個沒完沒了,你老子定有很多很多事想和你講,無奈父子緣薄,只得用別的方式傳達。」
桓古尋忙問:「那……那父親想傳達甚麼?」肥碩的兩臂一攤,表示不明:「老夫可不認識你老子,豈知他想講甚麼,不過呢……長輩通常不喜少年郎橫衝直撞的。」
「橫衝直撞?」寧澈不解:「阿尋的個性不衝動啊。」
「那是在你看來……」許震海捏了下肚腩,「在老夫眼中,你們倆簡直膽大包天,恣意妄為。」
正想反唇,卻聞:「太好了,老先生果然平安!」溫婉的女聲隨同輕盈的蓮步跑來,是洪珺萱,藍渝樺亦在。
桓古尋偏頭瞅了瞅:「盧姑娘呢?」洪珺萱拎高手裡的蔬果,答:「她陪師尊去藥鋪抓藥了,我和大師姐則買些吃食,約好在這兒碰面。」
「桓大哥、寧公子,二位……」藍渝樺猶疑地四下張望,確定左近沒有生人,方續:「高世保及吳蛟幫的事……是你們做的?」
「事態複雜,三言兩語很難說得清。」寧澈應說:「為防旁人擅自臆測,若有要互相幫忙的,可透過禹航會轉達,雙方少見為妙。」
「兩位的安危方為當務之急。」洪珺萱正色:「我們探聽過薛渠頭的死因,同是短劍長刀造成致命傷,從右上背及右後腰穿透至前,致使他失血過多而亡……」
桓古尋當即聽出不對勁:「如果是我倆行刺,一招刎頸即死,不會給他喘息呼救的空檔,也用不著聯手,更何況小澈是左撇子,短劍怎會從右側出擊?」
「是啊!」藍渝樺說:「類似的矛盾疑點重重,大夥兒卻似著了魔般,只想揪出個人來殺頭,不管實際真相為何。」
許震海掏著耳朵,道:「眼下沒人關心真相了,兩個娃兒就不承認、不辯解,看誰的拳頭硬!」
藍渝樺不以為然:「這恐會引起眾怒……」「眾怒來得快,去得也快。」寧澈的眼底似有暗流湧上:「一旦爆出更嚴重的事,就沒空理睬與自身無關的人了。」
「更嚴重的事?」洪珺萱疑惑:「有甚麼事會比這些命案……」「大師姐、二師姐,我們來了!」盧筠甄的嗓聲驀然傳至,循聲回溯,除她之外,其身旁還站著一名紗帽覆面,黑衫裹身的女子,正是玄默散人。
二女相偕走近,盧筠甄滿面欣喜:「噫,真巧啊寧公子,你們也來買……」語未畢,身邊的師尊倏地一頓。
兀自奇怪,玄默散人霍然拔劍,劍指樹下老者,「許震海,納命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