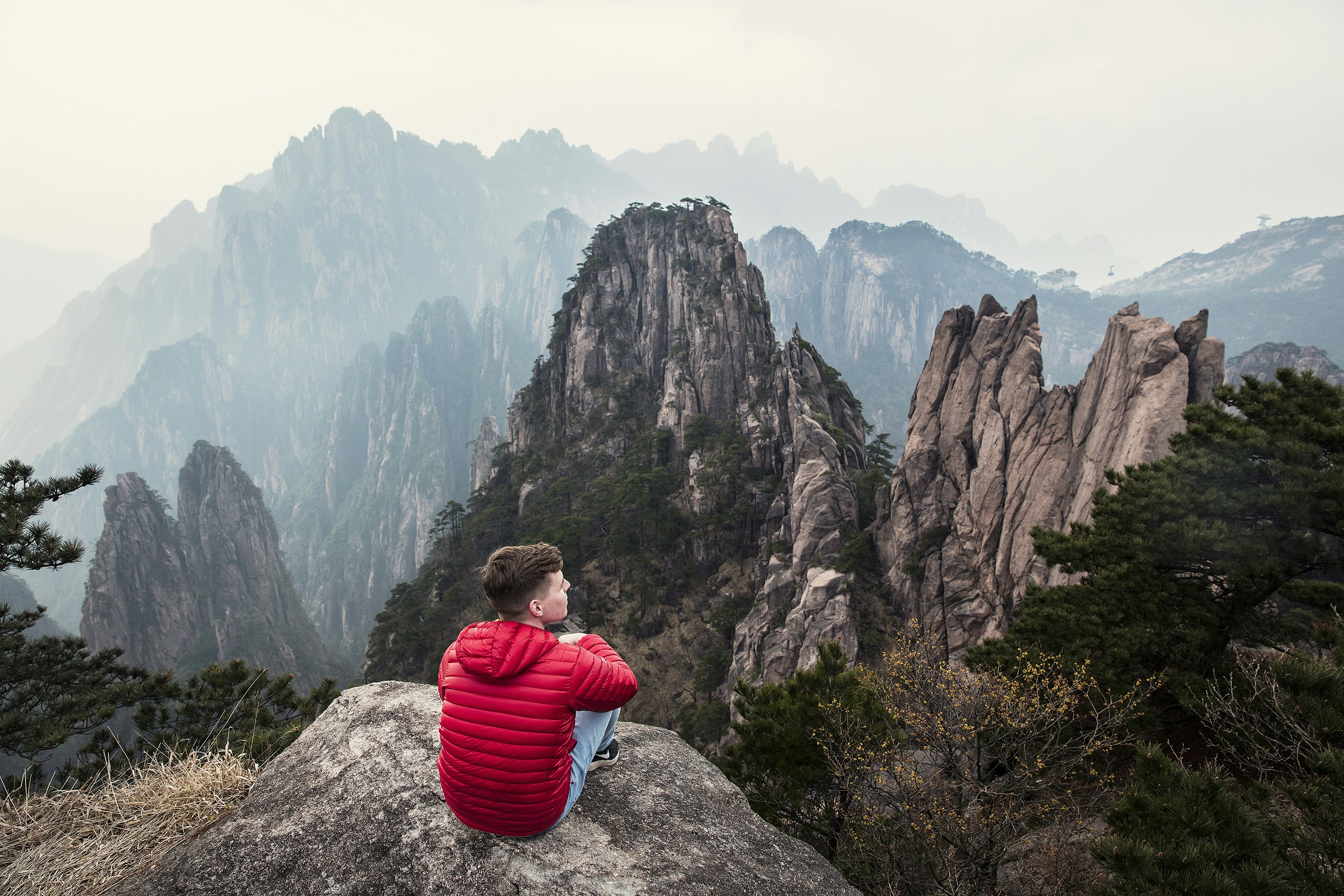送行
七歲的我總以為學校很遠,總是在校門口等待外婆騎腳踏車的身影,或是在家中催促著要去學校上社團課。被抱下娃娃座椅的我總是急著離開,回到有厚重電視機的家裡,或是有新鮮玩意的課後社團課,鮮少回頭對你說一聲「掰掰」。直到換我留在原地送你離開,才執意不斷的說明天再見。
十四年前的夏天還不像現在灼熱難耐,還覺得走路七分鐘遠的學校令人疲倦,所以那三五年間,我都在短暫的幾分鐘,隨著搖搖晃晃的路面,在腳踏車的娃娃椅上看著你的背影發呆。小學的我總感覺時間好漫長,好似永遠都離不開那堅實的堡壘,日常漫長的像永恆,像外婆有些泛白的髮根,黑色與棕色卻屹立不搖,把歲月停止在那六年。離開了凍結時光的城堡,晃眼就是三五年,下一次靜下心來看你,已經如小時候聽的「冰雪皇后」一樣,為雪白的銀絲覆蓋。這時騎腳踏車的後座已容不下我,我的學校也遠得得用汽車通勤。
小時候童年無忌,總喜歡說些「觸霉頭」的話,所以總是被你警告性的瞪一眼。小學生最喜歡亂講的「靠夭」、「靠北」一律不可以脫口,否則就是一連好幾句台語的念。高三那年,外婆的大兒子罹患肝癌,已經末期。我坐在餐桌前讀書,看著外婆拿著浸過符水的毛巾拍著舅舅的肩頭,顫抖的嗓音重複著「佛祖保佑」、「無病無痛」⋯⋯雖然無奈,卻也沒有人忍心拒絕這些。
最平凡的早晨,你驚訝我怎麼這麼早起,我則剛好趕上要出門的你。我像平常一樣說話沒大沒小,你也像平常一樣洋裝委屈,沒有人知道那是我們最後一次在家裡碰面。
先是聽說腦幹上方溢血造成中風,接著聽說腸子潰瘍。大家都盼著將要好轉的時候,B型肝炎猛爆,腎臟功能毀損,你卻說「我也已經活到 70 了,可不可以不要再拖了?」這樣晦氣的話。每一天喊著痛,看著逐漸泛黃的皮膚,我想別過頭,卻迫使自己注視。若不是這樣做,或許我會自私的對你說「別走」。
無效。不論科學化的醫療,抑或神學的三太子,都沒有辦法告訴我們該怎麼做。所以時間沒有停下,我回想起在國軍公墓,你說阿公右邊的位置是給你躺的,你看著墓碑哭泣的樣子也歷歷在目。好幾次,你送我上學、送我回家,這一次,我等不到你回家,只能送到讓你無病無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