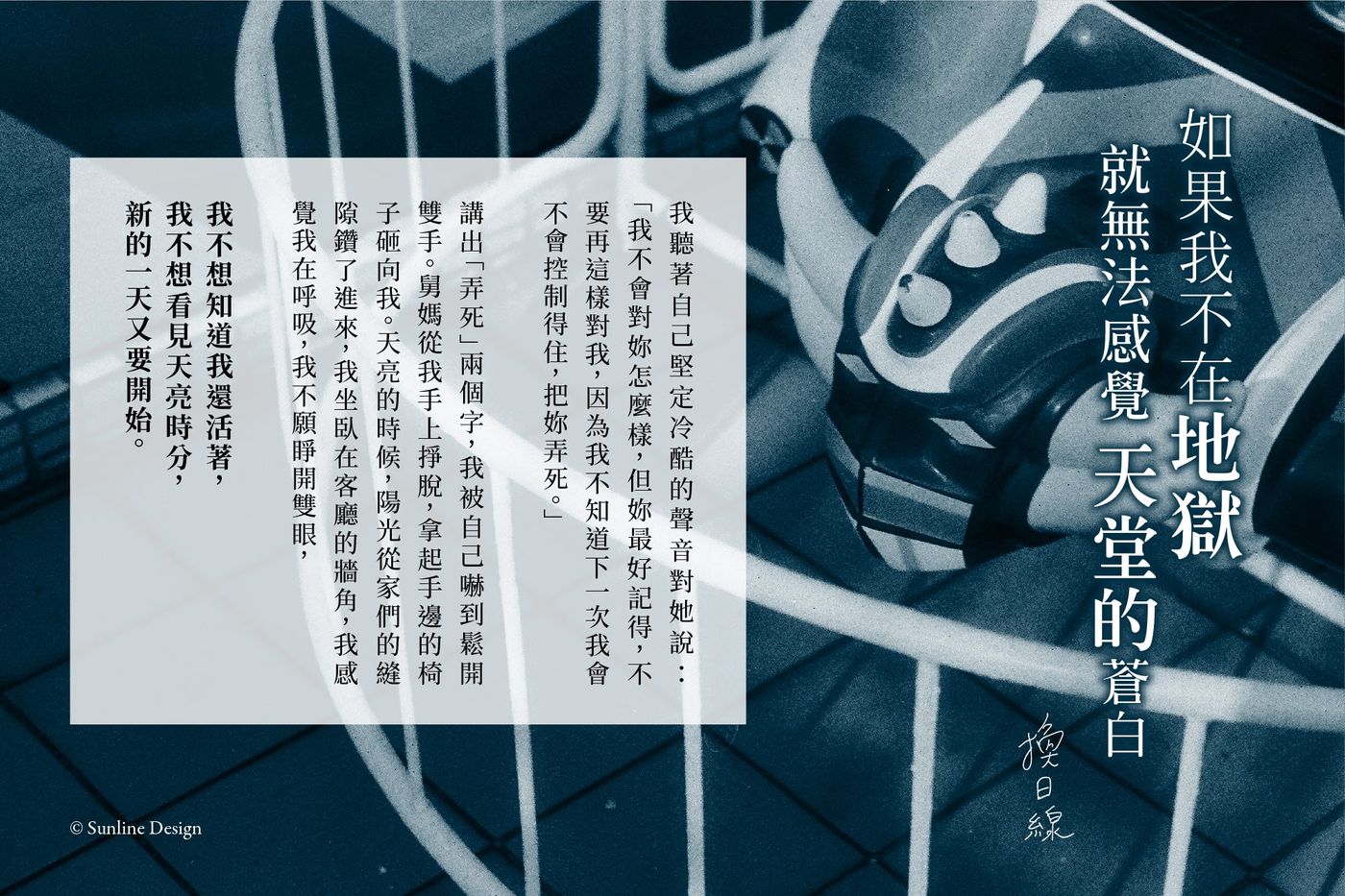|附身:旋轉,張開,躲起來
沿著路走。沿著人行道蜿蜒爬行的裂縫,像踩一條蛇那樣往前,經過第一個街區,然後第二個,找到那條巷子,找到那棟樓,找到正確的樓層(同樣是兇險的十三樓,正平行於這個位置,這個露台,直直看過去能看見)。找到兩扇鐵門,右邊。
P和P’。如果把那對雙胞胎從他們各自的公寓裡揀出,排列起來,將脊椎對齊,重合,像失散的字母,你會得到一個相逆而對稱的形狀,一只鑰匙。
你如果嘗試將鑰匙反握,你其實可以旋開對面那扇門,進入一座裝潢擺飾格局皆相同的公寓,遇見相同的男孩,微笑著坐在那裡好像在等你回來。那一定是一開始的選擇而已。關於握住的手法和方向。碰巧是P,就只是這樣。不應該責怪太多,但你仍必須知道那反面的存在。否則你會走失的。你會使某些人恨你,或者非常、非常傷心。
・
我們回到那個入冬的傍晚。
P也曾用他的鑰匙打開枚(向上、向上)。在那昏暗迷離、光線虛無的公寓裡,他緊緊親吻枚,扣上彼此的脊椎,手指上滑,向下。輕柔摩擦,默記對方所有光滑的骨節。
而你就在外面,背抵著P關上的鐵門,以一名跟蹤者的姿態瘦弱地竊聽一切穿透、發生。那時枚的背仍乾淨白皙。兩具身體交錯撞擊出白色的音節。你把音節收進耳朵,吞入肚腹,想養出一條相同的聲帶也似。啊,我愛你,我愛你。
你的聲音在那空空的迴廊像遺棄的空瓶。沒有人想將你撿起,張勤。
你盯著對面那扇一模一樣的鐵門。頭頂的日光燈突然熄滅,窗景黯淡,冬天的風擦過你的身體,潛入身後的鐵門。你聽見P和枚閃爍的聲音,像碎玻璃被殘忍地踩進你身體。你聽見一場大雨砸落如樓頂墜落的人影。
天暗得很快。你像個不耐煩的影子再也等不下去了。你站起身,等電梯時在右邊的鐵門前停了好久,直到你看見玄關有燈亮起,腳步聲急切接近(你有種錯覺那是個和你同樣悲傷孤獨的人),電梯恰好抵達,你急忙踩進去按下樓,像躲進一雙張開的手掌。
你濕著身體橫越那條尚未積水成河的馬路,景色和樓都在顫抖。你回到宿舍的十二樓,關上十二月的窗。
學姊點完名後你幾乎確定她不可能回來了。然而在那個清晨你習慣性地起床寫劇本,她剛好回來,看起來異常平靜而空洞。
你卻有種失望的感覺。在她脫下上衣更換制服時,你背對著她,在紙上把你最愛的角色寫死。
.
而現在,我必須告訴你我做了什麼。我把鑰匙反過來,放進她手裡,在她抵達十三樓時,在耳邊告訴她是左邊的房間。右邊的人等了她一整個晚上。
錯誤的房間。正確的命運。我很難過我是站得最高的那個人,必須注視和賜予一切情節發生。
就像你跟我說過的故事,暗算,偽裝,進入是為了互相取代。我幫你完成一切,接著我離開這個悶熱而孤寂的頂端。
這沒什麼不好。三月時我會給你我的刀。
我只是同情你,親愛的張勤。
|慈悲
羚又來到這個陽台。她曾在那麽多的白日和黑夜,抽著菸在這十三層的頂樓,照看一切發生。她目睹她們抵達,簽到,分配房間(她那時候沒心情下去打招呼:大病未癒的邊緣,仍太過灼熱,憂傷),羚試著把她們每個人的名字都背起來:張勤,段喬,劉子晴,習慣音節穿過嘴腔的質感(她太久沒說話了);在這個角度羚能看見喬頻繁來回於宿舍和對街巷子裡的公寓,以及張勤跟蹤著喬,兩個完全相同的男孩;她看見喬和子晴並肩走去很遠的地方,再返回。回程保持沈默。
羚看見大河淹沒,其中一個男孩一步一步走進水裡,接著一瞬間就陷下去了。
羚像個無比慈悲的神,流下一滴淚。
羚把手上的菸壓在石製的圍欄上捻熄,逆時針旋轉。吐出的最後一口煙霧已經消散成天色。她越過圍欄,張開手掌,將揉碎的菸蒂向下擲去。
張開手掌給予她們名字,就像她之前被給予的。阿時,枚,張勤還是張勤。張開手掌給予他們命運和意義。
像掏空身體。她凝視著遠方好久,最後回到腳下看著逐漸褪色的影子,直到手指也變得透明,感覺自己很輕。
|《斷橋》
「(第一頁。四個女演員。靜止的群眾。)
(黑色衣服的女演員由後方進場,走進無人的舞台中央。對著很遠很遠的地方,聲音像旁白平淡)
女演員:恨是怎麼產生的?起初絕對是愛,嫉妒,悲傷,然後才是恨。而要如何結束?我的意思是,仇恨是會瓦解的嗎?當恨一個人像過大的水壓,終於越過某個臨界值時,水缸炸裂,碎片四濺,碰,突然之間一切就消散了。你會渴死在乾燥的空氣中,可是感到非常、非常自由。⋯⋯
|贗品
枚的背上多了四顆鈕扣。枚睡得很沉,纖細的一雙腿在床框外平靜懸吊著。
而桌前她正安裝好另一副瞳孔。塗抹臉孔,填補凹洞。在手心捏軟一塊土,小心捏出新的鼻頭和眉骨,挖掉多餘的臉頰。輕刷陰影血色,點上白粉,壓實,宛若天生。割掉原本的眉毛,畫上新的。新的唇色。枚不在時她已練習多次,化妝仍像掩一座墳,原本的身體陷下去,躺上新的人。
驅離鬼魂。新的枚在鏡子裡看著枚。枚的眼睫,枚的雀斑,枚的削瘦。練習拆卸衣服的手勢,展示粉刷後的皮膚,找到角度。
偷竊的成果。可是我,我偷不了妳的鈕扣。她轉過身盯著背後由上鋪懸下來的兩隻小腿。枚爬上枚的床梯,將枚的小腿折上去,蓋上棉被。假裝沒有人在這裡。
而現在該去赴約了。她轉開房門,凹下去的鎖鈕應聲彈起。
|一種對折
應門的他彷彿早就知道她會來,他露出笑容。她曾在腦中排練過這幕多次,包括他笑起來的各種弧度。他擁抱起來比想像中還柔軟,還要潮濕貼合。
潮濕貼合地親吻。他的手指熟練地撫摸她的脊椎,一節一節地向下,向下,輕柔如飄浮讓她想到宿舍的電梯。
向下。她的笨拙快被看穿。
他停下。
「我知道妳是假的。」
但他並沒有鬆開。她聽見關上的窗外沒有風聲。
「但我也是。」他滑過她缺乏鈕扣的脊椎,溫柔得非常珍惜。
我轉錯了彎,拿反了鑰匙。她想起枚回來的清晨在阿時的懷裡低聲哭泣。她想起十二月的傍晚她坐在外面,盯著對面,一扇一模一樣的鐵門。
然後他們激烈擁抱如一種對折,重複開閤。
|回程
門一打開阿時就在那裡,滿身菸味。「我們走吧。去看橋。」沒有鈕扣的枚說,對著阿時微笑。阿時說好。
電梯叮一聲抵達,敞開。「我帶路?」枚問。「也只有你知道怎麼去。」阿時說。枚踏入電梯時看著鏡子裡的自己看了好久。一隻手滑入口袋,摸到一只刀柄,握緊。
「這樣問可能很奇怪,可是我看起來,像,我自己嗎?」
阿時瞥了她一眼。「其實我不知道。我越來越不確定你是什麼樣子了。我是說,我也開始不明白自己。這不是你的錯,不是我們的錯。」
電梯屏幕上鮮紅的箭頭一路向下,向下,向下。像一種失足墜落。
|長夢
四顆鈕扣的枚在過度曝曬中醒來,做了一個很長、很長的夢。
夢裡她有一具健康嶄新的身體,背上不再鑲有鈕扣而輕盈無比。她感覺自己浮了起來,由她的上舖穿透長著壁癌的天花板,上升,上升,她離開十二樓,在十三樓的露台張望,腳下的影子已遠離自己近乎消失。
而她看見她們兩人從宿舍走出,像是從她的身體出發。久違的枚和阿時,在前往橋的路上。她們並肩踩過殘缺的人行道,路過一整列關閉的店,小心迴避沿路的積水,她們都還是非常乾淨、乾燥的人,還不想弄髒自己的任何一部份。
阿時一定以為他們要走進騎樓於是堅持直走。她說不對,阿時,往這個方向。她走向人行道邊緣示意阿時,阿時用一種非常訝異的,接近恐怖的神情看著她。
妳先不要那樣子看我。
她一腳踩進水裡,氣泡從水底沿著腳踝爬出水面。再真實不過了水的涼意浸溼她的知覺,她仍十分決然地踩下一步,一步,再一步。而欠缺所有下陷沈淪的跡象。
(這真的是我的夢嗎還是某種已然或者勢將逝去的真實——四顆鈕扣的枚駭然於一切相似,包括那水蝕進身體的寒冷,那人行道凹陷破碎的形狀。)
跟過來啊。轉身對著阿時大笑。陽光灑落,她的眼睫閃爍發光。
旋轉起舞。她突然理解P為什麼要渡河。為什麼要走進水裡,把自己推離岸邊——
為什麼P在那裡他們相遇認識回到他的公寓。
——為了這樣遙遠的抵達嗎?
她想起P第一次非常怯懦地親吻她的臉頰,在他巢一樣的公寓裡雛鳥也似。她嘗試將他深深地抱近自己,貼緊他的背脊。他們一起凝視窗景。P轉過來跟她說:
對不起,我想我還是認錯人了。
那天晚上她在P身旁熟睡但仍然有夢,夢見自己回到宿舍,看見張勤對著鏡子化妝。張勤轉過來看著她的位置,她驚恐地發現那張臉和她完全一樣幾乎是剝下來的。她突然明白一切了。她好恨張勤。
阿時,妳知道嗎,根本沒有那座橋,那是我的謊言。我們總經過這個街口,打消主意說下次再去。你可以恨我。我只是為了讓她看見,讓她以為我們去了很遠。
讓誰?讓張勤。
讓頂樓的那隻鬼。發高燒死去的那個女孩。記得嗎?她原本就住我們對面。她才是走錯房間的。她把所有我的事情都告訴張勤了。我知道。我確定張勤會很痛苦,我也隱隱知道我自己的結局。可是妳知道嗎?我已經不在乎了,非常殘忍但我不在乎了。
她繼續前行。河水拍擊她聽不見身後阿時的聲音。空氣中有種辛辣的鹹味。她越走越遠,越走越輕,然後她發現自己離開水面,懸浮在大河的上方,盯著河裡的自己一步步濺起水花渡河。她看著她代為指使她的身體。
她看著P。他們相遇的時候。他就坐在那裡,姿態平靜。
(平靜像是他說,深呼吸,我要縫第一顆了,不會很痛,就只是向下,向下。)
(然後我們擁抱。)
用力擁抱。用力握緊手裡的刀。她在空中看見翻覆的浪洗去枚的臉孔,留下模糊不成形的張勤。張勤向前跑去,抱緊了正起身臉露詫異的P’(代她指使她的身體。)張勤反手將小刀刺進P’的反面,將P’的身體更努力地貼緊自己,狠狠地向下、向下,割開一具偽造的愛人;割開偽造的自己。她剝出P’的脊椎,脊椎血淋淋地橫躺下來,她身上披掛著他泥濘破碎的剩餘,刀尖指向心臟。
阿時瞬間發出無聲,鮮紅而透明的尖叫。
她聽見光芒撤去,烏雲翻騰,遠方的雷砸向她也有溺死的感覺。她突然什麼都看不見了。
窗外下起了一場滂沱的雨。枚從沈睡中猛然驚醒,整張臉被淚水浸濕,身後的鈕扣頓時脫落,有如曬乾的沙子。
|獨幕
雨停之後段喬第一次出門,第一次一個人,就一個人。天色仍然陰暗,但她沒有帶傘。一整條街都關閉,騎樓漫著死寂的水窪,她經過長牆一樣的鐵門,門裡佈滿皺褶的倒影沿路緊隨著她。在殘缺的人行道上踢到一塊隆起來的磚。她很快就走到熟悉的巷子對面,折進去走到底是他的公寓。而她不打算橫跨過去。
馬路上一台車都沒有,積水肆意漫流顯得突兀。路上陷落幾道裂痕,提醒她這還是三月,還是非常乾燥的天氣。難得有雨,難得空氣中有海瀰漫。
她繼續往前,越過這個街區,直到他發現對面人行道有什麼東西掉在那,亮晃晃的。她遲疑了一下,還是穿越了馬路,猶習慣性地看向左右確認來車。她撿起來。
一把乾淨的小刀。
奇怪的是不遠處掉著一只鞋,浸滿了泥巴看不出原本的顏色,看起來是從好遠的地方沖刷下來的。
段喬突然決定不往前走了。好像深怕自己還會撿到一只一模一樣的鞋,她會真的想帶走這雙鞋,仔細洗淨,曬乾,懸在床邊。
她回到房間不久天就全黑了。戴眼鏡的學姊敲門點名,通知。明天一切就會恢復了。學姊這麼告訴她。
都在?
都在。
學姊關上門後她打開抽屜,裡頭放著一本灰色的筆記本。她翻開,那是一部已經完成的劇作,獨幕劇,第一頁的角落鑲著細瘦的字,《斷橋》。篇幅不長,她卻花了很久才讀完。她找到最後倖存下來的那個角色,拿出口袋裡的小刀,在心臟的上方輕輕刻下了那個女孩的名字。
而很快又要四月。
她嗅到煙味,她知道羚要回來了。
2021.04
/後記
你知道嗎有好長一段在城市的時光,我每天入眠前最後一件事都是仔細在腦中排演這個故事。幾乎搭建出一座舞台懸浮在長有壁癌的天花板上,人影晃動,面目模糊。床下猶有話語她們壓低聲音交談,輕笑著。我突然很害怕這個故事的原型其實這個房間和我自己。
「妳有沒有產生過一種,想要狠狠地傷害某個人的衝動?我是指,只是看到路邊一個不認識的女孩,卻想用手邊最接近兇器的物品,從背後靠近她,舉起手,用盡力氣砸破她的頭顱。你有沒有過這種感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當我開始有這種想法的那天開始,我口袋裡總摸得到一把刀。
「我不知道。或許只是我昏頭了。天氣太熱。是天氣逼我們的。」
這段對白是故事的開始,最後還是被我捨棄了。現在讀來卻覺得貼合無比。或許應該停在這裡就好,我寫得太多了。一萬餘字是什麼概念?手裡玩弄的一萬餘字像捏不好的土,由指縫不斷、不斷滲漏,漏成一條遙遠的歧路。原先已經構想好該如何慎重,儀式性地刊登,然後小說就寫壞了。儘管我還是很喜歡這些複雜的聲道最終聚合為一的效果,但是前面的結構有種拼貼過頭之感。於是這個構思許久的作品被隨便命名,敷衍對待了,胡亂切成三篇但不認為有人會逐篇讀完。
回到故事。在宿舍的時候我偶爾會討厭她們,那種被瞞著什麼的感覺。「如果你討厭誰,就把他寫成段子。」前陣子喜歡的脫口秀演員說的。如果你討厭誰,就把她寫進小說作為報復。連枚這個名字都是偷來的。真正的枚會看到這篇嗎?我感到抱歉,因為她們不是那麼壞的人啊。我曾經想過要在小說裡加上比較溫馨的一段:四個人包含羚在鎖上的房間裡交換秘密,大笑,脫去身上的一切衣物飾品,同時上床入睡。但這代表之後不變的情節將更加殘忍。我寧願她們沒原諒彼此就撕裂,因為在真正的,這個房間裡,只有無奈甚至虛偽的不斷原諒。
書寫恨這件事其實是為了原諒嗎?
容我抄錄一段巴特勒的文字:
與此同時,依照這個邏輯,即使過去曾經因為攻擊傾向吞噬了各種從善的努力,一種曾經不是、或永遠不可能是好孩子的人,如今都能夠成為好孩子。因此,當置身於克萊恩所謂「真誠的同情」時,我也正在努力彌補我的傷痛與委屈、甚至是為自己贖罪。⋯⋯我努力重建那些被我丟失、或者從未擁有的事物;或試圖與我所犯下的罪、抑或是想摧毀他人的衝動和解,即便這種衝動只存在於幻象之中。我的同情是否是被我自己的失去或罪惡感、或是從幫助他人的過程中與他人共享的快樂給激發出來的,其中「我」和「你」之間也許並沒有我們所想的不同?如果他們會彼此共享,那麼它們到底分享了什麼?還是它們最初被幻象給部分掩蓋了,而它們最初也是幻象的一部分?
〈長夢〉的刺殺場景是源自於一個夢。夢裡那是一個毀敗的末日城市,殺戮之間並沒有恨或是任何意義,就是見人就殺那樣輕易荒謬。夢中我也是旁觀著,像阿時一樣看著朋友笑著將陌生人的背割開,拉出長長的脊椎再被持刀然後被仍未死的對方刺入心臟。不追究邏輯上的矛盾去解讀,這個場景中的暴力是扁平麻木的。然而在小說的最後同樣的場景被填充了某種有點哀傷卻無比真誠的償還之情:我不知道我是否有真正透過小説闡明我想說的,巴特勒式的和解與原諒。那明明是明顯矛盾的這樣柔美的一種情感以如此殘忍的情境解釋——卻是我整篇小說少數滿意的地方。
後來線上課程的演練讓我們都短暫離開那個房間兩週,而因為疫情加劇讓一切延期又延期,我們才意識到這就是最後了。不會再一起住,不會再因為生活細節的衝突而討厭彼此了。假如枚也有要搬離宿舍的那天,她會想起阿時,張勤,甚至是羚嗎:她會不會終於覺得,自己在這個房間其實非常幸運可貴。她的未來裡那些曾經的憎恨,都將會成為一種充滿悼念意味的珍惜。
這就是最後了。身為一個糟糕的小說作者我必須寫這麼長的後記來解釋自己的作品,抱歉閱讀過程中所有的混淆不清及造成的迷惑,但仍然感謝讀到這裡的你。
*摘錄內容為Judith Butler《非暴力的力量》,近日非常推薦的政治哲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