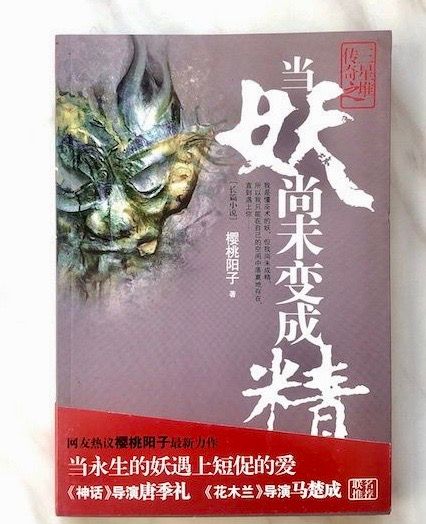原文首先刊載於關鍵評論網
對於沒有獎項烘托、名人加持、行銷銀彈支援的本土大眾小說作家而言,竭力寫成八到十萬字出一本書,卻只收到幾千塊版稅,是常有的事(因此可以理解為什麼寫不下去的人這麼多)。
蘇偉貞《租書店的女兒》,第二人稱說起開租書店的父親,從小讓她得以悠遊在金庸與瓊瑤間;而寫作,大概是種自覺,讀遍了大眾小說以後,興起一股「也許我也能試試」的念頭,卻又不滿足於大眾小說的流於公式,比如愛情除了「他愛她但她不愛他」,還可以有別的什麼?於是,彷彿踩著階梯,志文經典文學系列簡直開啟新宇宙,原來,這是文學!
對寫作者而言,純文學與大眾文學並不互斥,但養成路徑及終極目標卻大相逕庭。左轉純文學,追求榮耀冠冕、承載思想洞見,企圖在作品的語言/形式上進行各種突破;右轉大眾文學,追求掌聲與銷量,最大目標是把故事「寫得好看」。我無意將它們二元化,粗暴批評純文學作品不在乎易讀性、大眾文學不具備藝術高度;事實上,這兩個方向都可能相互擁有彼此特質。
對渴求「好作品」的讀者來說,差異不大;對寫作者而言,向左向右,關乎個人能力傾向、如何努力,特別是在很容易成為「憤青」的年紀,總有一派人鄙視大眾文學對市場的彎腰獻媚,另一派人則譏嘲純文學根本是小圈子裡的人彼此追捧。
文學性與故事性
比如一棟房子,你可以分析它的結構耐不耐震,管線拉得合不合邏輯,甚至拿把放大鏡沿牆面審視油漆工的技術是否扎實;有個空間,你打開門走了進去,覺得它安全舒適、使你放鬆,卻又可以在許多細節或角落引發你的好奇與興趣。純文學小說在乎的「文學性」便是這樣一種空間。
而大眾小說在乎的「故事性」,旨在說出一個好看的故事,它由縝密的情節衝突、立體的人物設計、精準的對白、節奏穩定的「演」與「說」這些元素共構;故事性在讀者全心投入、與主角共感,一頁翻過一頁迫不及待想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的時候體現。
對寫作者來說,故事性是更易複製與檢驗的,你幾乎只要丟給一個受眾正確的熟人讀者(比如你寫BL,這位讀者至少得對這個類型有涉獵),他直觀的好不好看,幾乎可以以此檢驗你作品故事性的強度。
文學性頻繁被檢驗的地方是以純文學小說為訴求的文學獎評審現場,評審多半是閱讀經驗豐富、自有一套審美標準的專業讀者;事實上文學性更強地與讀者的閱讀及生命經驗相關,比如近兩年連奪大獎的作家林楷倫,便是在題材的特殊性上使人耳目一新。相對來說,當小說主題是「高中初戀」這樣一個人人皆體驗見聞過的事件,會更難彰顯作品的文學性。
當然,它們也並不能「非A即B」地二元化。
跨界如何可能
2011年,陳栢青以葉覆鹿為筆名,寫作《小城市》拿下九歌兩百萬小說獎榮譽獎;九年後,《尖叫連線》出版,一次訪談中他坦言,曾有朋友勸他,你這樣寫,純文學圈不當你自己人,大眾小說圈也不當你自己人,等於兩邊不是人。陳栢青被視為純文學作家,然而當他以類型小說為框架、純文學為內核交出這部作品,企圖心驚人,只文學作品的積澱與影響力的滲透擴散需要時間證明,暫不能斷言後勢如何。
邱常婷以《怪物之鄉》出道,其後出版的作品包括少兒及類型小說,直至《新神》入列聯經當代名家,展現打磨多年、藝業驚人的說故事本領,而後《哨譜》同樣也是一部武俠與純文學交融的作品。
大眾小說的困難可能更多的是在「怎樣的故事可以吸引讀者掏錢買書」(於是寫作必須迎合市場口味)、「擁有更多讀者與銷量」(行銷策略和預算、繁體中文市場對比簡體中文根本OO比雞腿的讀者基數);純文學小說與之相比,有更多的空間讓作家「自我實現」、「寫自己真正想寫的」,於是,對於說故事及小說技法已臻成熟的純文學作家而言,只要願意好好地「寫一個好看的故事」,跨界書寫難度係數較低。
那麼邏輯上來說,我想當職業作家,鐵定是要右轉選大眾的對吧?書賣得多才有版稅收呀,偏偏台灣書市的情況卻非如此。
台灣的出版市場與讀者基數
與日本出版市場相較,台灣可謂翻譯出版大國,近三年翻譯圖書占比將近25%,而2017年的翻譯小說在「小說」類別一項就占比達29%之多。但經過各種挑選標準進入台灣書市的翻譯小說,時常在話題、品質、銷量和種類上都壓倒華文小說。(此段引用自黃崇凱〈比較的幽靈〉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