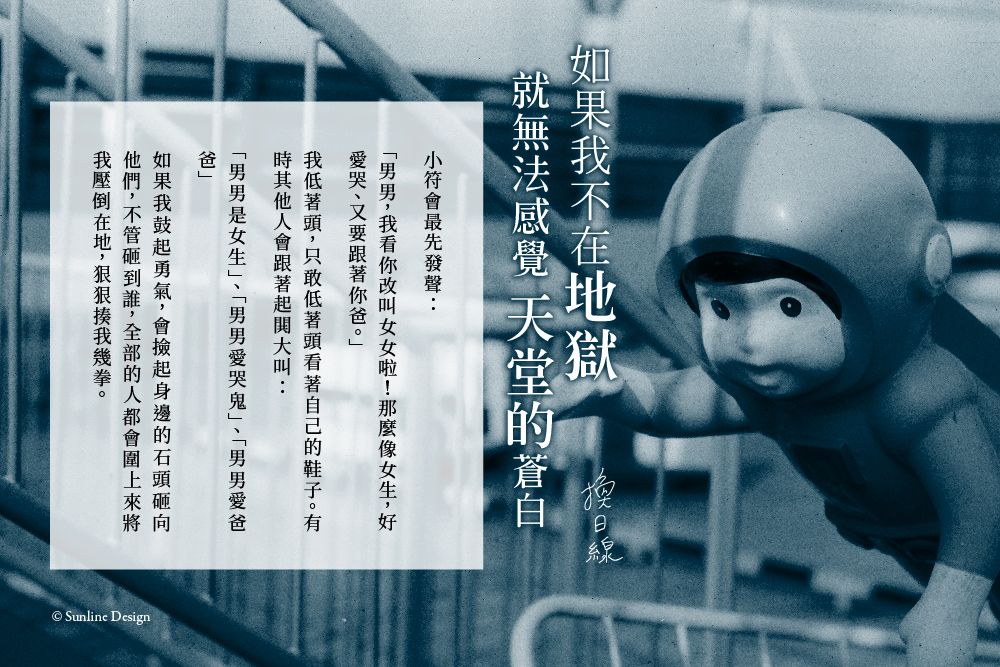她純白的制服襯衫在跑過路上街燈時折射霧氣,
在他眼底化成水融融的一道暖光。
從今以後,他成為少女世界唯一的解答。
寫給故事的結尾與開端。
願你我在低潮時都能收到神的包裹,讓心有所寄託。
濱海柏油路邊的這棟民房敞開著窗簾,落地窗邊正鋪著人形的毯子。整整兩個禮拜,這張膚色的毯子從日到夜都攤在這。整張濃密的體毛沿著呼吸的頻率震抖光塵,展開整間日光的升息往返。
在這個看似靜止的房間裡,聽來除了老舊冷氣機發出的聲響,還有一隻狗正掙扎著塑膠袋的悉索而汪汪地叫個不停。他卻失聰似的任憑狗吠不止。
他沉浸在自己的悲傷之中不可自拔,面朝湛藍卻怎麼也無法感染太平洋的海闊天空。在他雜亂無章的濃眉底下,兩輪血絲糾結的紅棕色太陽因為低垂的睫毛影子而墮落無神。
他不是沒有想過要爬起身振作精神,也許刷個牙洗把臉,或是從櫃子裡抽出一本書來脫離現實,但那些散落在房子各處的玩具,在他爬起身或轉過頭時總能一而再、再而再的擊潰他。
他孤獨地被卡在這棟民房的時間之流裡。
不知過了多久,白肚在海的彼面又翻過圓身,星光點點的圓背裡有顆淺藍的月亮因潛出海面正泡水般虛透身形。
屋內看似沒有任何變動,狗吠的汪汪卻戛然而止。他因此終於止住泉湧的淚腺,開始正常的眼瞼運動。一陣莫名的狂躁幾乎是同時襲來。
他猛地站起身瘋狂翻找空間裡丟失的聲音。
於此同時,柏油路上有一輛全新的紅色TOYOTA駛過他的家門到隔壁的老屋。
「到底為什麼要搬來這種鳥不生蛋的地方」後座穿著女校制服的她將眉頭皺比山高。
「什麼鳥不生蛋?在這至少不用忍耐妳爸的荒謬」母親從容的走下車,對著海洋伸了大大的懶腰。
她邊瞪向車外重獲新生的母親邊用力的推開車門,踹開擋路的石頭往屋子裡走去。
屋子不大卻佈滿溫馨,牆上掛滿母親的手作及她孩提時的美勞作業。櫃子上幾幀母女的合照,從很久以前她真心歡喜的肥嫩笑臉,到上個禮拜她不爽極致的雀斑側臉。
曾經的都市女孩如今正被迫桎梏在偏鄉海岸。
「妹妹,菜都煮好可以吃飯了」母親進門時的叫喊,讓她從樓梯掉頭走回餐廳。
「餓死了」她隨手將斜在肩上的書包丟往樓梯口。
「這東西是什麼?」有幾個快遞紙箱正堆在她的餐椅。她邊問邊把紙箱扔下桌。
「喔。」母親不在意的聳聳肩「是隔壁的包裹啦,郵差說是都沒人在家,懶得辦郵局遞交」
「隔壁都沒人在?」她的聲音帶高八度的質疑。
「對啊,我等等去按一下門鈴好了」母親端上熱菜,在她對面入座。
她點點頭,端起飯碗的手卻隱隱發抖。
「還是妳去啊?聽轉角阿伯說,隔壁住的是妳們學校的老師」
「是嗎?可是我在學校都沒看過他……」
「妳有看過隔壁鄰居?」母親驚訝的問。因為自己搬來這兩個禮拜都沒遇過隔壁鄰居一次。
她無視問題開始大口的扒起飯。
在母親眼裡她就是個正值叛逆期的少女。所以母親只是無奈的嘆口氣。
餐席間,母親趁隙夾了一塊肥肉到她的碗裡。
「多吃一點」話還沒說完,手機鈴聲兀自響起。母親瞥眼來電顯示。
「先吃、不用等我喔,媽媽去處理大人的事情」母親面露不耐煩地離開餐桌。
她聽見父母隔空的爭吵,看著碗裡的肥肉沒了食慾。視線順向地上的幾個紙箱。
等到母親解決完「大人的事情」再回到餐桌,位置上只剩她碗裡沒有缺兩的肥肉。
他跪在家門內,手裡捧著被撂倒在紅色透明塑膠袋裡的玩具吉娃娃,沒有下一步動作。
而她正巧晃進門縫敞開的光影之中,進退不是,只好開口。
「那個、你……還好嗎?」她的聲音帶著不安與窘迫。
他因為聽見久違的人聲而回過神。
仰望她圓潤稚嫩的臉龐,他望下自己跪姿並赤裸的中年體態、再望前她的女校制服。
她也順著同樣的視線,感到一陣尷尬。
「呃、這是你的包裹」她匆匆將手中的幾個紙箱塞往他家,要逃離這詭異的氣氛。
他反射性的拋下手裡的塑膠袋與玩具吉娃娃與收下紙箱。
在動作行進的須臾之間,兩人不經意觸碰到彼此的肌膚,再觸電般彈回各自的宇宙。
「BEST?FRIEND……!」他驚訝地看見紙箱謄寫的寄件方,不敢置信地抬頭想得到她合理的解答,卻只得到她慌亂逃離的背影。
她純白的制服襯衫在跑過路上街燈時折射霧氣,在他眼底化成水融融的一道暖光。
而她帶著怦怦的心跳躲回房間,鎖上門。
她的房間不大,東西多數還沒拆箱,有一扇大窗被框在牆上。大窗緊靠著她的書桌,桌面除了作業跟文具,就剩一管她從手電筒上拔來的單管望遠鏡。
大窗被輕推開一小縫隙,在虛透的月光照耀下正巧可以看進他家敞開的落地窗。
看見他抱著紙箱走回窗邊,她羞得趕緊將大窗關緊。
仰倒在淺紫色的單人床上,枕頭邊那幾本少女懷春的漫畫彷彿畫的都是她。
紅透兩面臉頰,她偷偷吻上自己剛才觸電的手。
從今以後,他成為少女世界唯一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