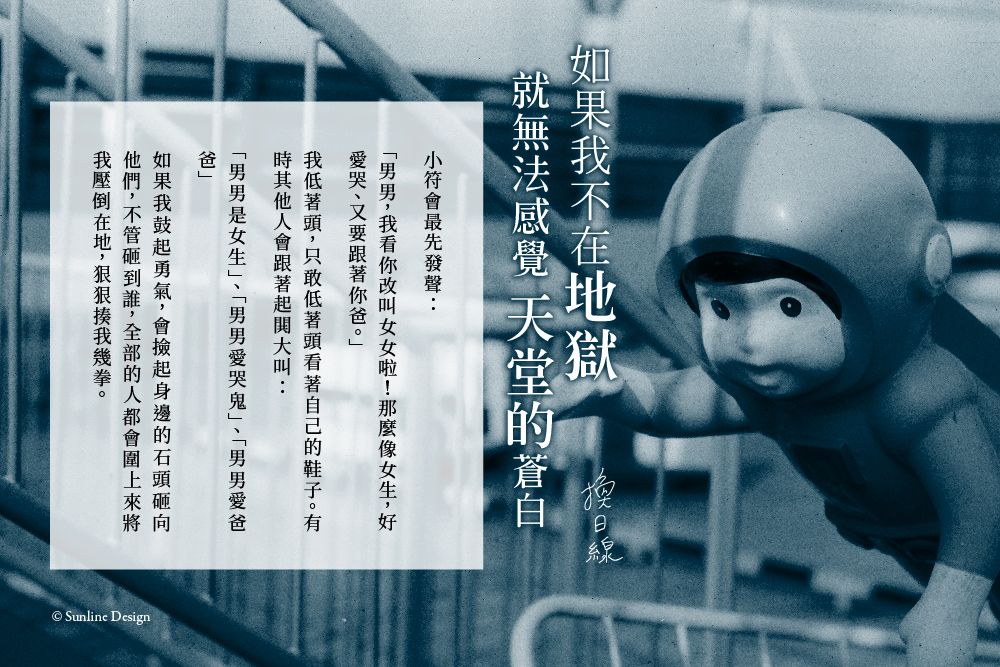是上輩子或這輩子的事呢?是自己的還是別人的呢?感覺意識與潛意識相擰成一艘無漿的獨木舟,生死一瞬地驚行在無情奔流的冥河之中,没有選擇,不能抗拒。左岸是神州烽火下的家毀人亡,右岸是妻離子散後的黃泉無伴;漂近時猶如利箭穿心,漂遠時宛如夢裡淌血;人鬼殊途的悔恨,就算是向地府閻王遞狀喊冤,怕也無緣再聞一聲陽世的殷切呼喚。

到底有多久没回來了?久到清水都變成了酒。清脆的金屬碰撞聲,來自手中的鑰匙串,宛如喪禮的輓歌前奏,催人心肝;很想叫它安靜,但似乎有一頭被情緒寵壞的猛獸,正發了瘋似的噬咬著鐵面具底下那塊最軟弱的肉,迫使他停不住顫抖。
轉開鎖,恍若隔世;推開門,難如移山。倏地,一團冷冽空氣迎面襲來,像是釋放了封印千年的雪妖,颳起陣陣風暴,令人瑟縮地想要躲逃。這個世界上,已經没有人記得這戶人家了,街道門牌,姓氐名字,早已隱埋在歲月的黄頁裡,連鄰居也失去了蹤跡,若不是律師交給了一串鑰匙,包括他自己,幾乎都要徹底遺忘、徹底遠離。地上窗影稍稍改變了位置,看得出太陽繼續緩慢地向西偏移,世界仍在運行,凍結的只有他的身軀。漫天風雪止息,所見不過是傳說中的塵埃精靈,因著他的突來到訪,一時受到驚嚇所引起的一片騷動。陋居中的一景一物,隨著塵霧淡去而漸漸分明,彷彿時光逆轉,現出了衰敗前的本來面目。
終於,他舉步維艱地往內深入,在急速呼吸聲的配樂下四處探尋,那副模樣,就像是迷路的孩子巴望著快點找到自己的雙親。從他那盈眶却強忍未溢的淚水來看,這房子似是與他有著非常緊密的關係,是愛?是恨?還是割不斷的血脈親情?他若不說,答案便要永遠埋葬在無名的墳塚裡。
老公寓裡飄起了細雨,雨水灑落的痕跡因塵沙四濺而顯得格外清晰。淚水瓦解了記憶的結界,耳邊傳來細微的聲音,但也只有曾經住過這裡的人才聽得出差異;有時是拖鞋踩地的脚步聲,有時是傾吐心事的竊竊私語,有時是逗得彼此開懷的咯咯大笑,如幻似夢般飄忽在走道和每個房間,彷彿那些離開他生命已久的親人都在,没有露面,是因為他們想給他一個驚喜,所以躲了起來。他急切的穿梭張望,不錯放任何可以藏匿的角落,來來回回,依然徒勞無獲。最後,他在父親臥室的門口,瞥見了一張歷盡滄桑的老臉,不禁呼喊了一聲:「爸」。
半响得不到回應,還以為是不肯原諒的故作沉默,怎知趨前確認的結果,映照在那斑駁殘鏡中的容顏,竟然是他像極了父親、與父親有著相同絕望心境的自己。
有一年,他們一家三口去到台南的古蹟「安平古堡」遊玩,那時他還小,見到父親一直凝視著遠方,良久不語,便天真的問母親說:「爸爸是在看砲台嗎?」

母親面無表情的回答:「不是,是再遠一點的地方。」
「喔!爸爸一定是在看那座燈塔,對不對?」
母親微微搖頭:「比那座燈塔還要遠!」
他訝異的瞪大了眼睛:「比燈塔還要遠?再過去不就是大海了嗎!爸爸又不是巨人,怎麼可能看得見?」
母親拍了拍他的肩膀,勉強擠出一絲笑容說:「比大海更遠,遠在海的那一邊。」
他正思索的時候,又聽見母親輕聲對他說:「如果有一天,媽媽不在你身邊,不是媽媽不愛你,實在是不得已,你要乖乖聽爸爸的話,不要學壞,不要惹爸爸生氣,等你將來長大,記得要娶一個好太太來照顧你,懂嗎!這些話不能告訴爸爸,只能放在你心裡,說不定到時候,媽媽會帶著你………」
某天放學回家,媽媽如同晨星一般,只在他剛懂事的生命裡停留片刻,隨即消失了蹤影,没有留下隻字片語,忘了把他裝進行李,空蕩蕩的一個家,從今往後,雖然少了夫妻的爭吵,却加添了孩子的啜泣。
打從亞當和夏娃生下第一個由精血孕育的人類開始,向來就没有哪個孩子懂得父母的感情事,為什麼結合以後又要分開?為什麼明明是在喜悅中生養了孩子,還可以狠下心腸抛棄孩子?《聖經》的作者也許不敢寫出真相,生養眾多,其實是苦難增多。上帝可能一時糊塗,在頒給摩西十誡的時候,漏列了一條「不得犧牲孩子幸福」的誡命,逼得少數孩子,就只能鼓起勇氣,堅強地面對光陰的潰傷,自行在稚氣未脫的童臉上,戴起了冷酷無情的面具。

場景在眼簾後方快速切換,靈魂一下子剝離,一下子入體;掩面癱倒,即便就這麼斷氣,也無補於被怨恨掏空的生命。一句「天哪!我究竟做了什麼?」道出了久經壓抑的歉意。如果說,人間有一顆心遭受了撕裂的痛楚,必然是在更早以前,有另外一顆心飽嚐了難言的悲苦。
或許是這狀似墜崖般的心境,讓他自然反射出求生的意志,本能的想要抓住些什麼;接著,奇蹟降臨,腦海中浮現一條搭救的繩索,是到此之前,律師將鑰匙交給他時所說的一番話語。
「你好,這是我們第二次見面,上一次是十六年前,為了辦理遺產繼承手續,這一次是為了將那筆遺產交給你。雖然只是一間老舊公寓,可也是你父親這一生僅有的積蓄,還有他想彌補你的心意。二十個年頭,真是好長好長的一段歲月啊!」律師忍不住有些哽咽:「你被關在監牢裡,你父親又何嘗不是關在他自己的心牢裡,他的苦絕不亞於你啊!不說你不知情,為了怕影響你,他主動斷絕與家鄉連繫,存下每一分錢供你受教育,盼得無非是你出人頭地。没有去監獄看你,不是氣你、怨你,而是重病臥床不起,寧可不請看護,早早死去,也不肯賣房子救命,心裡總是記掛著,萬一哪天你願意回來了,家却没有了,那可不行。」
律師語重心長的繼續說:「拿著吧!對你而言,這間房子代表的不僅是遺產,開大門進去的餐桌上,擺著一個木盒子,裡頭有一包你父親的骨灰和一封信;如今,我總算是完成了你父親的託付,接下來,就看你要如何處理。唉!生命有限,親情無價,一旦失去,人生就甚麼意義也没有了,希望你好自為之。」
啊!餐桌上的木盒子!他一躍而起,如熱氣球因點燃火焰充飽身體,瞬間離地,但也只維持了三秒鐘的興奮而已!木盒近在眼前,他却像座石雕僵住不動,右手懸在半空,周圍圈著烏雲,眼神呆滯如屍,無異是將歷史博物館中的某個蠟像展覽搬進了家裡,令人看了不禁感到一陣鼻酸。
隱約透著亮漆色的木盒,被灰塵掩去了光澤,宛如剛出土的古物,但又不具一丁點價值;此刻,這個在世人眼中毫無價值的古物,恐怕才是他今生最珍貴的寶物。

人在遇到進退兩難的時候,通常會被吸入時光隧道─他看見父親氣喘吁吁地高舉掃把,使勁地狠打在他的背脊,憤怒的咆哮中夾著喪子一樣的痛心。
「該死的!堂堂正正的人你不做,偏要做見不得人的鬼;大清帝國就因為受到鴉片的毒害,才導致一蹶不振,飽受八國欺凌的下場,你書都讀到哪裡去了!看在老天爺的份上,與其放縱你販毒為害,背負禍國殃民的罪名,還不如現在就打死你,當我没生過你這個兒子,免得將來眼見你被關死在牢裡。」
「夠了!」他没有反抗扙擊,不表示接受父親口中的道理,一把奪下掃帚,然後大吼反駁道:「該死的不只有我,還有你!在本地人的眼裡,你從來就不是近代史的悲劇英雄,僅僅是個外來的落難老兵,是個氣走自己老婆的没用老頭。我受夠了聽你一再重複的狗屁過往,我看不出你在不停地抱怨咒罵中得到了什麼!我之所以有今天,全是你一手造成的,你有什麼資格教訓我!想當初,你根本不該結婚,不該生下我,不該活在這片土地。只要我走出這個大門,你是你,我是我,你大可賣了房子滾回你的老家去,反正我不會再回來。……我是真的不甘心,不甘心老天欺負了你,還要欺負我………」
自從那天起,他父親失去了他的消息,而他也不想知道父親的消息,他認定父親必然會像母親一樣,悄悄拎著行李箱離去,這輩子再無可能相見了。
鐵窗外的月色,冷清;鐵窗內的人影,孤寂;失去盼望的等待,最是折磨。

展讀父親親筆寫下的遺書,悲極,慟極,好希望能有哪一位神明,可以改變這一場玩笑式的遭遇。
吾兒平安
容我借用耶穌的話語,因為我找不到更合適的詞句,而這也是為父最想要給你的東西。這麼多年來,你一定過得很辛苦吧!都怪我没能給你一個完整的家,没本事賺錢改善我們的生活。我知道你恨我,恨我没留住你媽媽,恨我用自己的牢騷扭曲了你的人格;不要緊,我不怨你,我想我和你一樣,都需要重新做人,一個在陰間,一個在陽世,好好反省。只不過,做人太悲慘,若是可以選擇,我倒希望我的來生是株萬年青。
如果你看了這封信,表示你還留著一點父子情,麻煩你為我做最後一件事,將我的骨灰沿著台灣海峽灑遍,這樣的話,不管你日後住在哪一個地方,我都可以隨著潮汐去看你。
等不及你回來,只好先向你說聲對不起,請原諒爸爸撐不住,最後還是撇下了你。永別了,我的愛兒!來世換你當父親,我做兒子,我保證不會讓你失望,絕不讓任何人欺負你。
懷著愧疚日夜思念你的老爸絕筆
老公寓被粉刷成裡外一新,屋內擺設却没有任何變異,惟獨陽台上多了一盆萬年青,在陽光溫煦的照拂下,展現旺盛的生命力。
有時,悲慘的人生,不是因為生命失去了盼望,而是不懂得在失去盼望底下,活出新的生命。
他半趴在陽台的欄杆上,凝視遠方,不時伸手撫摸萬年青的葉子,印象是好久以前父親的背影。安平古堡的風景已渺,深刻的是對家的感情。驀然,前方更遠更遠的視線忽而拉近,兩行熱淚潸然落在萬年青的葉片上,滾動成碩大的水珠,水珠晶瑩如鏡,倒映著一張卸下面具的臉孔。此時,天空有幾隻灰鴿撲撲飛過,恰巧聽見他大徹大悟的說:「錯過了上輩子和這輩子,下輩子不論老天的安排是什麼,我們都要好好的過一輩子。爸!我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