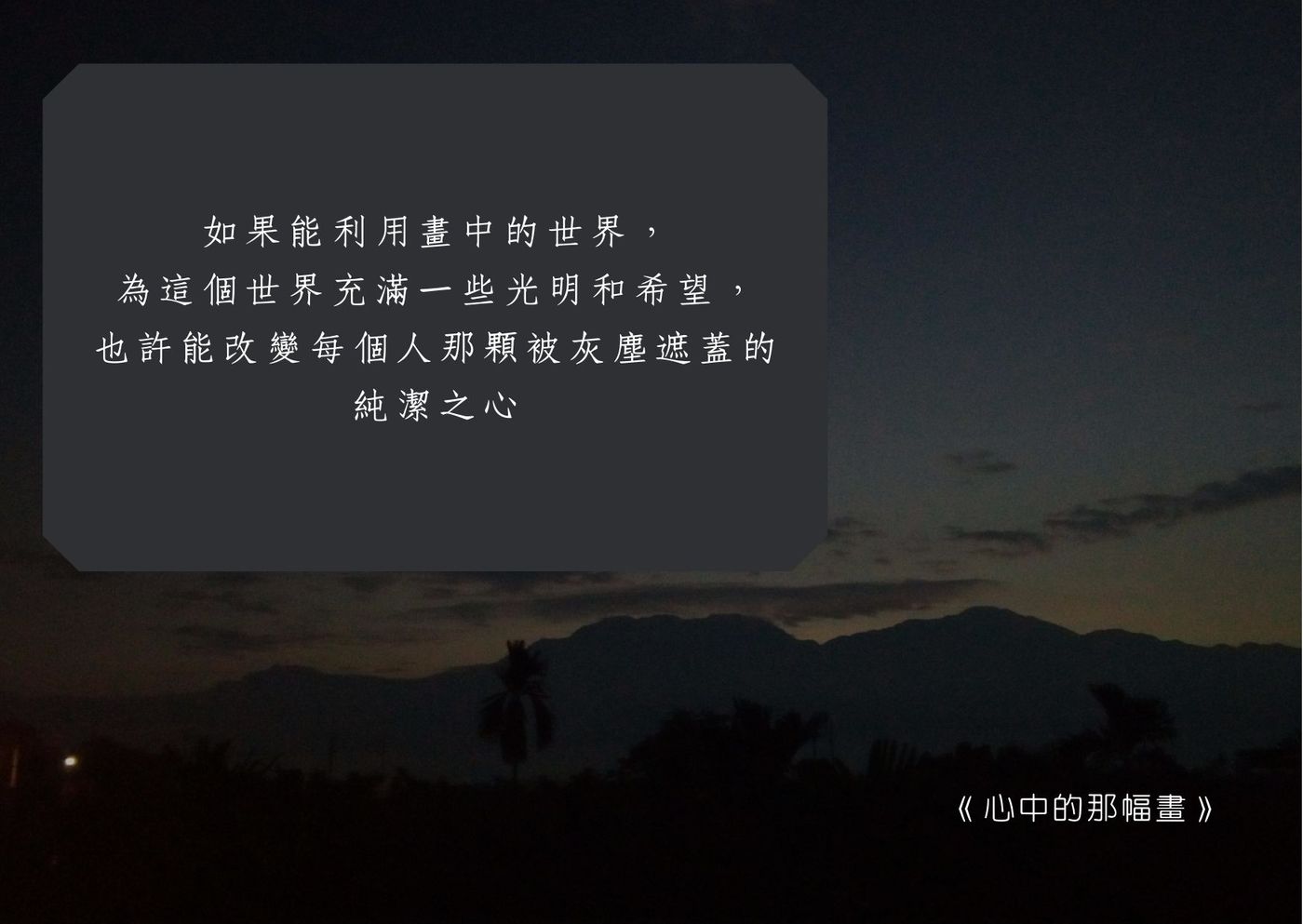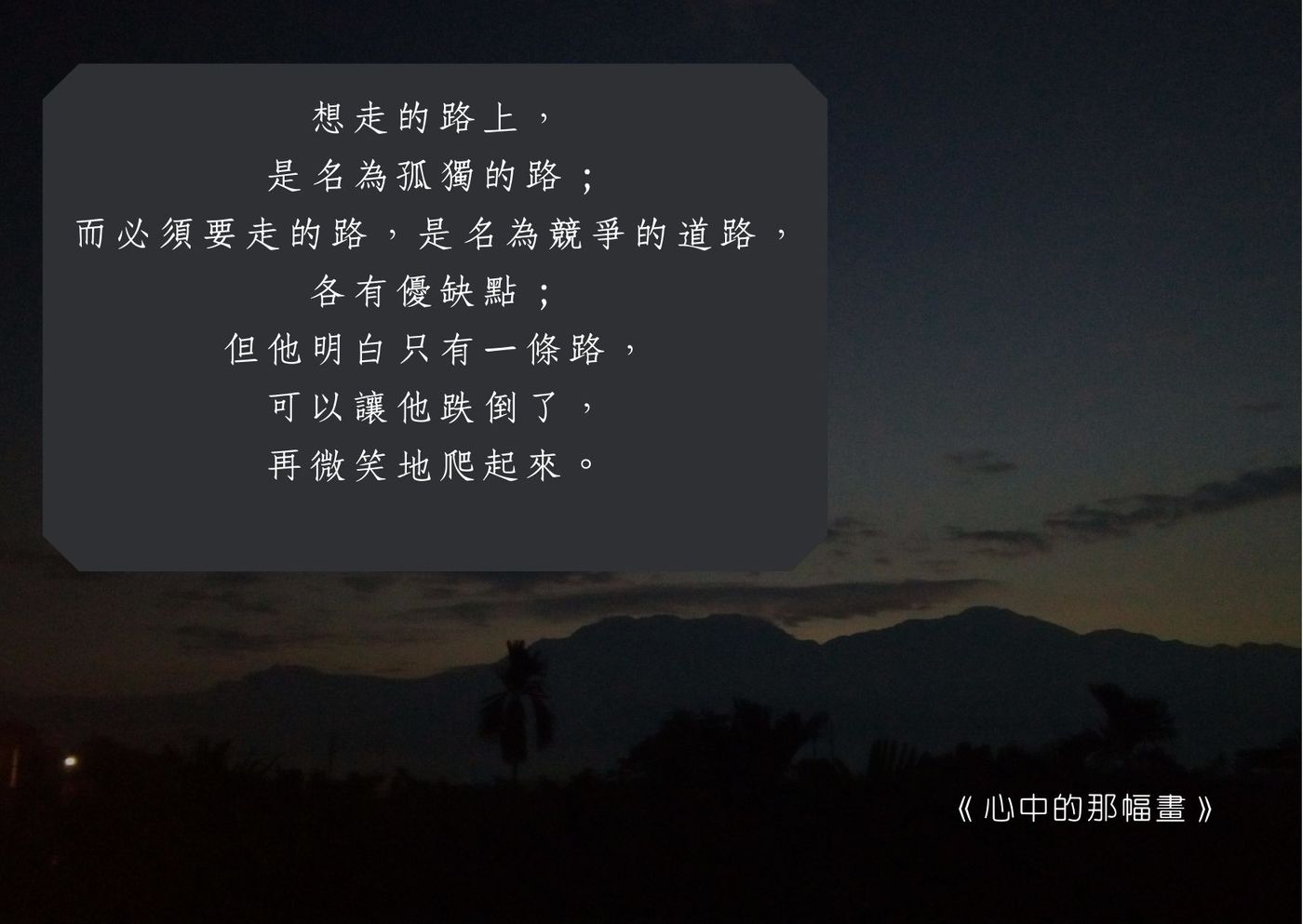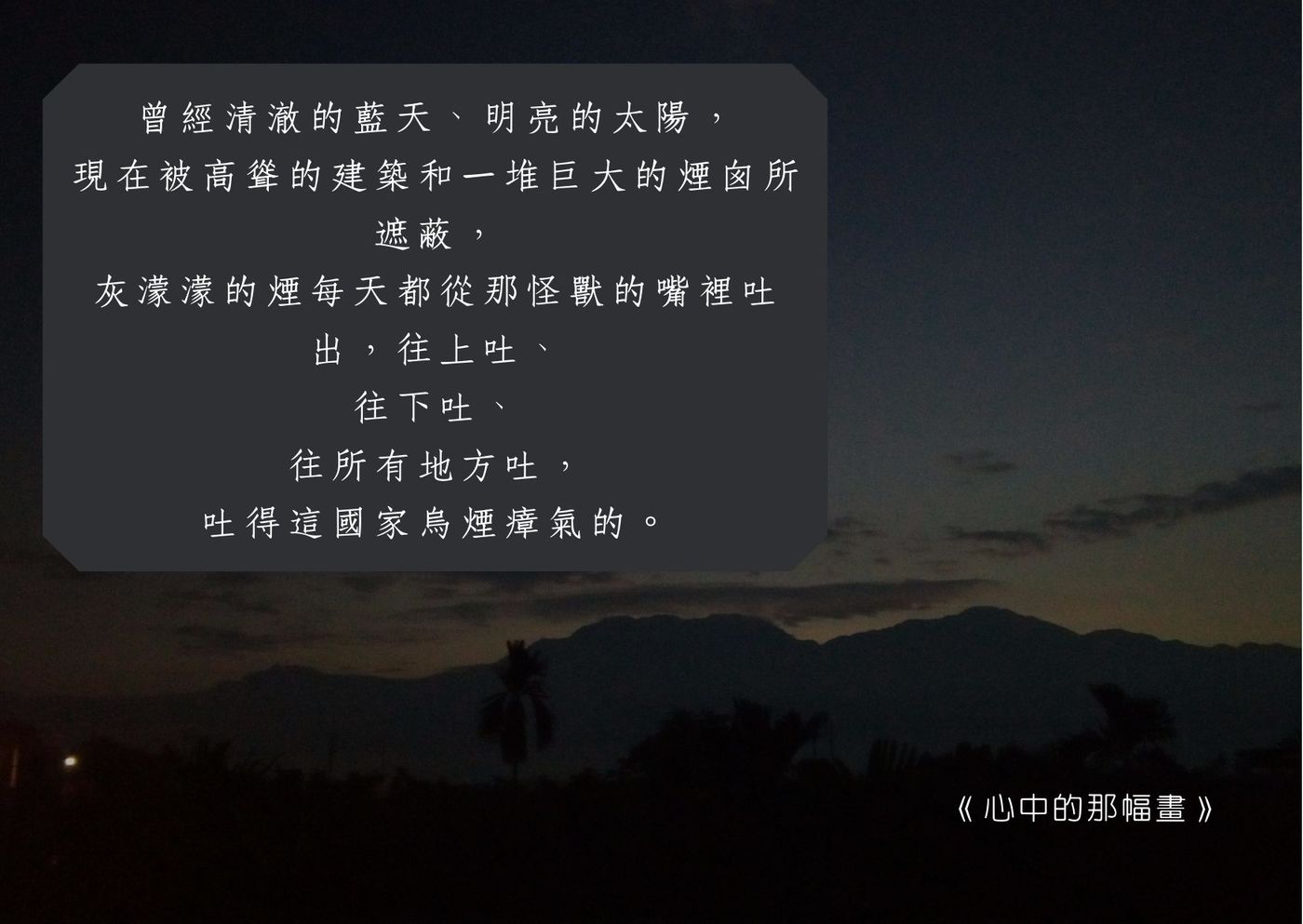金牌教練,師鐸獎名師,太多頭銜擱在肩膀,再加上一桶油漆,一張製圖桌,似乎太重了,那是世人不想馱負的責任,被丟棄在荒山僻壤。
「他們是一群潛能還未被開發的孩子,或許沒有人相信他們能得到金牌,但我相信。」
作為馬那邦山的獨攀者,在鼾聲未止前,便磕磕絆絆上了山。沿臺三線迂迴七十公里,粗糙而厚實的手掌老練地換了D擋,在陡峭山路的彼端,他看見那座熟悉的隧道,隧道的盡頭,是一道隱形的牆,一道由城鄉差距建構而成的高牆。 被體制放逐的少年困在裏頭,被群山霧靄的迷茫給繚繞成了團黑白的混亂,他們躁動,他們糜爛,任由最清澈的失望浸染,兀自把牆面弄的剝蝕零落,卻從未自頹圮不堪的室內走出去。
油漆桶裏的憧憬被他潑灑成輪廓,緩緩滲透進心牆,暈開背後那塊沒有理想的荒蕪境地;製圖桌上擺了張室內設計圖,斷流很久的熱血開始從少年的右心室內汩汩流出,流淌成了夢想藍圖,他們第一次知道,原來自己也可以贏過牆外的人,或者,他們根本可以靠著自己走出牆外。「大家都忘了,他們是群可愛純樸的孩子,只是成績差了點,家裡出了點狀況,在找不到成就感的生活裡受了點傷而已。」一層又一層的鮮豔油漆覆蓋了牆上陳舊的傷口,他奮力的刷著,試圖讓世人也回頭看看,這個絢麗的邊陲地帶有多麼燦爛。
約訪那天,坑坑疤疤的月亮把身子挺的圓潤,只為了恰好和四十三億公里外的天王星匆匆對上一眼,彼此反射的殘光交疊在一起,在天上成了千載一時的奇景。而柏油路上也是,我和平常只有週三和週末才會回家的父親,一起緩慢的散步到家附近的咖啡廳,我們倆的影子合在一起,離的好近好近,但感覺又是如此遙遠,我盤算著要怎麼窺探彼此間的縫隙,他卻像個孩子似的仰起頦兒,直勾勾地盯著那抹橫陳在夜色中的艷紅,好像要穿透天際一般。「太不真實了,實在是紅得太不真實了,像小時候做家庭手工的大紅燈泡,更像,被戳破的廉價塑膠氣球。」他蒼白的雙眉蹙在一起,對夜空中格格不入的紅氣球獃愣著,就彷彿是他兒時來不及抓住的那顆。他不禁和我提起,他那稍縱即逝的童年。
天馬行空朝他傾斜,一不小心壓死了古阿明
「那個小男孩小心翼翼地捧著畫,看那樣子,彷彿手裡的東西是什麼無價之寶,一不小心掉下來就會碎裂一般。」──《魯冰花》
他說第一次看魯冰花是在大學的時候,看完後便不自覺淚流滿面,長大以後看更是老淚縱橫,每一次,他都想起了兒時的自己。「這個社會太現實,總是對天才不太公平,尤其是窮人家的孩子。」出生在新瓦屋庄裡最窮的一戶,老舊的泥磚屋裏,別人家在水泥鋼筋裏頭燒起瓦斯,他家只能勉強靠著颱風過後,拖著犁仔腳挨家挨戶拾來的柴火度日。「那個時候的我很在意面子,很想逃離眾人的目光,拖車的牽繩卻牢牢套在腰際,想跑也跑不了。」或許是掙脫不了,長大後的他在學生身上瞥見同樣的勒痕,便義無反顧地走向陰翳的盡頭,世人視線所不能及的彼個所在。
是從什麼時候喜歡上畫畫的,他也不太記得了,只記得有天堂弟炫耀自己在和台北的畫家學畫畫,一堂課五百塊,他聽了好生羨慕,於是他也和父親嚷著要學。「畫圖有麼个用?花恁多錢?」一個月薪水只有幾千塊的家,怎麼有辦法支撐他學畫畫的開銷?他只能在美術課的時候奢侈的「揮霍」一下,享受顏料隨心所欲揮灑在紙面上的感覺,享受那些不曾存在過的畫面在紙上的觸感,是那麼的真實,無心的「插畫」竟開始萌芽生根,沒有受過正規美術教育的他在學校辦的美術比賽拿了好多次獎。印象最深的是小六那次的保防漫畫比賽,買不起水彩的他想了奇招,把畫面分割成了四塊,用彩色筆一層一層的堆疊渲染成了一張搞笑四格漫畫,最後破天荒的在幾乎都是水彩的入圍作品中被選出,得到了全新竹的第二名。但在那之後,他身上的色彩也幾乎被現實給褪去,上了初中以後,這種「三流」的畫法,再也不會被評審青睞了。
走進他的祖祠忠孝堂,他將指尖抵在自己的牌位上,輕輕摩挲幾下刻在上頭的諡號—禮謙,那是庄頭裡拜生祠的傳統,其實也不太明白緣由。不過我想或許吧,或許那個牌位在紀念的,就是過往那些艱困的日子裡,因為貧困的家境那些曾經以為會變得色彩斑斕,卻被迫黯然死去的渴望罷。約訪隔天的十五,他燃了柱香,裊裊白霧在牌位中間縈繞,像是在跟從前死去的那些阿明們說,謝謝你的堅持與努力,現在的你終於從那些窮困的陰影中走出來了啊。
古阿明死了,但郭雲天沒有
後來再接觸畫畫或者藝術的時候,已經是考高中時偷偷把志願改成新竹高工家具木工科的時候了,原本他是聽朋友說建築師可以賺很多錢,自己也可以藉此發揮繪畫天份,沒想到他被父親罵得很慘,「讀木工科畢業係愛去做棺木係沒?」他邊說邊上揚嘴角苦笑,但眼角泛的淚卻還是流了下來。
聯考的時候,他失常了,只錄取了私立的聯大建築系,於是開始了半工半讀的重考生活。無奈家裡的經濟狀況每下愈況,建築師的夢想似乎離他越來越遠,補習班的輔導老師和他說師大的公費生不用繳學費。為了籌補習班的學費,他去一座座木業工廠打工,鋸一根木棒只能賺一角。「我破了工廠的紀錄,一天能賺五、六百塊!」木頭的稜角一次次被磨平,父親也是,在顛倒的日夜砥礪著,深埋在內心的渴望又悄然被磨開。
世界上有太多古阿明,死了千次百次,卻遇不到郭雲天,在某個輾轉難眠的夜裡,他暗自思忖著,如果自己能當郭雲天呢?重考的第二年放榜,他考上了台師大工教系,五百分之一的錄取率,那天他高興地和老母親在磚瓦前歡蹦亂跳了好幾下,他告訴自己,再也不能放棄任何一個天才。
或許是因為生活太過匆忙且艱苦,他也總是把握每一個充實自己的機會,所以在學生時期,從樂隊豎笛手、羽球隊隊長,到工藝社、吉他社,攝影社、登山社等的一分子,他都是校園裡的風雲人物。「拜託,我以前在竹女打球還有很多粉絲欸,那時候打贏新竹中學、打贏新竹高商的,新竹女中好幾個女生一直看著我這樣子,然後想要給我簽名的感覺,把我當成周天成那樣。」他的語氣興奮地像是剛接下一顆賽末點的殺球。
問他怎麼什麼都會,他深長地說:「多一個技能啊,有什麼不好?」疲憊的魚尾紋浮現在深邃的眼下,卻是溫柔且上揚的,也許對他來說最幸福的事,就是在這壞掉的世界裡,有那麼多溫暖的事物可以擁抱。「還記得那天 你穿著藍色的外套 向我走過來 沒有往常的微笑......」他拿起塵封已久的吉他輕輕唱著,葉蒨文的忘了說再見,他的年少最愛。
山魑杳杳,浮紅欲稔
「第一次走進大湖(農工),其實沒有那種來到偏鄉的感覺,我是興奮的,期待看見那些曾經的自己。」民國八十二年被分發到大湖農工實習的他,還沒感受到偏鄉的匱乏,就和學生們打成一片。然而不久後,他便發覺學校的體制很舊,當年的室內設計科才正從家具木工科轉型過來,科裡的資深老師們沒人要教新的課程,於是他這個菜鳥只能硬著頭皮接下了色彩原理還有室內裝潢等課程,學著學著,自己便不知不覺成了專家。

幾年過去,民國九十四年當上科主任的他開始訓練選手參加技能競賽的漆作和技藝競賽的室內空間設計項目,利用課餘時間和技佐一起東修西補,把原本廢棄的木工廠湊合出來座漆作工廠,申請了十幾萬塊買比賽的用具和材料,試著從匱乏的資源中找出一點什麼。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下班後晚上六點半到九點半甚至夜半時分,他都留在選手室或漆作工廠裡訓練選手。他說,最疲倦的時候反而不是教術科實作,而是教他們最不擅長的學科試題的時候,因為那太乏味冗長了。「有的時候我覺得太累了,當我總是付出全力去教一兩個人的時候,我害怕得不到回應,我害怕我講了很久他們卻仍然聽不懂。」他往窗外的星星看去,像是細數著無數個疲憊的夜晚,夜晚的教室被切分得只剩下彼此,那些曾被世界逃避忽視的平庸和愚鈍都被攤在桌面上,太複雜,太繁瑣,他只能一題題的教他們解開。「不過只要咬牙ㄍㄧㄥ下去,學科過了,在術科那方面,他們可都是天才呢。」他一派輕鬆的喝了涼水,但現實往往沒那麼輕鬆,前輩對於學生的蔑視與嘲笑,認為他們在這麼稀少的資源和資質下不可能得獎,還有其他和他們競爭的高職,大多都有著更豐沛的人才和資金,壓力燒灼滾燙的涼水沿著浮脹的喉尖一飲而盡,當年的他還是咬牙ㄍㄧㄥ了過去。從11月到3、4月的全國技能分區賽,4月到9月的全國技能決賽,到7、8月到11月中旬的技藝競賽,日復一日的刻苦訓練成了生活週期。而原本被友校前輩嘲笑不可能得獎的他和學生們,成功的果實卻在週期的盡頭給碰上了,二十五個年頭來,無意間撒下的一粒粒莓籽,長成的一牕鬧紅結實積累了19座金手獎,全國性技能競賽近百位學生獲獎。
零畸之地的粉塵

關於三千坪牆壁彩繪的濫觴,是源於某天他驀地瞥見教室外牆壁上幾道淺黑色的鞋印,「一開始我是很生氣的。」他微微地掐住杯子,「不過後來,我就萌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他將想法都寫成了教案,創意工具讓夢想起飛。他教學生捲起捆布絞了絞,均勻滾動的雙手在牆面上暈染成了不規則的斑紋,那是他自創的滾布法。後來更發展出了型染法、海綿拍打法、木紋器型法、規筆大理石畫法,一個個黑色印子被塗上的顏色覆蓋,像是那些他在背地裡為學子奮鬥的足跡,最後只徒留在獎台上的光鮮亮麗。
我問他,塗上的漆為什麼會龜裂破碎成不平整的模樣呢?他說,那是塗裝瑕疵,如果溫度或者濕度改變了,漆料是會黃化、白化甚至粉化的。我無法想像現實的溫度是多麼的灼烈,當我碰觸的父親十幾年來的心血還有漆作訓練廠,因為決策者們所認為的沒有必要和經費不足而被學校拆掉的惝怳,還有鐵了心去考校長卻在決選時懷才不遇的無奈,才明白油漆被陽光曬乾的無助。
他哽咽了許久,憶起那些訓練的歲月,印象最深的便是在漆作得到全國第一的W了,他是個堅持到大二還在比技能競賽到孩子,高三那年本來的奪金機會,卻因為調色競速時看錯題目而葬送了。「他真的是個很認真的孩子,幸好老天爺最後還是眷顧了他。」平平淡淡的一句,卻停滯了五年才能脫口而出。
斷掉很久的,都能榫接回來
直至金手獎第一名填滿了選手室的最後一色,他便不再訓練孩子了。「我想用剩下的時間去彌補自己身上的那些空白。」他怔怔地望向我,「抱歉了,如果你小時候我可以多花一點時間來陪你就好了。」就如同外頭遙望月球的天王星,成為天王的代價便是不能當一顆陪伴在月球旁的地球吧。如果說那些被流放的孩子是流星,那已經替他們找到依歸卻被隕石砸傷的他,現在要尋找的便是那條回到初衷的軌道吧。
「我決定要去考一張建築師證照!」渴望閃過睫毛,後來的日子他去了北科大技職所,把因為因為對選手培訓的投入而延畢多年的博士讀完,也找了熟識的畫家盤算著拜師學油畫,爬百岳,橫渡日月潭,甚至再去次聖家堂,那是他從高中以來便仰慕的建築師高第之作。這次,他要靠自己調出的色彩覆蓋身上那些人情世故劃出的傷痕累累。
我問他,如果想像內心是一棟房子,會把他漆成什麼顏色的,他應道:「藍色吧,因為那代表著大海,很自由,很美。」從兒時家門前的十五朗圳,到大湖的山間泉水,還有十幾年前在南方澳考潛水證的時光,出外奮鬥的憧憬讓他在外漂泊了快二十幾年,飄盪週期的唯一縫隙,是珊瑚堆成的礁堡,只有每年寒假在墾丁海泳才能沉溺進去。他說冬天的太平洋還是溫熱的,可以把油漆殘留在身上的有毒物質皆餘洗淨滌除。
後記 熱牛奶與垂流

還記得上次和父親靠得這麼近,平平靜靜地聊了這麽久,是重新粉刷我房間的那天下午,把佈滿塗鴉的牆面給重新粉刷,他輕輕地抓著我的手,從牆面滑過,覆蓋住牆面上幾個不忍直視、歪歪扭扭的大字「我會考上第一志願!」,他嘴上偶爾會唸了幾聲關於會考沒考好的事情,他的刷子卻好像是這樣在說,蓋住不看就好。漆完後他遞給我杯熱牛奶,他說牛奶可以抵抗漆料裏頭的毒素,那杯牛奶好暖好暖,傾刻間似乎融化了心牆間的縫隙。
或許罷,曾經我們的感情似漆,卻不曾如膠。
有些油漆只會凝滯在表面,覆蓋兩人心牆間的壁癌,悶得彼此近乎窒息。別人說,他是名師,他是金牌教練,但從前的我只覺得他是個自大迂腐的騙子,幼稚園他總在我的沉睡中返家,在我的鼾聲中離家,原本一家三口的小餐桌上只剩下被堆滿的學科、術科講義,後來真的沒空管我了,又把我丟在祖父母家;偶然在他房間抽屜深處翻到幾盒涼菸,他說那是他沒收學生的,但陽台的菸味卻還沒散去。
他撒了好多瞞天大謊,真的好多好多,如果沒有親眼看過牆內的縫隙,我想那些漆是會凝固一輩子的。
那些年來被列入徵收範圍的老房子面臨拆遷的命運,為了還蓋新房的房貸,他總是在週末四處奔波掙錢,然後平日晚上還得訓練選手。「老闆你好,可以幫我送兩個六十塊便當到門房嗎?錢我下禮拜一起給您。」幾乎是每個假日中午,他都會打電話給自助餐確認孩子有沒有飯吃,自己卻什麼都不點,只吃家裡的剩菜剩飯。
我想起了垂流,那是另一種塗裝缺陷,當上漆時太貪心,一不小心塗了太多,漫溢出來的顏料便回傾瀉而下。或許父親的愛之於我,早已氾濫成了垂流,那些他試圖彌補的關心還來不及在心牆凝固,便被感到厭煩的我給抹去了吧。
約訪那天,我同樣點了杯熱牛奶,當它流近血液的末梢,垂流好像滲了進去,心牆深處的那棟心室內,現在,或許就連現實也無法將它抹去了啊。
作者介紹 林怯
「視倏忽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
林佳諭,字怯,號林黛賽玉,停滯在某個不合時宜的頃刻,怔忡不安的亮孩,卻小心翼翼地在體制裏漆上象牙白色的痕跡,因為最脆弱的地方,往往是敞開而溫柔的。
那是關於浪漫,關於叛逆,關於無人知曉的旮旯,關於惝恍間的所見所聞,關於我僅擁有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