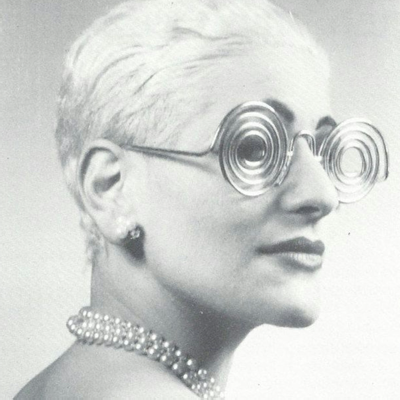晨光漫過蘭桂坊的玻璃幕牆,咖啡杯底沉澱的往事在蒸氣中甦醒。侍者擦拭銅壺的指節泛著象牙色光暈,讓我想起祖母生前梳頭時,老檀木梳滑過銀絲的弧度。人生確如鏡花水月,偏是這浮光掠影裏的溫存,比大理石紀念碑更經得起歲月摩挲。
中環街市二樓的茶餐廳,陳老闆每日用同一塊麂皮抹玻璃杯。三十年前妻子病榻前許諾「要擦出全港最亮的杯子」,如今他虎口的老繭已能打磨時光。某個暴雨夜,我看見他對著櫥窗呵氣畫心形,水霧裏浮現的或是太平山頂的初吻,或是瑪麗醫院走廊的消毒水氣味。蘇軾說「事如春夢了無痕」,卻未見萬家燈火中,每個窗格都鑲嵌著不願醒來的夢境。
深水埗唐樓天台的晾衣繩搖曳如五線譜,住客們的記憶在褪色被單間流轉。三樓阿婆保存著五十年前逃難時的繡花鞋,七樓後生仔的電結他鎖著中學初戀的顫音。博爾赫斯筆下的《阿萊夫》該是這般景象——在時空的褶皺裏,每粒塵埃都折射著銀河。我們何嘗不是提著易碎的琉璃燈,在永夜中交換彼此的光暈?薄扶林漁港的疍家夫妻,將四十載風浪綴補成船帆。老翁掌舵時總哼著咸水歌末句「月落星沉天欲曉」,阿婆便接「共君今夜不須眠」。去年颱風折斷桅杆那夜,他們在搖晃的船艙對飲陳年糯米酒,笑說這般顛簸才像洞房花燭。李商隱「此情可待成追憶」的惘然,竟被漁火煨成了琥珀色的當下。
太平館餐廳的留聲機仍在轉動周璇的金嗓子,白頭侍應托盤上的舒芙蕾總在最佳時刻坍塌。這座城的魔幻在於,所有稍縱即逝的美好都被賦予了儀式感。就像重慶大廈轉角的報攤,印度老者三十年如一日地擺放《明報》,他說紙墨幽香能讓亡妻的倩影從鉛字間娉婷走出。
暮色漫上維多利亞港時,我看見撐拐杖的老紳士對著渡輪敬禮。他珍藏的勳章在1953年的大霧中沉入鯉魚門,如今對著鋼鐵巨輪致意的,是那個在甲板上為愛人讀濟慈詩的年輕少尉。我們嘲笑唐吉訶德大戰風車,卻未解每個清晨對鏡打領帶的儀式,都是對歲月風車的溫柔宣戰。
最後一班天星小輪靠岸時,賣白玉蘭的老嫗將未售盡的花串拋向浪花。素馨載沉載浮,恍如銀河傾瀉。忽然懂得為何張愛玲要將香港比喻成華美的袍,原來每道皺褶裏都藏著未完的針腳。此刻星光跌落水面,竟比鑽石更永恆——因這剎那光華,已收納了百年潮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