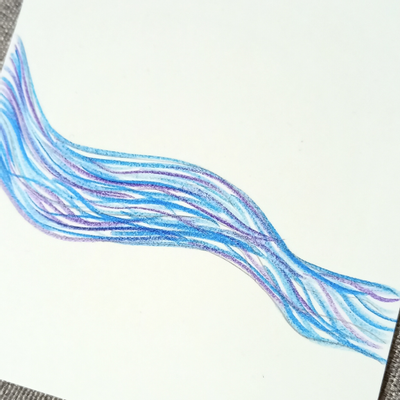別看我每天在夜晚迷走於台中舊城區的市街行道,更總是喜歡穿梭在黑暗裡的巷弄路角;然而不是我在自誇,小時候的我可是很怕黑的,是個跟正常人一樣畏懼黑暗的小孩。
小時候住在台中海線的鄉鎮,是個非常鄉下的地方。那個年代的鄉間,馬路不會太寬,很遠才會有一盞水銀路燈……是嗎?也許設備還沒那麼好,印象中路燈形狀是長條型的,說不定燈罩裡頭安裝的是比水銀燈更暗的日光燈;總之那個路燈的亮度實在有限,有效的照明範圍當然沒辦法很廣,僅能引導路上的行人朝著燈盞走過去,到了路燈底下,再朝下一個光點前行;當然用路人絕對無法看見路面上有狗屎而避開,會不會踩到屎全憑運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旦環境中的照明被關掉,視覺被剝奪時,聽覺會被更大程度的開啟,這幾乎是一種很自然的生物機制。在鄉下,入夜熄燈後,各種聲音都會被放大呈現,一點點風吹草動,都能引發人們的無限幻想;這時候過去聽過的各種鄉野奇談,便會開始在腦海當中輪播,尤其是越恐怖的那些越是會強勢佔滿當時的腦容量。當然會有這樣的幻想,大多是來自於小孩子可貴的天真,遲鈍的大人大多無法享有這種迷人的奇幻樂趣;也許有做虧心事的大人會例外,而被許多幻想充滿腦海的小孩,也未必覺得那是什麼樂趣就是。
孩童時期在鄉下,夜晚是全家共同睡在一個大通鋪上。雖然住的是簡陋的閩式土磚屋舍,但通鋪上還是有個放棉被的日式押入——即放棉被的小櫥櫃,小叮噹(多拉A夢)睡覺的那個空間——。那個小櫥櫃白天常常成為小孩躲起來玩耍的角落,然而到了夜晚,卻成了小孩子的夢魘——櫃門從裏頭被拉開,接著會有妖怪緩緩爬出來抓小孩的黑洞。
夜裡,房間中會留一盞三燭光的小燈泡亮著,雖然昏暗,好過熄掉後的伸手不見五指。隔壁的起居活動空間,一座有著鐘擺的老爺時鐘,縱擒器來回運作發出的滴答聲,被夜晚的寂靜放大得響若雷鳴,連在隔壁房間都可以聽得很清楚;這會讓我的視線,隨著注意力投射往房門外的黑暗。有時候房門外的黑暗當中會有些許微光,並傳來書頁翻動的聲響,那是我的三姑姑利用夜裡時間,批改學生作文本的聲音,她是國中的國文老師;那個翻頁聲,能夠讓我稍微安心一點,因為知道至少有長輩還清醒著在活動,這就像是夜晚的世界還有人在駐守著,妖魔鬼怪就無法來侵擾一般。
鄉下的廁所不在屋內,而是在屋外一個邊陲角落,雖然建築物是相連的,但與人們居住的空間,中間還相隔著穀倉以及豬圈,無法從室內直接去上廁所,而是得繞室外的路徑。因此別說是下雨天要去上個廁所還得打傘很麻煩,就算沒下雨,夜晚要上廁所,打個手電筒或是提著燈籠也是必要的。
小時候會與弟弟相互結伴去廁所,廁所裡只有一盞五燭光的昏黃小燈,相當幽暗;廁所外面等候的人,手上的手電筒或燈籠更是亮不到哪去。然而小孩頑皮,上完廁所後,我們常常用提燈或是手電筒的光去照旁邊的豬圈,睡夢中的豬隻會被驚醒掀起一陣騷動,我們就會覺得很好玩,但大人會生氣。後來想想,也許豬隻的騷動並不是因為受到驚嚇,而是牠們以為有人來餵食有得吃而感覺到激動。這時候的我稍微大一點了,對於黑暗的恐懼似乎也稍微消退了些。
不記得從什麼時候開始,我變得不再懼怕黑暗,對於身處幽暗的環境,反而讓我感覺輕鬆且自在。甚至在如今的都會裡,黑暗,反而成了我渴望的棲身所在。為什麼會這樣?我也說不出個具體的所以然,只知道,找到一個靜謐乾淨的黑暗角落,就算只是身處片刻,也能讓我暫時避開世間的紛擾,產生出獨享這整個世界的錯覺……對,只是錯覺;但即便是錯覺,也好!